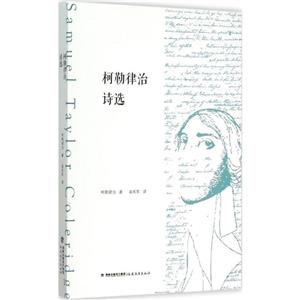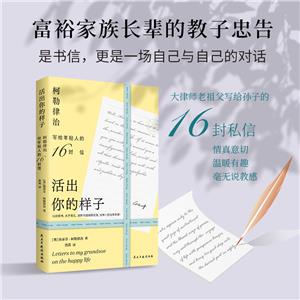作者:张玮玮著
页数:184
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50965915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作为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杰出代表,柯勒律治是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神学家。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柯勒律治在其诗歌作品中表现出对自然强烈的生态伦理关怀,并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与此同时,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同样占据了他哲学和神学思考的中心。他始终从哲学和神学的层面上追求上帝、人和自然的整体性,并最终以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为神学支撑形成了极具现代意义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此外,柯勒律治还追求文学、哲学和神学等一切知识体系的统一。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后,随着世界的祛魅和社会的日益世俗化,宗教的影响日渐式微,但艺术能够通过向人类再现上帝的创造过程成为神、人和自然之间的调停力量。艺术能够令人类超过物质的束缚,恢复对无限的神性世界的向往,使人意识到与自然世界的亲密联系。因此,《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柯勒律治文艺理论研究》试图全面梳理柯勒律治的诗歌作品和哲学及神学著作,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研究柯勒律治的自然观以及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并梳理建立在他的神学自然观基础上的艺术理论。为凸显柯勒律治神学自然论的艺术观的独特性和意义,该书还将其与华兹华斯和爱默生进行对比。在具体内容上,《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柯勒律治文艺理论研究》将回顾西方文学史中自然这一维度的相对缺失以及自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回归,以此凸显出柯勒律治把自然置于诗歌创作及诗学和哲学思辨的中心的重要意义,追溯柯勒律治艺术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和宗教背景,进而系统理柯勒律治通过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概念形成的有机整体自然观。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模仿”“天才”“想象”“象征”等概念的探讨,系统梳理柯勒律治的艺术理论。此外,通过与华兹华斯的对比研究并考察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者对柯勒治思想的传承,还将揭示柯勒律治艺术理论的独特性及其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张玮玮,女,1982年3月生,山东淄博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副教授,博士。2015年6月毕业于山东大学文艺学专业,师从曾繁仁先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自参加工作以来,发表论文6篇,其中CSSCI论文2篇;主持省级课题1项,厅级课题3项,参与课题多项:先后获得山东省软科学成果奖、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山东赛区)讲课比赛三等奖等奖励。
目录
第一节 选题背景
第二节 柯勒律治生平及著述简介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第四节 研究意义
第一章 西方文学中自然的位置
第一节 西方文学人文传统中自然的缺失
第二节 田园文学中“自然”的辨析
第三节 浪漫主义文学中自然的回归
第二章 柯勒律治自然观的形成背景
第一节 社会历史背景
第二节 哲学背景
第三节 文学背景
第四节 自然科学背景
第五节 宗教背景
第三章 柯勒律治的“三一论”神学与有机整体自然观
第一节 从泛神论向“三一论”的转变
第二节 “三一论”神学观与有机整体自然观的形成
第三节 自然的有机整体性
第四节 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
第四章 柯勒律治的神学自然论艺术观
第一节 艺术本质论——论“模仿
第二节 艺术主体论——论天才
第三节 艺术创造论——论想象
第四节 艺术表现论——论象征
第五章 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自然观和艺术观的比较研究
第一节 从”共生“到分裂
第二节 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神学自然观的分歧
第三节 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艺术观的分歧
第六章 柯勒律治对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
第一节 柯勒律治与美国超验主义的兴起1
第二节 爱默生对柯勒律治思想的同化和吸收
第三节 爱默生与柯勒律治思想的差异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第一节 结论
第二节 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节选
《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柯勒律治文艺理论研究》: 其次,针对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没有任何区别的观点,柯勒律治指出,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之间“可能存在着、确实存在着,也应该存在着一种本质的区别”。③柯勒律治认为,诗歌语言能从根本上区别于散文语言的原因在于格律。格律不是附加于诗歌之上的,而是诗歌的本质特征和正当形式。与华兹华斯一样,柯勒律治也认可诗歌是自然感情的产物,但是他指出人的心灵中同时存在着控制激情冲动的努力,即为了达到愉悦的目的而进行的有意志和判断的行动。二者的互相对立既能够彼此加强,又能彼此平衡构成格律。所以,一方面,格律是在一种加强了的情感状态下产生的,它本身就伴有兴奋时的自然语言;另一方面,格律的成分是通过人有意识的行为人工地合成的,诗歌中应当具有意志的痕迹。因而诗歌语言具有一种统一性,“一种热情与意志的相互渗透;自发的冲动与自主的意图的相互渗透。”④但是,虽然格律是诗歌语言区别于散文语言的本质特征,但它却不能构成诗歌的充分条件。因为一首诗就是一个准自然的有机体,它的不同部分之间应当互相支持。诗的格律要求其他部分的配合,并反过来融入诗的整体之中。这是柯勒律治对一首诗或者说狭义的诗歌的认识。除了对一首诗进行界定,柯勒律治还试图为总体的诗寻求定义。以柏拉图、泰勒主教(Jeremy Taylor)等的作品为代表,总体的诗也许不具备格律的形式,但他们作为天才的作品被柯勒律治认为是诗的最高形式。柯勒律治并没有正面回答“诗是什么”,而是转而探讨“诗人是什么”。“诗人(用理想的完美来描写时)将人的全部灵魂带动起来,使它的各种能力按照相对的价值和地位彼此从属。他散发一种一致的情调与精神,借赖那种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使它们彼此混合或(仿佛是)溶化为一体。”①诗人凭借自己超凡的想象力能够将同一与殊异、一般和具体、概念和形象、个别的和有代表性的、新鲜的与陈旧的、天然的与人工的等一系列对立的事物彼此调和,形成有机的整体。因而,在柯勒律治的批评中,对于不一致的或对立的审美特性加以想象地综合,并以此替代华兹华斯的“自然”而作为诗歌最高价值的判断标准。②对立面的调和恰恰是通过人的想象力实现的。 可见,柯勒律治反驳华兹华斯诗歌语言观的依据最终汇集于他的想象理论上。他在他的艺术理论中将想象视为诗歌的灵魂,赋予想象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指出想象作为一种有机的能力与机械的幻想是从类别上完全不同的两种能力。反观华兹华斯,虽然他的诗歌创作使得柯勒律治确定,有必要假定想象力的存在,推动了柯勒律治想象理论的提出,但柯勒律治对他的想象理论却颇为不满。在柯勒律治看来,华兹华斯想象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将想象与幻想混为一谈。华兹华斯同样认可想象是诗人必不可少的能力,也说想象是创造性的,但他接着指出幻想同样也是一种创造能力:“幻想既然是一种主动的能力,那么它在自身规律支配下,有它自己的精神,难道不也是一种创造能力吗?”③与此同时,他又宣称幻想和想象都是“改变、创造和联想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