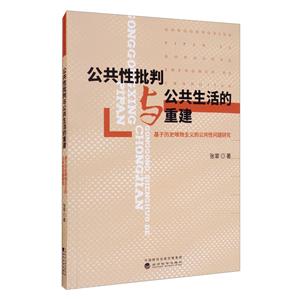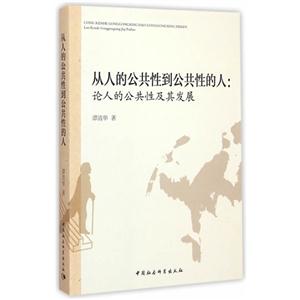作者:廖申白
页数:304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ISBN:9787303088270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是借助历史学和社会学材料对交往生活这一主题的哲学省思,构成对它的一种预备性的研究。内容包括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转变;村社社会与身份制度的历史变迁;宪政、民主与公民;国家与社会之间——重叠交错的中间领域;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等。
目录
节选
nbsp; 序
中国近两个世纪的社会发展经历着一种转变——交往生活的
公共性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中国的村社社会基础逐步改变,农
民作为身份的制度痕迹在逐步消失,公民社会及其实践的公共领
域在逐步发育。寻求中国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中的生活规范——
公民伦理的健全发展,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实践目标。
人们曾习惯于把经历这种转变的发展看作必定要我们远离自
己的精神家园,这种见解今天已经不再令人信服。我们文化传统
的精髓仍然保持它弥久常新的生命力,并且有待我们继续发现它
的价值。但是,中国社会当前仍然在经历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转变
的阵痛。一个公民社会及其实践领域的发育健全可以从三个方面
来判断: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领域的适度界分,法律的可依赖程
度和社会在公共交往领域的确信程度。健全的公民伦理是公民交
往生活的相互有效性要求,是一个政治社会维持公民间的自愿交
往和持久和平的合作与协商所需要的准则和规范储备。作为一种
生活的或普遍实践的伦理,健全的公民伦理是一个公民社会及其
实践领域的健全发展的伴随物,它随着这种发展而发育,并促进
着这种发展。在这样一种公共交往生活伦理基础上,公共交往将
被习惯地视为不同于私人交往的领域,法律的可依赖程度将比较
高,对公共交往行为的公信将可以期待。中国的伦理传统,尤其
是儒家伦理传统,是否能经受住这种阵痛,取决于它是否能容纳
一种私人交往和公共交往领域适度界分、在公共交往领域中重视
法律的可依赖性,并基于此而形成社会公信的公民政治伦理文化,
成为对它自身的必要补充,与它共同生长为一种新的伦理文化传
统,并同时在私人交往领域中保持它的影响人心的文化生命力。
对于儒家学说这一有续久生命活力的传统,我们或许有理由期待
这样一种发展。
这三本小书是对于这一主题的一种尝试性的探讨。但它们不
构成一种体系性的系列。每本书的主要撰稿人都在独立地阐述自
己对这一主题的系统思考。但是它们之间又有所分工。《交往生活
的公共性转变》是借助历史学和社会学材料对这一主题的哲学省
思,构成对它的一种预备性的研究。同样基于对历史的、社会的
材料的省察,《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着重从理论上探讨一种适合
中国的这种发展的健全公民伦理的内含。它构成整个系列的主体
部分;《公民伦理教育的基础与方法》将对一种健全公民伦理的理
解引申到教育的方面,探讨一个逐步成熟的公民社会怎样能够使
这种伦理成为它的成员和新一代的成员的生活观念,以及怎样能
够通过这种教育鼓励他们去发展和追求各自的、更高的生活价值。
这个系列研究仍然仅仅是初步思考的结果。它所述引的材料
远不够充分,它的观察和所形成的判断与观点都具有尝试性。在
把它呈献给学界同事和读者时,我们唯一希望的是关心这一主题
的同事和读者对它提出批评意见,以期引出对这个主题的更冷静、
更清晰的探索与思考,因为这对于中国的今天与未来是重要的和
有益的。
四、先有共和国民,还是先有共和宪政
在政治哲学的思考上,立宪派提出的真正有意义的核心论点是,
不能够坐等国民程度自然提高,国民的程度是在君主立宪的实践中提
高的。而且,国民的程度越提高,君主就越将成为“虚君”,国家就
越可以回到国民的掌握之中。君主立宪制下的国会的活动亦然。杨度
指出,各国国会在初期都是不完美的,经过几次磨练,议会或许经过
一连串解散,才会逐步变得有秩序,人民也才会逐渐知道怎样才能矫
正政府。人民也只有在参政过程中才能提高公共心,要使人民有公共
心和参政热情,就要开国会,实行立宪。①张謇认为,国会是使国民
演进的制度,如果不开国会,国民的程度永无增进的可能,对多数国
民,需要一面施以教育,一面以政治来化育,而不是坐等国民程度整
齐划一。②
但是,在梁启超看来,如果国民、政党、议会的活动尚不能达到
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尽管这并不意味完善的)程度,不仅开共和政
制,而且开君宪政制,都会将一种本来很好的政制败坏。所以,与其
在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下草率开宪政,不如先使精英们将注意力放在
培育国民以到达基本的程度这件事,于国家和民族更为有益。
这看起来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先有基本合格的国民,尔后有民主
宪政,还是相反?这场讨论所提出的事实上是民主政治中的一个永恒
的话题,也许,还是一个永无完备答案的话题。就民主制度本身需要
人们理解它的那些程序性安排的含义和尊重这些安排的规则而言,梁
启超是对的,民主制度的习惯需要培养。基本的事实是,在20世纪
初的清末社会,社会还没有基本的准备:农民还束缚在身份制度中,
工商界还在初步的发展中,还没有产生对宪政的强烈要求,中国人在
过去的历史中没有发育的社会公共生活,因此也没有过民主的政治生
活所需要的尊重共同的契约、尊重规则的习惯,社会启蒙思想刚在发
生,就面临着拯救国家与民族于危亡的历史境遇,对个人权利、自由
的尊重,对个性和独立人格的尊重,都让位于服从救亡的使命,而没
有获得足够的历史空间来展开。辛亥革命是一个勇敢的建立共和宪政
的尝试,但它所实行的共和宪政缺乏充分的社会准备。正因为这样,
袁世凯才抓住时机从革命派手中窃走了革命的果实,并随后无情地嘲
弄了共和宪政。也因为这样,在袁世凯之后,共和宪政成了地方强人
轮换控制政治的装饰品,再也没有恢复它作为一个初生的宪政政体的
生气,并最后结束于国民党的党治政治中。
这些社会的准备需要从基层社会中逐步发生的改变来实现,需要
知识精英们将这些改变做深入的讨论,提炼健全的、能为普通民众理
解和接受的观念,再影响到基层社会的组织结构。这些社会的准备需
要制度性的改变这一点,其实是梁启超和立宪派甚至革命派之间的共
同点。既然国民过民主制度的生活习惯需要培养,那么就需要一个帮
助他们培养这种习惯的环境。作为帮助实现多数人治理的制度,创造
这样的环境并促使人们在此环境中养成习惯正是民主制度本身的问
题。如果这些思想首先着眼于社会基层生活性质和交往关系结构的发
展,就是更为真实的见解。梁启超与立宪派关于国民程度与宪政之关
系的讨论是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宪政观念的一次重要的启
蒙课程,甚至至今都还有意义。
第四节 士绅与乡村自治
一、半自治的乡村保甲户籍管理制度
中国自商周以来,在乡村基层一直沿袭着不同形式的里甲、保甲
户籍管理与维护基层治安的制度,这种制度具有半官府管制半自治的
双重性质。历代王朝设立此类制度的目的,一是为了对乡村基层实行
网格化的有效控制,二也是为了减少由国家支付薪俸的官吏的数目。
采取这种制度形式,国家在乡村基层可以不设官吏,以地方人士实行
自治式的治理,官吏可以不下乡,民治也不出乡,国家节省了县级以
下的财政投入,又能够从乡村有效征收到税赋和徭役。这是一种出于
王朝政治目的的以民治民策略。①所以,这种制度得以沿袭数千年而
不辍。
这种制度也使乡村基层社会有了半自治的性质。所谓半自治,是
说它不是充分的自治。它要由国家来授权,由国家来指派一些人代表
国家来治理,而不是由基层地方的人们代表他们自己来治理。自治社
会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民主的自治,即由社会全体有资格的公民共同
就重要的公共事务作出决定的自治。另一种是强人的或地方精英的自
治,中国过去时代和西方中世纪的采邑庄园的自治属于这一类。人们
常说的“天高皇帝远”,就是指在王权不及的地方,由强人或精英们
统治一方。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是普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