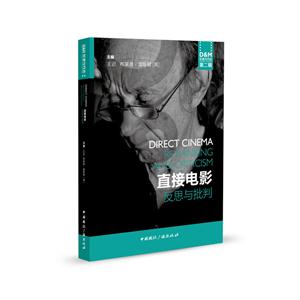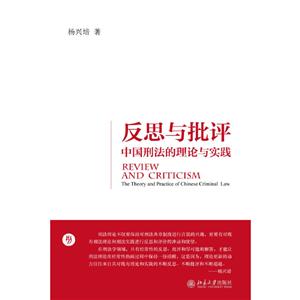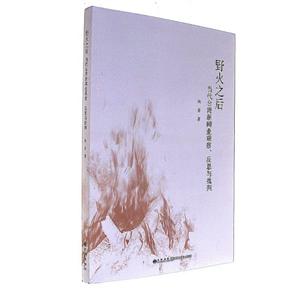
作者:向芬著
页数:292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ISBN:9787510858192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以台湾民主转型中的新闻传播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台湾新闻界、学界人士的访谈,展现台湾民主转型中台湾新闻传播的历史过往和现实,并探讨台湾媒体解禁后的实际状况,分析了台湾媒体政治光谱分化、商业势力极端垄断、新闻品质下降和媒体视野狭小等现实问题。
作者简介
向芬,博士,副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史论、新闻传播制度与管理政策。
目录
目录
序一公共服务媒体必须是领头羊
序二我们找到星星了吗?
第一章通天塔与不归路:从报禁到解禁
一、行政管制与自由市场
(一)党政军控制媒体和高校内化教育
(二)由硬转软的控制
(三)自由市场的媒体乱象
二、侍从媒体与政治合谋
(一)强人阴影下的侍从媒体
(二)台湾媒体是民主的推手还是权力的跟从?
(三)新政商关系——合谋的伙伴
三、西化影响与本土意识
(一)自由主义思潮对解除报禁的影响
(二)新闻传播政策制定中的唯西方论
四、新闻传播政策与良性媒体环境
(一)以“非无限”的自由与合理的管制去除市场之虞
(二)长远规划符合本土的新闻传播政策
第二章野火之后:台湾媒体市场、行政管控与新闻自由
一、何谓新闻自由?
(一)欠缺共识的新闻自由
(二)作为制度性权利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区别和重叠
(三)媒体的自由与民众的自由
(四)消极的新闻自由和积极的新闻自由
二、台湾媒体解严后仍被诟病缺乏新闻自由的症结
(一)第四权的适用与局限:媒体的特权与限权
(二)自由放任论的终点:媒体所有权与多元化市场
(三)社会责任论的乌托邦?——人民利益、政府作为与
媒体操守
三、寻路台湾:新闻自由如何构建?
(一)结构性管制:以权力的制衡来保障新闻自由
(二)合理的社会结构促进媒体多元化和自由度
(三)偏重公共媒体的多元资源
第三章台湾新闻学界访谈录
一、郑贞铭访谈录
二、冯建三访谈录
三、林元辉访谈录
四、林丽云访谈录
五、苏蘅访谈录
六、陈百龄访谈录
七、倪炎元访谈录
第四章台湾新闻业界访谈录
一、陈国祥访谈录
二、尤英夫访谈录
三、何荣幸访谈录
四、邱家宜访谈录
五、程宗明访谈录
第五章台湾新闻管理界访谈录
一、邵玉铭访谈录
二、苏正平访谈录
后记
节选
一、郑贞铭访谈录
郑贞铭简介
文化大学新闻学系教授(退休)。1936年出生,曾任文化大学新闻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香港时报》董事长,英文《中国邮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台湾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代表作有《新闻原理》《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新闻采访的理论与实际》《世界百年报人》等。曾荣获“中兴文艺奖”、“五四文艺奖”(台北)、“新闻教育终生成就奖”(纽约)、“美国新闻教育特殊贡献奖”(纽约)、“文化交流贡献奖”(香港)。
访谈时间:2013年10月22日
访谈地点:咖啡厅
自由与控制永远是在拉锯当中
苏惠群(以下简称苏):提到报禁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
郑贞铭(以下简称郑):我想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有两个基本的观念跟认知说一下:第一点是从两三百年英美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自由的发展,以及我们台湾六七十年来的发展,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自由与控制永远是在拉锯当中,从两三百年的历史去看是处于拉锯之中,不只是台湾,从整个人类新闻史来看,过去英美报人多少人为了新闻自由,向政府争取自由,而牺牲生命,后来英美新闻自由的思想观念普遍走入民间。我想这个前提的意思不是说自由就是好的,控制就是不好的。其实自由也好,控制也好,都是中性的名词。我们一方面当然要追求自由,可是你能够永远不受控制吗?父母对你的教育是一种控制,对你行为的管制也是一种控制。我今天坐在这儿,我有伸个懒腰的自由,可是伸出去的手不能碰到别人。所以,西方说自由是以自由观的鼻子为界,你不能碰到他的鼻子,去侵犯别人的自由。其实自由也好控制也好,都是要去追求“为什么要传播”这样一个理想,我们人类为什么要传播?传播最重要的就是要沟通、要增进了解。如果说你自由过度,侵犯别人隐私权,你是不是就侵犯到别人了呢?这是我首先要提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二个对这个议题很重要的观念是,所有的自由包括新闻自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有权力的人赏赐给你的,永远都要争取。所以当自由和控制在对抗的时候,自由退一步、控制就进一步,控制退一步、自由就进一步。所以,我第二个观念,自由是要争取来的,不是政府赏赐给你,或者有权力的人赏给你的。对新闻自由的争取永无陨时,你不要认为我现在已经够了,因为你说够的时候就是退的时候,控制的力量又过来了。
苏:这种对抗是永远会持续下去的?
郑:对,要用历史的观点去看。也不只是看台湾的历史,要看整个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新闻自由的历史。以上是我的两个很重要的基本观点。
台湾报禁的问题,老实讲也是当局控制和新闻界争取自由的对抗或者是斗争的结果,为什么有报禁?就是当局要控制新闻界,当局控制新闻界确实也是有当时的背景、理由以及需要的。但是,新闻界争取自由,台湾能够变成今天这样也是多少人付出的努力,不过我自己个人认为,时空背景的转变也是一个因素。首先要了解当时台湾的社会背景,台湾被日本统治了50年,日本对台湾也是实行控制,思想控制包括学日文、办日文报等等。本省的老一辈的人还有人会很怀念日本,这一方面也是受了日本思想、精神控制的结果。
结合台湾当时的背景,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台湾今天新闻自由的环境真是得来不易,可是台湾为什么会变成自由民主思想为主流的一个地方?当时台湾当局要实行报禁,还有当时时局的关系,比如与中共之间的对抗,我们那时也觉得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无孔不入,对不对?新闻界的渗透也是其中最重要的渗透之一,后来因为“匪谍”之类的,新闻界也被抓了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从蒋公时期有报禁,这有其时空环境和背景,一方面为了保持台湾的安全,跟中共对抗;另一方面,日本奴化思想还没有去掉,需要把它去掉。
苏:我们一般会想到第一个,第二个想得比较少。
我们今天用的主要理论还是英美的
郑:台湾从那样一个社会走到今天这样的自由民主真的是得来不易。第三个是难免的也是事实,就是蒋公个人的威权思想,从他的个人性格还有过去他在大陆的统治等等,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威权性格。他当然比较没有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他是日本受的教育。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讲台湾报禁、报业发展的时候,必须讲到台湾早期负责新闻宣传政策的几个重要的人,都了不起,这些人刚好都是我们这一辈的人,他们一方面当然要遵从蒋公的管制路线,但是另一方面这几个人都是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像马星野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谢然之是明尼苏达大学和密苏里新闻学院,他们都做过第四组主任,也都是宣传部长,都是直接负责宣传政策的,还有曾虚白、董显光。这些人个人受教育的背景和他所了解的新闻传播观念的东西,今天老实讲,中生代的这一批新闻学研究者从来没有去考虑这几位先生对台湾新闻事业走向的贡献,一方面他们要尊重蒋公的意志,一方面他们要在各种场合展现应该走向何处。
我在谢然之老师90岁的时候在美国去看过他很多次,有一次他亲自跟我讲过:一方面蒋公的意思他不能违背,另一方面他要去发展新闻教育的原因是什么?新闻教育我们今天用的主要理论还是根据英美的,他说他做第四组主任、宣传部长,他也在日本留学过,他比较研究了日本跟美国对新闻事业的两种思想和态度,他觉得确实英美的思想是比较优秀的,所以就大量引进西方的新闻思想和理论。曾虚白、董显光这些人其实贡献很大。马星野主办的党报《中央日报》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时期很有名,叫作“政策的辩论”,就是到底应该“先中央后日报,还是应该先日报后中央”,这是《中央日报》党报两大政策辩论。一开始主张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当然要宣传国民党的政策、国民党的思想、总裁言论,当时提出这个主张的代表人物是陶希圣。陶希圣是《中央日报》董事,马星野是社长,他们两个就是两派,马星野主张“先日报后中央”,你要办报,你要使你这个报纸被读者接受,读者喜欢看你的报,相信你的报,在报纸的公信力建立之后,所登的东西读者才会相信。
苏:陶希圣与马星野的观点刚好相反?
郑:陶希圣是党中央思想的重要管制者,为什么马星野会提出这个呢?那时候想要求变不是很容易的事,他是忠于自己的理想、自己所学和自己的信念。谢然之为什么说日本那套不行,还是美国这套好?他在日本和美国都有留学经历,他对日本奴役台湾50年后遗留下来的问题是高瞻远瞩的。
苏:在我的印象中陶希圣不是学新闻的。
郑:对,他没有学新闻的背景,也不是留学美国的,所以他是传统的党的思想管制者。现在中年学者,都不太了解这一段历史和这些人物,我早期比较幸运的是在马星野身边做了三年多的事情,他在中国大陆办《中央日报》,任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在台湾没有教过一天书,但是我为什么对马星野思想那么了解?我们办了一个“中华民国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他众望所归担任理事长,他提名我做秘书长,后来过了三年,他又提名我和徐佳士做副理事长,我跟了他三年,真正比较了解。谢然之老师,在政大时是我们第一任系主任,后来到文化大学又创办新闻系,我到美国曾多次和他深入的切磋思想。
追求一种对未来的向往
苏:您当时以第一名考上新闻研究所,大学部是第二名考上,请问当时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教学理念是怎样的?像王洪钧、曾虚白,这些前辈是怎样讲述报禁的?提到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是怎样的?
郑:基本上像谢然之老师,还有讲“中国新闻史”的曾虚白老师,他们当时都是党的重要的文宣政策的制定者,尤其是他们在宣传部的角色,在政治上会为党实行的报禁说很多的理由,讲当时不得已的原因,比如“国家”安全。其实,真正影响我思想的反而是他们在谈新闻学概念、西方概念的时候,不露痕迹地让你知道自由民主是会还是不会?新闻自由是会还是不会?意思就是说他也为党的政治来辩护,但是他更让你去追求一种对未来的向往。因为他们预计当时实行报禁的这几个政策,可能慢慢随着时光都会转变,为实行报禁而具备的理由都不是永恒的真理,只是因为当时客观的情况而不得已。
苏:他们在基本的讲法上面还是维护报禁这个政策,但区别是不露痕迹的还是明确新闻自由的这种讲法。他们自己本身认不认同报禁?他们受过现代化的教育,在学校教书,当时的环境是这样,他们公开当然要讲报禁的理由,但是跟同学们私下是什么态度?
郑:在我的印象中,私下很少谈这么敏感的问题,毕竟环境不一样,他们也是要慎重,但是后来特别是王洪钧老师从美国回来,他就比前面几位老师讲得更多。王洪钧写的第一篇文章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叫作《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那时候很多上一代的老人家怪他:你在鼓动青年抢饭碗。
苏:他是有理想性的人。
郑:你去看一看他们过去的文章,不止是对新闻自由的问题,就是对整个“国家”的走向,他们都还是非常有理想的,而且敢讲话。王洪钧是受到胡适之的影响,他做记者时经常访问胡适之,非常有理想。徐佳士老师是第一个翻译西方大众传播理论的学者,他写的那本《大众传播理论》风靡一时,非常深入浅出。这种传播理论里面启发我们人类传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苏:也让我们反思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像您刚才讲的自由和控制是中性的名词,尤其是在大学院校里面看到报禁,其实也是一个中性的名称,应该是用这种态度去看。
郑: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从“蒋公的人”走向“专家”时代
苏:您当时在中央文工会担任副主任,您担任副主任那个阶段还是报禁时期,当局在具体的管控媒体的方式和手段方面有哪些?
郑:我的印象就是我在文工会负责的时候,其实这种演变已经慢慢开始了,过去的宣传主体,像宣传部长、副部长基本都是“总统”最信任的、过去在新闻界任职的人士,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他们几乎都是从哪里来的?秦孝仪、楚崧秋、宋楚瑜,这些人都是新闻秘书出身,他们都是深得蒋公信任的人,专门派他们出来做党营媒体的社长或负责人。我是那个年代在李登辉任内任命的第一批,我在蒋经国时期在青工会是专任委员兼总干事。我在青工会11年,后来才到文工会,从青工会调到文工会的时候我不是李登辉派任的,是李焕派任的。其实客观地讲,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宣传部主管人员的任命开始走向“专家”时代。我一直都是学新闻、教新闻的,不是过去传统那种在“总统”身边做新闻秘书多少年然后任命的人士。我个人的体会是过去文工会对媒体的控制非常厉害,不过报禁还没有解除时,我们对于媒体的管制已经逐步放松了。
说到管控手段和方法还是有好几种:第一个,媒体主要还是党营媒体较多,有八大党营媒体,如中央社、《中央日报》、《中华日报》、“中视”、“中影”等等,而《联合报》、《中国时报》都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所以第一个很简单,就是人治派任,用人治来控制。你看那时候,文工会的副主任都是“中视”总经理,总干事起码也是个副社长。
第二个,新闻协调。重要的事情,文工会约请重要的媒体负责人,咨询新闻界该如何处理?当然他也会邀请很多人做背景调研,关于外交敏感的问题请“外交部长”讲为什么“中美断交”了,背景是什么样的,媒体该怎么把握言论。
第三个,政策传达。党目前对某件重要的事情有什么重要的政策,他要跟这些媒体人士传达,他们回去写社论,配合新闻报道。特别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时间开这种会,比如突发了一个重要事件,通常是电话通知,所以为什么说那个时候总干事不得了,指令就像圣旨一样的,一个总干事打一个电话,总经理、副总经理或者新闻部经理都得按照他的意图去办。
还有一种,那个时候我的理解文工会是真正党的宣传工作方面的主角,“新闻局”其实只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我还记得,那时我是文工会副主任,管新闻这一部分,邵玉铭在“新闻局”做“副局长”,我们常常碰到,我等于是在传达党中央的声音,由他们“新闻局”去计划、执行。但是,事前他们要到文工会来了解,我们曾经一起开过无数次会议。
文工会下面分好几个室,一是管新闻联系的,二是管地方宣传的,三是管文学艺术的,四是管新闻媒体的等等。每一个室都有不同的任务、不同的角色,碰到特定重大事件,比如和美国很紧张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的新闻每天都要注意,每天都要了解,特别是党能够管到的那几个方面更是要重视。
苏:请问在报禁时期,当时的政治领袖对各个媒体有些什么影响或者作为?
郑:那个时候在公权力机关这一部分,包括我们在内,当时很期盼公权力机关做公共关系,那时候的“交通部部长”贺衷寒先生推动很多公关工作,公关界有很多人称贺衷寒为“公关之父”。我在文化大学,创办公共关系专业,台湾第一个广告系是我办的。我们开始认识到政府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包括我们也常常和“新闻局”合作,“新闻局”主办公关人员的训练班,中间一定会邀请了解中央政策的人去讲。“新闻局”讲的大部分是公关技术,我们那边主要倾向于公关政策方面。
所以在政治领袖里面,经国先生据我了解对于新闻界是很接纳的,还是蛮宽容的。我也兼任过英文《中国邮报》副社长,余梦燕做社长,她是报界女强人。期间蒋经国先生就召见过几十位重要媒体的主管,我也去了,蒋先生他也问了很多新闻界对“国家”大事的看法。我还和黄遹霈、余梦燕夫妇去和蒋经国先生谈,据我了解他接见《中国邮报》不一定公开,外面不一定都知道,他也很重视、很尊重新闻界的意见。
当局官员里面有几个人是对新闻操作比较有兴趣的,或者对这方面比较有他的想法,或者说有他的野心的。谢然之老师后来为什么被派出做“驻外大使”?就是被排除出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党部有两个副秘书长秦孝仪和谢然之,他们两个人的专才不一样,兴趣也不一样。秦孝仪对新闻界、新闻媒体非常有贡献、非常重视。他和谢然之二人想涉入的领域也不一样,因为秦孝仪兼做蒋公的新闻秘书,天天在蒋公面前咬耳朵,所以后来把谢然之派出去了,避免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纷争。宋楚瑜当然对新闻媒体这一块软的、硬的用了很多方法,在新闻或宣传这一块,特别是对文工会的影响力还是较大的。
苏:您曾经在《中央日报》和中央通讯社实习过,当时情况如何?
郑:我大学三年级就开始在《中央日报》。那时候《中央日报》一天只出一大张报,我在报社做正式的助理编辑。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去上班吗?那是我一辈子最辛苦的一段日子,晚上12点上班,上到天亮,做国际航空版的助理编辑。《中央日报》国际航空版是专门销到海外的,给留学生、海外华侨看。要等到“国内版”编完了,才开始编辑“国际版”,所以我都是12点去上班,“国内版”的编辑都下班了,我们开始编辑。那是我最辛苦的时候,后来就一直在研究所念完书,我毕业出来跑党政新闻,也跑“行政院”和“内政部”(连震东那时候是“内政部长”),他们很重视《中央日报》,《中央日报》替他们写的东西和报道跟他们很亲近,采访机会也很容易,那时候《中央日报》记者出去采访人家非常欢迎。
时代在变,潮流也在变
苏:您认为是什么促成了报禁开放?请列举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
郑:基本上一方面是国际的压力,一方面是岛内的压力。国际压力方面国际舆论对我们十分的不利,不能否认台湾那几年经济发展做得不错,政治是专制独裁,还实施党禁报禁,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经常给台湾形成相当大的压力;岛内的压力更大也更近,反对运动主要就是针对这些议题,这也是为什么蒋经国会说“时代在变,潮流也在变”。
那时候的秘书长应该还算是保守中的开明派,包括李焕先生,他对新闻界也很同情、很了解,所以他们都有不露痕迹的把海内外的形势给经国先生报告,经国先生也是耳听八方,他也是多方面的听取意见,中间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钱复先生,他在做“驻美代表”的时候,经常把这种“国家”压力、国际舆论反映到经国先生那里,他跟经国先生可以直接讲话,把这种状况直接转告给经国先生,包括党禁年代的“戒严法”,他曾经说:我们真正实行的“戒严法”只有西方国家定义的百分之多少?
苏:百分之三,我记得是这样,我们叫“百分之三的戒严”。
郑:是的,我们要去抗整个这样一个压力,实在不划算。当然这件事情真正暴露出来,是《华盛顿邮报》的社长Graham(Katharine Graham凯瑟琳·葛兰姆)女士到台湾来,蒋经国接受了她的独家访问,钱复与当时的“新闻局局长”张京育负责安排Graham女士的专访。Graham对台湾印象一直不好,《华盛顿邮报》对台湾的态度一直也是不友好、批评的。
苏:您刚提到美国、钱复、美国态度和压力等情况,请问美国那时候的盘算是怎样的?他们对台湾报禁问题的着眼点是什么?
郑:我觉得不一定判断准确,美国这个国家是要向世界推销他的法宝,要你改造成像他一样的国家,你光是经济发展很好但还是独裁,他们就很不满,他们对老蒋从误会到慢慢接受,这中间也经过一个过程,他并不是那么热心在支持你,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所以我相信他还是为美国的理想和利益。我曾经指导过一篇博士论文《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新闻思想的研究》,我到杰斐逊纪念塔去过两次,我收集了杰斐逊的很多资料,他的观点也普遍为美国人所接受,确实有那样的总统,也不完全说是自私的。所以,理想、现实压力、“国家”或个人利益等因素都有。
苏:您认为台湾媒体在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郑:绝对是正面而且非常重要的,过了头的这一部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我对马英九印象不好,我也觉得现在有点过了头了。所以,台湾报禁解除对于台湾民主政治深有影响,民主运动毕竟是全民运动,每一个人民都要有这样的参与才会是真民主。媒体在平常所灌输的自由民主思想慢慢深入到民间,深入到老百姓的心中,培养人民的人格基础。
这次我去厦门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大陆、台湾、香港有几十位学者参加,最后我做闭幕总结发言,我说媒体界也好、行政部门也好,必须知道在媒体角色变化的情况下,尤其是互联网时代,需要注意三点:过去我们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三个基础上,一是权力者,有权的人,特别是皇帝高高在上;第二是贵族阶级,封疆割土,各霸一方;第三个是哲人,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中国人为什么要拼命读书?是要成为一个读书人。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你在这个社会上一辈子不得翻身,你生来什么角色一辈子就是那个角色,甚至于世世代代永世不得翻身,但这三种人毕竟是很少很少的,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太少。
今天的社会结构面临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台湾社会的结构组织(我相信台湾还很少人讲这儿)也是三大基础:第一就是个人的自尊,每个人都很有自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随便侵犯他的权益;第二是彼此的同情,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就马英九和王金平的“关说”事情来说,王金平也有错,但是为什么大家不敢明讲,很多的老百姓觉得马英九在欺负人家,过度的强逼,不顾人情。我并不是说王金平没错,但是我更不同意马英九用这么强势的手段。再比如最近洪仲丘事件,一个阿兵哥,二十几万民众上街支持。所以一个文明现代社会的标杆,就是看这个社会对弱势族群采取什么态度,新女权运动、同性恋者等等,现在我们对待这些跟过去相比有很大的转变,你不要小看小老百姓,他利用网络一通知,马上二十万人上街支持,他又不是为权力为个人,他就是有一种同情心,现代社会集思广益大众的智慧,来发掘最好的解决方法。
新闻自由是谁的自由?
苏:请谈谈解禁后,台湾媒体与当局之间关系有些什么变化?
郑:当然有变化,舆论界因为在报禁之后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对当局的监督和批评更多了,更自由了,更全面了。当局变得有点像个小媳妇,我觉得他们非常左右两难,又不能不尊重新闻界,但是新闻界的批评又不一定全部都是真正客观的,我个人觉得有时候有点过。过去是不够,现在有一部分媒体有点过。主要是新闻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对问题的了解不够深入,现在很多的记者都很年轻,特别是主持有点深度的节目的或者写专栏的,需要对背景有详细的了解,所以在分析问题和观察问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调查和分析。
加上现在民主的流弊,民主有正反两面,正面的就是针对信息管道的公开,确实也是对当局的某些不当措施有一种预警,但是也不是没有偏见的,比如某台它是民进党的,那么无论如何都认为民进党是对的,或者某台是当局的,那么当局的就都是对的,这有失舆论真正的理想。
当然,我们有点理想化,学院派都难免有些理想化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牵扯到专业教育。我做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秘书长的时候,9个院校有新闻传播系,现在有120多个学校有新闻与传播系,新闻传播很时髦,年轻人喜欢,很好招生,但里面的师资、设备特别是办校的重心都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