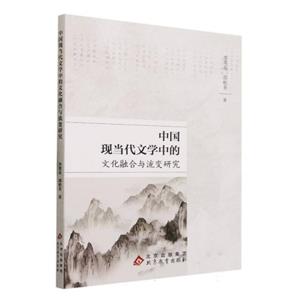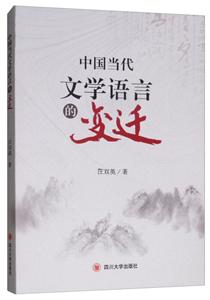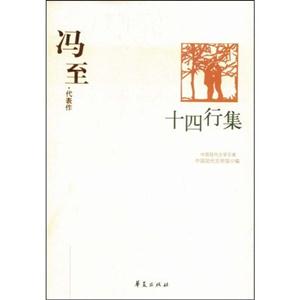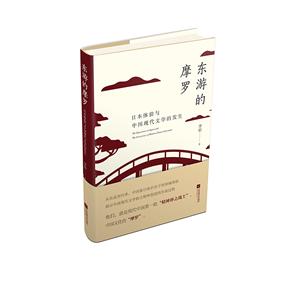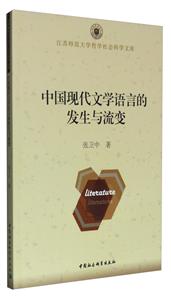
作者:张卫中
页数:248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
ISBN:9787516180136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在20世纪初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在从“五四”至今近一百年的时间中(1917-2015),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经历了发生、发展和走向相对成熟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自成系统,显示了独特的规律;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大后发现代性国家,其文学语言转型也值得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尝试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探讨它的发生、发展与走向相对成熟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走到今天是多种选择的结果,因而也显示了独特面貌。《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拟将时代变革与作家个人的探索结合起来,力求回答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经过百年演变,何以呈现当今面貌的问题。
作者简介
张卫中,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5部。
目录
第一编 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
第一章 “五四”作家语言的转型与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
第一节 鲁迅等作家语言的转型
第二节 郁达夫等作家的语言转型
第三节 叶圣陶等作家的语言转型
第二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作家的语言探索及意义
第一节 语言自身的建设
第二节 新文学的扩展与语言的跟进
第三节 大众语运动与新式白话的推广
第三章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语言的变革及意义
第一节 新的时代导向
第二节 作家生活与创作环境的改变
第三节 解放区本土作家的崛起
第四节 变革的意义
第四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方言问题
第一节 中国早期语言变革中的方言问题
第二节 新文学的方言理论与策略
第三节 新文学作家的方言实践
第二编 新中国成立后30年文学语言的流变
第一章 当代“工农兵”作家语言论
第一节 早期教育与身份认同
第二节 语言政策的引领与导向
第三节 当代工农兵作家的语言形态
第二章 “十七年”作家的语言探索与创新
第一节 语言欧化方面的探求
第二节 语言诗化方面的探求
第三节 口语化方面的探求
第三章 “文革”小说语言的特点
第一节 文学语言的政治化
第二节 文学语言的模式化
第三节 刻板与规范并存
第四章 “十七年”小说的方言问题
第一节 新的语境与新的策略
第二节 方言使用的新特点
第三编 新时期文学语言的流变
第一章 新时期中国小说语言流变论
第一节 艰难的起步
第二节 在借鉴中创新
第三节 转型与提高
第二章 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异与语言差异
第一节 文学观的差异与语言差异
第二节 语言传统的传承与语言差异
第三节 文化背景与语言差异
第三章 新时期小说“新诗性”语言的建构
第一节 语言转型与诗性功能的重建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现代汉语诗性的自觉
第三节 新时期作家对诗性语言的探讨
第四章 新世纪中国小说语言论
第一节 民间语言的使用
第二节 语言的诗化实验
结语
附录 关于赵树理语言研究的审美反思
参考文献
节选
《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 但是这套注音方案公布不久,就发生了“京(音)国(音)”之争。当时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文中批评了用杂合的方式统一国音的主张,他提出应该选取一个地区人群的口语为标准,推广至全国,他认为最适合作为“国语”标准的,就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口语。”①后来,许多人参与了这场讨论。经过五年的讨论,最后,以北京话作为基准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达成共识,在1926年召开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上得到确认。这个会议的《宣言》指出:“(国语)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语言中的一种;……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平的方言……北平的方言就是用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② 20世纪语言变革中,国语运动本来应当取得更大成绩;切音运动开始之初,许多改革者也曾对这场改革寄予厚望,因为在当时看来,中国文字的主要问题就是言文分离,而他们正是要用拼音的方式改变这种状况。按照乐观的想法,中国文字实现拼音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费力不多,但功莫大焉。然而,在实践中却遭遇方言的阻击。因为中国方言众多,汉语书面语一直承担着跨方言交流的任务,中国要在短时间内完全采取拼音文字,同时又保证语言的统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人急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口,让各种方言都拥有自己的拼音文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当时许多人已经指出的,维护一个国家的统一,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各种方言彼此差异很大的情况下,语言的统一几乎全靠书面语维持,因此,任何一种新的书面语都必须具有超方言的功能,而开始被寄予厚望的拼音文字恰恰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实早在晚清关于拼音化的讨论中就已经有人“把包括官话字母在内的切音字皆视为统一国语的障碍。”①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就曾指出:中国“幸而为文字统一之国。若因语言不同,而用拼音以另成一种文字,则既足为汉文之障碍,而所谓官话者又不足以通行,其流弊可知矣。”②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语运动”在演变中呈现了不断走下坡路的过程:切音运动开始之初,改革者自信满满地推出和实施了各种拼音方案,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例如王照的“官话字母”因获袁世凯的支持,曾被列入师范和小学的课程,“于是‘官话字母’传遍十三省。”③但是庚子之后,国语运动的重心在从“言文一致”转向“国语统一”,其势头很快就削减大半,其意义也被大大地削弱了:因为在“言文一致”的追求中,“国语运动”的目标是创制一种新的文字,而后来的“国语统一”则仅仅是为统一“国音”做一些准备,如果说前者是一个事关民族历史走向的大事,那么后者就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技术工作,其意义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国语运动转向之后,早期改革者兴致勃勃创制的拼音文字被剥夺了作为“字”的资格,仅仅成为注音字母。 中国近现代史上另一次语言变革运动,即“五四”白话文运动则要幸运得多,它与国语运动的命运似乎正好形成了对比:国语运动参加的人数众多,历史绵长,在推行过程中曾获得晚清、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官方出面数次举办大型会议,很多名人介入其中,但是最终取得的成果并不显著。而“五四”白话文运动似乎只是胡适、陈独秀登高一呼,很快就响应者云集,也很快就成为中国书面语改革的主要方向;汉语书面语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书面语的走向。 “五四”白话文运动之所以能够“轻易”地在竞争中胜出,取得语言变革的“头功”,最重要原因是它在语言变革上选择了一条“妥协”的路径。在语言变革的原则上,白话文运动的态度是保守的,它不是尝试“文字”的改换,而是着力于“语体”改革,它绕过文字改革这个“难啃的骨头”,通过变文言为白话,解决当时汉语面临的急迫问题,这种方略部分革除了汉语书面语的缺点,却保留了其优点,收取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