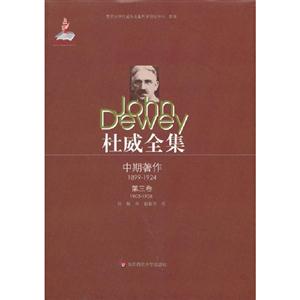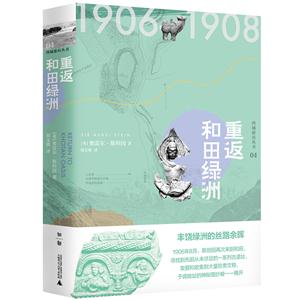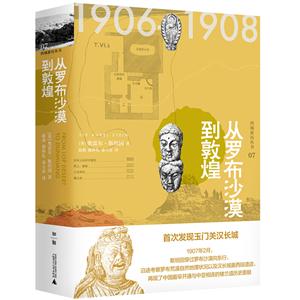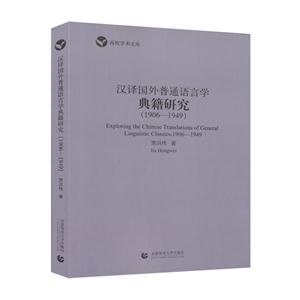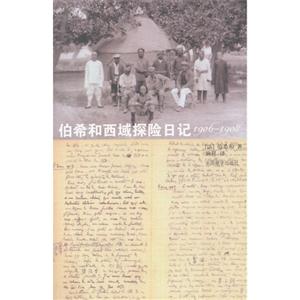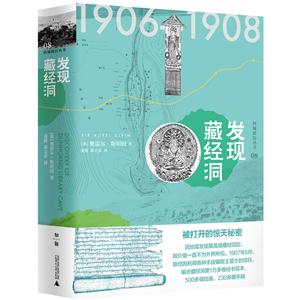
作者:(英)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
页数:306页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59827180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英籍匈牙利人奥雷尔??斯坦因先后到我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考古,并先后出版了这三次探险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三部著作是斯坦因的代表作,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国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窟宝藏与千佛洞佛教艺术,揭开了该地区古代文明面貌和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神秘面纱。西域游历丛书集斯坦因这三次中国西部探险考古资料于一体,对上述考古报告进行整合修订,使大众能更便捷了解其中的经过和成果。丛书共15册,本册出自《西域考古图记》:因地震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其价值一直不为外界所知。1907 年 5 月,斯坦因利用各种手段,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骗走了藏经洞里 1 万多卷经书写本,500多幅绘画,230 多捆手稿。
作者简介
奥雷尔·斯坦因(1862—1943),英国人,原籍匈牙利,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者。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三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考古探险。根据其考古探险经过及成果,先后撰写出版了《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姜波,博士,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论文《豆卢氏世系及其汉化》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专著《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出版《西域考古图记》等译著(合著)等。秦立彦,出版译著《西域考古图记》(合著)等。
目录
第一章 千佛洞
第一节 遗址概述 ………………………………………………………………….1
第二节 千佛洞的碑刻 ………………………………………………………..26
第三节 王道士和藏经洞 …………………………………………………….30
第二章 发现藏经洞
第一节 密室的开启 …………………………………………………………….41
第二节 藏经洞里的多种语言文书 ……………………………………57
第三节 密室藏经和艺术品的获取 ……………………………………69
第四节 后来对藏经洞的调查 …………………………………………….84
第三章 千佛洞的绘画
第一节 绘画的发现和研究过程 ………………………………………..92
第二节 绘画的时间和环境 ………………………………………………101
第三节 画的结构、材料和工艺 ………………………………………116
第四节 佛传故事幢幡 ………………………………………………………134
第五节 佛和菩萨 ………………………………………………………………153
第六节 天王和金刚 …………………………………………………………..175
第七节 成组的神祇 …………………………………………………………..187
第八节 佛教净土画 …………………………………………………………..200
第四章 千佛洞的织物和写卷
第一节 装饰性织物:起源、用途和工艺 ………………………214
第二节 织物中的中国风格图案 ………………………………………230
第三节 萨珊风格的图案及其仿制品 ………………………………242
第四节 藏经洞中发现的婆罗米文和汉文写卷 ………………255
第五节 藏文、粟特文、突厥文写卷 ………………………………267
第六节 一些千佛洞石窟的装饰艺术 ………………………………279
节选
第三节 王道士和藏经洞 3月,我曾匆匆造访过千佛洞,这里有关佛教艺术的丰富资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我更大的目的不全在于此。
扎希德伯克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土耳其商人,他当时被从新疆驱逐到敦煌,成为当地一小群穆斯林商人的头目。我正是从扎希德伯克那里获悉藏经洞里偶然发现了大批古代写卷的消息。这批无价之宝据称当时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扎希德伯克宣称这批写卷中还有不是用汉文书写的材料,这更激起了我想探个究竟的欲望。经过蒋师爷一连串急切的追问,证实这个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于是我俩作了周密审慎的计划,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去获取这批写卷。
我刚到千佛洞时,王道士正好同他的两个助手外出化缘去了。如果这时候将我们的计划付诸实施显然不明智。幸好留下来看守的那个年轻的唐古忒和尚知道一些情况,蒋师爷没费多大劲就从他嘴里套出了一些有用的内情。据他说,藏经发现于一个大型的洞窟里,洞窟编号为 Ch.I。这个洞窟靠近北组(主组)洞窟的最北端,外部建筑粉刷一新,这是王道士新近主持对它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缮。他来这里已差不多有 7年了。通向洞窟的入口已被崩落的岩体和流沙所挡住,这与靠南一些的山脚崖面上的洞窟的情形一样。当年在对洞窟和窟前地面(现在已为殿堂所占)进行整修时,工匠在连接两个洞室的走廊壁面上发现了一条裂痕,挑开裂缝便从这堵土墙之后发现了一个凿在岩石里的密室(图 6),图 20是该洞窟的平面图。
据称,打开密室时,里面塞满了用汉文书写的但是读不通的大量经卷,其数量之多,可以装满几辆马车。石室发现经卷的消息传到了距敦煌很远的兰州,当地长官曾命令送些样本去。最终,甘肃省府下了一道命令,命令所有写卷就地封存。所以,这批不曾被读懂的藏经重又被封存在发现它们的石室里,由王道士负责妥善保管。
由于王道士不在,我们无法得到更多的关于藏经洞的情况。但我还是抽出时间对藏经洞所在的地点作了观察。年轻和尚的师傅是一个西藏来的和尚,当时也出去化缘了。后者的临时住处是一间破旧的小屋,本是供前来敦煌朝圣者们居住的地方。他曾借得一个卷子,放在他的陋室里,以添得些风光。蒋师爷说服这个年轻和尚将他师傅处的那个卷子拿来看看。这是一个保存很好的卷本,直径约 10英寸,展开来的长度足有 15码。卷纸呈淡黄色,看上去很新,也很坚韧。由于这里气候干燥,经卷又是被精心封存在密室里,所以很难从纸的外观来判断它的年代,不过,从那细密的纸纹和磨得溜光的纸面还是可以看出它的年代相当久远。
这个卷子字迹清晰,书法秀美,这是我和蒋师爷共同的印象。卷子上的文字确确实实是汉文,尽管蒋师爷很有学识,他也不得不坦承,乍一看,连他也断不清句子。但不久我就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从蒋师爷不断地读到“菩萨”和“波罗蜜”这一类的固定术语,我判断出它就是中国佛界所熟知的、由梵文转译过来的《菩萨经》和《波罗蜜经》。由于佛教经文的字面意思晦涩难懂,因此包括蒋师爷在内,此前从没有人认出展现在面前的卷子就是一部佛经。对这个卷子作了初步鉴定以后,可以认定密室所藏写卷主要的应该是佛经。宋代活字印刷术出现以后,中国的书多装订成册,就像今天所见的书一样。这份经书是写在一个长长的卷子上,而不是被装订成册(原著用了“ concertina”一词,直译为“像手风琴一样能折叠的”——译者),这就说明它的时代应该很久远。
有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着去被发现的念头,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我重返千佛洞。但等到真的回到这里时,我不得不开始为我的计划担心起来,因为我从当地得到可靠的消息,保护着这批珍宝的王道士是一个恪尽职守、非常用心的人。藏经洞所在的那个寺宇看上去有些破旧,但它仍是当地人朝拜的一个圣地,容不得有任何的粗鲁举动,这也使我的考古工作受到影响。精明能干的蒋师爷收集到了有关看守藏经洞的和尚的性格和举止的情况,这更使我感到有必要在开始时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蒋师爷设法说服王道士等待我的到来,而不是在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一结束就开始去募集修庙的资财。值得称幸的是,由于敦煌副县长汪大老爷对我所进行的考古工作感兴趣,我逐渐博得了敦煌当地人的好感,我可以利用我学者的身份,使当地人对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5月 21日,我重返敦煌石窟,准备将我早已拟好的计划付诸实施。让我感到满意的是,除了王道士和他的两个助手以及一个身份卑贱的西藏喇嘛(他不懂汉文,所以对我的计划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整个遗址别无他人,一片荒凉,仿佛是一个被人们忘却了的地方。王道士等候在那里欢迎我的到来,在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感到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图 21)。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为了避免与他待在一起的时间过长,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对几个主要的洞窟进行考察,并对一些较为重要的壁画进行拍照,以此来掩饰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当我来到最北端的洞窟时,我瞟了一眼藏经洞的入口,那里就是发现大批藏经的地方,经卷至今还封存在里面(图 6)。藏经洞正好位于王道士改造的那个洞窟的旁边。藏经洞密室的入口比走廊的地面要高出 5英尺,让我感到一丝不安的是,我发现窄小的密室入口已被砖墙堵住,仿佛就是为了故意与我为难似的。
我的第一步主要目标是想看一下全部经卷的原始堆积、存放的情况。王道士住在另一个稍加整修过的洞窟里,为了设法让他同意我们的请求,我特地派蒋师爷到他的住处同他进行交涉。尽管蒋师爷费尽心机,但谈判的进展还是非常缓慢。在我们答应给王道士修缮庙宇进行捐助以后,他终于说出封堵密室入口的目的本是为了防范香客们的好奇心。最近几年,每到朝拜的时候,前来朝拜的香客往往数以千计,把整个遗址挤得水泄不通。但是,由于对我们心存疑忌,他始终不答应我们看一下全部经卷保存状况的请求。他唯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许多限制条件。蒋师爷急于想替我要到其中的一两份卷子,结果使得王道士很是心烦,我们的全盘计划一下子面临告吹的危险。
但谈判还是有一些收获。我们在敦煌听说的一些情况,从谈判过程中得到了肯定。当密室发现经卷的消息由肃州道台呈报甘肃省府时,省府衙门曾命令送一部分卷子去省府,后来又下令妥善保管所有卷子。蒋师爷怕王道士终止谈判的忧虑,被王道士流露出来的对官府上述做法不满的口气打消了。据王道士说,他确曾向兰州省府衙门送去一批佛经,但官府对此不感兴趣。官府甚至没有对这批卷子如何处置作出任何安排,也没有对他辛辛苦苦修缮庙宇而发现这批经卷的功劳进行褒奖,这使王道士感到有点愤愤不平,他对我们毫不掩饰自己当时的感受。当时官府甚至下了一纸粗暴的命令,要将这批经卷装满 7辆马车运走,后来由于运费不够,又嫌保管麻烦而作罢,于是又将这批经卷原封不动地交付给王道士,令他就地保管。
蒋师爷的报告使我感觉到,王道士的古怪性格将是我实现计划的最大障碍。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感情,或使他担心众怒难犯,或两者兼备。我觉得最好是先了解一下王道士的为人。于是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我郑重地登门拜访王道士,请求他让我们参观一下他所修复的庙宇。自从他 8年前来到敦煌,这便成了他的主要任务和精神支柱。所以,我的请求被王道士欣然接受。
他领着我们走过洞窟的前廊和高大的砖木结构殿堂,这里的建筑雕梁画栋、溢彩流光,我用预先想好的词语对它们进行恭维。当我们穿过藏经洞前的过道时,我实在忍不住藏经洞的诱惑,它就位于右侧最外面的位置,入口被一堵粗陋的砖墙挡住。我没有直接去问我们虔诚的向导藏经洞里有些什么,而是投其所好去询问他是如何整修这个洞窟,他曾虔诚地干着这项工作,我想这样做更能博得他的好感。从图 6中可以看出洞窟中雕刻的修复情形。这个洞窟中,有一个长约 56英尺、宽约 46英尺的马蹄形坛座,坛座很旧,但已经重新粉饰,上面排列着一群新做成的泥像,都和真人差不多大小,依我看它们比起这些洞窟中其他的塑像要笨拙逊色许多。
这个洞窟里的壁画相对而言则要优美得多,而且大多保存较好。墙壁上所绘的主要是大方格里的坐佛形象,窟顶则是模印花样。虽然这里的壁画比不上其他大型洞窟的精美,但也足以使里面的塑像和其他后期修复增补的东西显得粗俗而逊色许多。不过王道士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这个洞窟的修复工作和他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仍可称得上是费尽心机。
大约在 8年前,他从陕西只身来到这里,举目无亲。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当时,坍塌的物什堆满了地面,几乎堵住了通往洞窟的通道。其余的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流沙,洞窟也被流沙覆盖了很大一部分。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一想起这些,我心中不禁有一丝感动。在这座大殿的旁边,还有几层砖木结构的殿堂建筑,向上一直攀升到崖顶的位置。后来他还曾非常自豪地向蒋师爷展示过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每一笔都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毫。这些与蒋师爷在敦煌打听到的情况完全相符。
王道士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无知很快就被蒋师爷摸清了。我与一些有学识的中国官员交往时,往往能博得他们的支持和好感,但对王道士而言,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给他谈论考古学的价值、去给他谈论利用第一手的材料进行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意义等。但有一点值得与他进行探讨,那就是玄奘。在中国,只要一谈起玄奘,对方无论是学者还是白丁,我总是能与他谈得很是投机。这位古怪的王道士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虔诚、无知而又很执着。他使人不得不联想到中国古代的那位克服千难万苦赴印度取经的朝圣者,王道士头脑简单,信仰却很执着甚而至于有点迷信。唐玄奘一直被我当作我的中国保护神,王道士也喜欢听我谈论他。
于是,在周围满是佛教神像的氛围里,我开始向王道士谈起我对玄奘的崇拜:我是如何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又是如何去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等等。
尽管我的汉语很差,但这是一个我所熟悉的演讲题材,而且一旁往往还有蒋师爷适时的补充,所以我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他从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和我一样,对玄奘顶礼膜拜。有了这个共同点,我对自己的计划就更有信心了。他带着我们走到大殿前面的凉廊上,向我们炫耀那些描绘玄奘西行景色的壁画,这些画像都是他请一个当地画工画到墙上的。壁画上描绘的奇异的传说,正好是那些把唐僧神化了的内容。尽管这些故事都不曾见于《大唐西域记》,但我还是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导游”口若悬河地谈论墙上方格里所绘的神话故事。其中有一幅画面的寓意很是深刻,我费了很大工夫才看明白。 画面所描述的情形与我当时的处境正相类似。画面上,玄奘站在一处急流前,旁边是他的忠实的坐骑,满载着经卷。一只巨大的乌龟正向他游过来,准备驮他渡过这一“劫”。这里所描绘的正是这位朝圣者满载着 20捆佛经准备从印度返回中国时的情形。摆在他前面的困难将是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这些都在他的游记中作过描绘。不知道我身边的王道士是否能够理解这画中的情节,让我把这些古代经卷重又取回印度,这批经卷正由命运之神交付给他保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