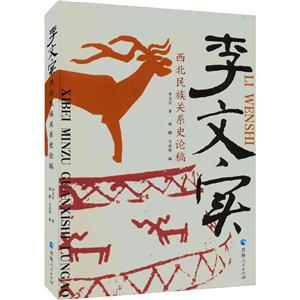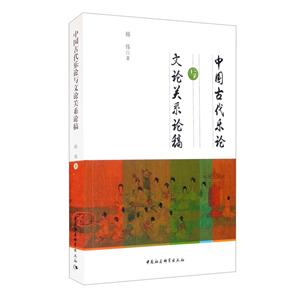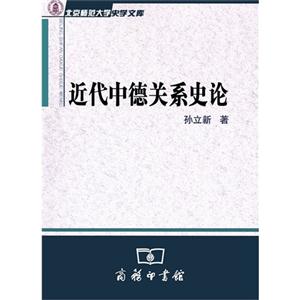作者:庄永平著;方立平丛书主编
页数:320页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7
ISBN:9787542650528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包括: 通论 ; 《诗经》《楚辞》中的腔词关系 ; 汉魏“乐府体”中的腔词关系 ; 唐歌诗体中的腔词关系 ; 宋唱词体中的腔词关系 ; 元、明度曲体 (曲牌体) 中的腔词关系等。
作者简介
庄永平,音乐学家。1945年生,上海市人。早年任上海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员,1965年入上海京剧院《海港》剧组参加京剧现代戏创作演出,1988年起入上海艺术研究所从事戏曲音乐、民族音乐研究。出版有《戏曲音乐史概述》、《京剧唱腔音乐研究》、《琵琶手册》、《音乐词曲关系史》、《琵琶·古谱·戏曲音乐研究——庄永平音乐文集》等专著;《京剧唱腔赏析》、《沪剧唱腔赏析》、《评弹唱腔赏析》、《青少年学琵琶》、《每日必弹——琵琶指能练习曲》、《图说琵琶》以及自传体回忆录《海上散谈录一个国乐家半个世纪的亲历》、《丝竹情怀,二胡情深——周皓演奏艺术生涯》等著作20余部。撰写有《上海艺术史·音乐史》、《上海百年文化史·音乐史》、《上海当代艺术图典·音乐》、《上海京剧志·音乐》、《京剧词典·音乐》等。主编中国首部《中国音乐主题辞典·器乐卷》;参加《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上海卷》编辑。另外,在各音乐院校学报上发表论文近二百篇,主要部分收录在《庄永平音乐文集》中。多年来尤其注重对隋唐燕乐与古谱学的研究,全译了《敦煌乐谱》、《五弦谱》、《三五要录》等古谱,并在燕乐理论方面有所新解。
本书特色
文学与音乐他们原本各有自己本体的发展领域。当然,在远古时,诗、歌、舞是三位一体的,后来才分化为三种不同门类的文学与艺术。但是,在声腔形式中,文学唱词与腔调音乐始终是一体的,他们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这种特殊的关系常常也反过来促进和影响了他们各自发展的进程。
目录
第一章通论
第一节唱词句型和腔调的关系
一、整齐句型
二、长短句型
第二节字位节奏关系的安排
第三节唱词四声平仄和腔调的关系
一、调
二、声与韵
第二章《诗经》《楚辞》中的腔词关系
第一节远古语言与音乐产生及声腔之发端
第二节《诗经》中的腔词关系
一、《诗经》的句型
二、《诗经》的曲式
第三节《楚辞》中的腔词关系
第四节疏“乱”
第五节《成相篇》的节律
第三章汉魏“乐府体”中的腔词关系
第一节乐府体制与腔词关系
第二节“相和歌”的曲式结构
第三节释“解”
第四节考“拍”
第五节音韵学的创立
第四章唐歌诗体中的腔词关系
第一节歌诗体中的一般腔词关系
第二节析“叠”与“遍”
第三节诗拍的形成与特点
第四节《敦煌乐谱》词曲组合
一、《又慢曲子西江月》
二、《又慢曲子伊州》与《伊州》
三、《水鼓子》
四、《倾杯乐》
第五节《阳关三叠》与《何满子》词曲组合
第五章宋唱词体中的腔词关系
第一节燕乐兴起与词的形成
第二节论“填词”
第三节词的四声与曲调
第四节词的文体结构
第五节词拍的形成与特点
第六节词的曲式
一、令、引(近)、慢
二、三台、序子
三、法曲、大曲
四、缠令、诸宫调
五、“折、掣”等符号析
第七节姜白石创作歌曲词调
第八节词调体腔词关系实例详解
第九节说唱体中的腔词关系
一、说唱音乐的成熟
二、说唱音乐腔词关系实例详解
第六章元明度曲体(曲牌体)中的腔词关系
第一节元杂剧中的腔词关系
一、《中原音韵》与新四声系统
二、元杂剧(曲)旋律节拍特点
三、元杂剧(曲)的曲式
第二节明南北曲中的腔词关系
一、南北曲的用韵与腔词关系
二、南北曲的唱腔节拍特点
三、论曲牌体式
四、曲牌体腔词关系实例详解
第七章明、清板腔体与民歌小调中的腔词关系
第一节明、清板腔体中的腔词关系
一、方言声调与曲调
二、京剧的用韵与声调特点
三、字位节奏关系与节拍特征
四、论板腔体式
五、板腔体腔词关系实例详解
第二节明、清民歌小调中的腔调关系
一、号子、山歌
二、小调
三、民歌腔词关系实例详解
引用谱列索引
参考文献
后记
节选
朱光潜在论及中国诗何以走上“律”之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乐府衰亡以后,诗转入有词而无调的时期,在词调并立以前,诗的音乐在调上见出;词既离调以后,诗的音乐要在词的文字本身见出。”首先,我们知道文学诗歌与腔调音乐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姐妹艺术,虽然在早期它们在运用上结合得较为紧密,但是,毕竟它们各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就是在今天的声腔音乐中仍是如此。正如笔者在《绪论》中所引刘尧民的话:“要想把诗歌竭力去融合音乐反映音乐,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因为语言与音乐毕竟是两回事,语言四声调值与音乐五音也是不能真正对应的,更何况当时外来音乐还不止用到五声。问题是否像朱说的那样,因为做不到而转而求其次,倒过来反而促使诗歌唱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呢?如果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看来未必恰当,也不甚科学。任半塘认为:“文字读音之声律,绝不得阑入真音乐范围。……此末期之诗,主文之程度益高,益为雕饰,乃音与义之更分化。”因而,任氏认为朱是将音乐之音与语言之音相牵混所致。因为诗歌有诗歌自身发展道路,虽然由于汉语声调具有音乐方面的因素,比起印欧语系来与音乐纵向关系上要密切些。但是,反过来看,正是汉语有这种音乐因素,它必然会利用这种因素并把它发展利用到好。我们知道,汉语由于以单音节为多,自古以来人们就发现了双声、叠韵在诗歌运用中的妙处。例如,在《诗经》中就大量存在这种双声、叠韵现象,而且对“韵”的认识和运用似乎比“声”要更早些。但是,由于那时的句子还很短小,像《诗经》常是以四字句为主的。而四字句仅为两两词组,其声、韵的对比较直接变化不多。后来随着句子的放长,各词组之间就存在运用上如何对比与平衡的问题,这就促使句子内部并累及到外部,产生诸如平仄、对仗等格律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