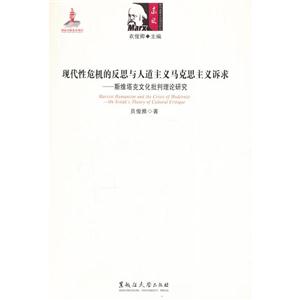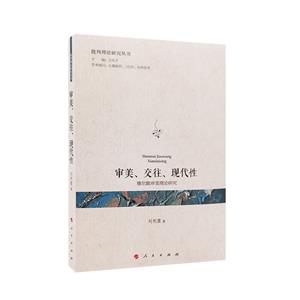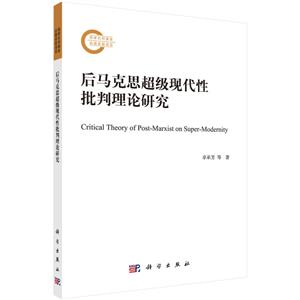
作者:卓承芳//胡大平
页数:226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030681805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试图以”不错现代性”这个新颖的视角来阐明鲍德里亚、鲍曼和维希留三位在当代具有重大影响的激进左派理论家之现代性批判思想及其马克思的关系。他们三者代表了当代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潮–即试图通过批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发展出比其更激进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潮–之独特的深度。在整体上,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陷入了以特别现象为标志的不错现代性阶段而不是自我修复的后现代阶段,并因此坚持比含糊的后现代思潮更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在其中,鲍德里亚通过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变化将”拟真”作为当代社会结构规律,鲍曼发展马克思的创造性破坏观点而提出”液化现代性”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维希留从技术转换到”速度-相对性”问题,试图以速度政治学来阐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虚无化,这些问题正是今天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创新、商品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所带来的不同层面的生存威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与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试图发展替代马克思的框架而把现代性批判这个事业推向深入。这些理论指出,在今天不错现代性语境中,速度改变了现实感,传统意义上稳定而真实的感觉不再可能(维希留);流动性摧毁了人类感只剩下实际以私人利益为核心的个人(鲍曼);仿真导致意义的丧失(鲍德里亚)。秩序的丧失、稳定性的消解、真实性的坍塌,正是我们在今天直接遭遇的现代性之结构问题。尽管这些后马克思理论家关于时代的诊断及其提供的药方并不接近获得我们的认同,但他们确实比那些试图改造观念的文化左派对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后马克思超级现代性批判理论家的意谓 1
第二节 当代激进左翼思潮的后马克思语境 3
第三节 从后现代到超级现代性 8
第四节 从超级现代性叙事看后马克思姿态 21
第二章 超现实与世界荒漠——鲍德里亚的荒诞玄学 38
第一节 鲍德里亚与后马克思语境 39
第二节 符号与生产逻辑的崩溃 49
第三节 世界的超现实化与致命的策略 53
第三章 液化现代性与存在的战栗——鲍曼的写作社会学 64
第一节 鲍曼与后马克思激进思潮现代性批判 64
第二节 现代性之矛盾性及其液化 72
第三节 恐惧或存在的战栗 89
第四章 后勤现代性与速度虚无主义——维希留的速度学 102
第一节 维希留的速度政治学与后马克思思潮 103
第二节 速度与后勤现代性 109
第三节 速度空间及其虚无主义危险 118
第四节 社会批判理论本体论视域深化 131
第五章 超级现代性与政治——不确定时代的激进想象 145
第一节 作为理论革命的荒诞玄学 145
第二节 后现代共同体伦理与新乌托邦议程 160
第三节 超级现代性与后解放政治美学 177
第六章 超级现代性语境与后马克思思潮的反思 186
第一节 认真对待超级现代性 187
第二节 西方激进政治学之政治难题的反思 197
第三节 重申超级现代性语境下的解放政治学 208
参考文献 223
节选
第一章 导论 本书是对鲍德里亚(1929—2007,也可译为波德里亚、博德里亚尔、布希亚)、鲍曼(1925—2017)和维希留(1932—2018,也可译为维利里奥)三位激进左派理论家的解读。对于国内学者来说,他们对鲍曼和鲍德里亚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他们的理论已经构成社会理论的中心话题。对于国内学者来说,维希留可能相对陌生一点,但随着其著作中译进程的加速,其理论也会逐步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热点。①也正是因为速度在今天的重要性,他被视为“20世纪晚期出现的最具原创性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②,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影响力将超过福柯、鲍德里亚等而成为21世纪的思想领军人物。③本书将他们作为后马克思超级现代性批判理论家以阐明其在当代激进思想版图中的独最地位。 第一节 后马克思超级现代性批判理论家的意谓 笔者将这三位性格和言说方式迵异的思想大家放在一起,坦率地说,对读者而言是一次具有挑战性的阅读之旅,但也是一次值得的冒险。在表面上,三个人的写作——鲍德里亚称自己的理论是“荒诞玄学”,鲍曼以“写作社会学”来定义自己,而维希留的理论则可称为“奇幻批评”,他们采取的都不是传统论证的方式,而是以散文体表现出来的预言式批评甚至萨满师式预言的方式,很难用某一标准将他们装到同一个抽屉里。不过,如果深入了解他们论述的问题和逻辑,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深刻的相似性。他们都是深受法国1968年政治风潮影响的思想家,现代性批判构成其中心议题。在现代性批判中,社会关系和人类生存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他们关注的核心。“拟真”“流动性”“速度”这三个关键词既表明他们对社会存在的不确定性之共识,又表明他们分析的视角存在差异。鲍德里亚将“拟真”作为当代社会结构的规律。在维希留那里,“速度-相对性”乃是叙事中轴。鲍曼则以“液化-不确定性”机制来解释现代性的变化。这三种不同的视角,都不同于注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倾向于将当代理解为超级现代性,即现代性的极端状态。因此,我们看到,作为左翼激进学者,三人的理论主张与受结构主义影响、大谈身份政治学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后现代知识左派大相径庭(其中,鲍曼更是直接对身份政治学和文化多元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们关注的是威胁人类和文明的“超真实”和“致命的策略”(鲍德里亚)、“液化的恐惧”(鲍曼),以及“技术意外”和“速度虚无主义”(维希留)。这些问题正是今天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创新、商品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给人类带来的不同层面的生存威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与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试图发展替代马克思的理论框架而把现代性批判推向深入。我们看到,在逻辑上,拟真作为价值之结构规律乃是对价值的市场规律的替代,“液化”乃是对“气化”的发挥,“速度”乃是“财富-权力”的等价形式。实际上,三者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推向前进,这也意味着,在他们的理论中都假设了马克思的分析“落伍于”时代发展。鲍德里亚针对的是以生产为出发点的价值形式所做的分析;鲍曼谈论的是与工厂时代沉重的现代性不一样的以后福特制(post-fordism)为代表的“轻盈”现代性;维希留强调的是财富-权力背后的速度。当然,虽然三者都是在后马克思逻辑上建构自己理论的,但他们的“后马克思”态度却有明显不同,即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了三种不同的关系。鲍德里亚尖锐地提出,要告别马克思,同时指出生产主义乃是维系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代表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走之后最激烈地打出后马克思旗帜的新激进主义。维希留试图把政治经济学升级为速度政治经济学,但他并不纠缠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另起炉灶去回应时代问题,他代表了那些处在马克思历史效应之中的新激进主义;鲍曼并没有直接批评马克思主义,甚至到最后都强调马克思分析对当代的意义,他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立场的批判理论。在整体上,他们都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变化,批判理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以及批判理论自身的困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他们作为典型来观察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特别的价值。 他们不同于那些以“后现代主义”名义告别马克思主义的新激进主义思潮(以利奥塔为代表),也不同于以“后马克思主义”名义告别马克思主义但仍然试图占据左派政治焦点的假激进思潮(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他们只是试图完成马克思并没有完成的现代性批判,在他们看来,发展到今天,现代性本身过度化或极端化了。他们的中心任务都是为诊断这种极端化了的现代性提供一种理论,即提出超现实、液化现代性、速度政权等理论。这些理论不同于超级现代性理论。由此,我们也看到他们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种独最价值,即揭示我们时代不断极端化的原因及其后果。他们指出,在今天超级现代性语境中,仿真导致意义的丧失(鲍德里亚);流动性摧毁了人类感而只剩下实际以私人利益为核心的个人(鲍曼);速度改变了现实感,传统意义上稳定而真实的感觉不再可能(维希留)。真实性的坍塌、稳定性的消解以及秩序的丧失,正是我们在今天直接遭遇的现代性之结构问题。尽管这些后马克思理论家关于时代的诊断及其提供的药方(鲍德里亚的理论恐怖主义、鲍曼的伦理呼吁以及维希留的预示录式批判)并不完全获得我们的认同,但他们确实比那些试图改造观念的文化左派对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具有更大的启示意义。在我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要在新时代实现自己的华丽升级,就必须给出对这些问题的有说服力的回答。 第二节 当代激进左翼思潮的后马克思语境 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第二国际到卢卡奇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今天,和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激进主义思潮经历了多次代际转型。如果不厘清这种转型,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不断加快与复杂化的代际转型(这就像与我们生活中的代际特征差异一样,似乎“代”的持续时间越来越短),要准确地判断和定位今天五花八门的激进主义理论或左派理论,将是十分困难的。这是因为,在这其中,既有哈维这样越老越“革命”的学院左派,也有齐泽克这种似乎横空出世的明星激进思想家,以及巴迪欧这样被重新发现的“老运动员”,又出现了皮凯蒂这样“返祖”(蒲鲁东派)的年轻新锐。在今天西方左翼思想界“众声喧哗”的格局中,要分门别类地鉴别就需要把各种关系都搞明白,没有思想史的位置参照是不行的。 然而,要恰当地对1968年的激进思潮进行逻辑上的断代,同样是十分困难的。这并非因为表面上的多样性,而是因为如下原因:1968年政治风潮耕犁后翻开的土壤,已经不再是滋养卢卡奇、萨特、霍克海默那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土壤了,无论是像鲍德里亚、鲍曼和维希留这些人因为年龄曾经受惠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像齐泽克这些从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出走的新星,抑或是那些在全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锐们,都注定要开辟自己的事业。如果从思想逻辑角度来说,宏观上,后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新的激进语境。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千年之交,有学者梳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状况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如今,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已经根深蒂固的理论立场。”④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潮,后马克思主义源自拉克劳和墨菲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该书明确地阐明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左派政治认识论。在某种意义上,就如20世纪初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那样,该书试图剔除占据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寻找新的理论根据,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内涵及其实现战略。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理论探讨(尽管拉克劳和墨菲具有社会活动的背景),而后者则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争论。与后者激起第二国际内部广泛的政治辩论和斗争一样,前者也很快引起了英国左派学者的内部争论并扩散到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成为全球性的理论事件。⑤ 在我们看来,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一语具有独最的内涵,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件只是以尖锐的形式挑明了西方激进主义隐藏的一个潜意识:我们处在后马克思的历史语境中。在某种意义上,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只是公开宣布经过1968年法国政治风潮洗礼之后的西方左翼激进学者告别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众所周知,1968年法国政治风潮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来说,乃是一道分水岭。这是因为,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法国学生造反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以阿多诺为典型代表、持传统人本主义立场的主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不支持学生的造反行为,以巴特等为代表,正如后来流传的“结构不上街”这个口号表明的,作为新锐的结构主义理论家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此,1968年政治风潮结束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进入并不活跃的转型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结构主义思潮意外地在美国的部分大学中得到广泛传播,但包括后来被捧上天的“解构”教主德里达等在内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在法国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除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5年),引起人们兴趣的多数仍然是在1968年之前的法国理论作品,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德国批判理论则早通过《合法化危机》(1973年)宣布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简言之,解构主义思潮不仅与关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而且通过强化这一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之外寻求或重建社会理论,形成了新的激进理论动态。例如,从列斐伏尔及其弟子所构建的理论来看,这是十分明显的。鲍德里亚和卡斯特都是列斐伏尔的授业弟子,都受其“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这一思想影响,而把消费社会批判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并表现出激进的特征。然而,他们在起点上都告别了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转向对马克思的“超越”。其中,鲍德里亚出版的《消费社会》受巴特符号学影响,在马克思之外建构了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其结果便是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年)中公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而卡斯特则受另一位导师阿兰?图雷纳的影响,在其成名作《城市问题》中试图从消费领域寻找后工业社会的改良之路,虽然该书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兴起的三部代表作,但其实际逻辑却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的。“学二代”与他们的导师之间的距离就这样鲜明地凸显出来了。鲍德里亚和卡斯特都是非常重要的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与工业文明早期社会现实保持了一致的逻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如阿兰?图雷纳和丹尼尔?贝尔等声称)。在这一语境下,不经反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如马尔库塞批评的科学技术崇拜,以及后来多数左翼学者都与之保持距离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因此需要在理论上另起炉灶,通过比马克思站得更高来实现马克思追求的启蒙规划。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如此,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和价值生产理论也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现实也使得传统的启蒙规划陷入黯淡,这使得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政治上出现了多条告别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如哈贝马斯虽然坚守“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划”,但通过交往行为理论而与主流思潮达成和解并因此成为主流哲学家,而鲍德里亚则走上彻底的不合作道路,走向他自己所称的作为“理论上的恐怖主义”的荒诞玄学。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拉克劳和默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在日益走向中心的英语激进理论界中,通过对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道路的审理,从而为这种理论动态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证。他们之所以引发广泛的争论,并非他们理论中的深刻性,而是他们的立场。正如西姆所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苏东剧变后,在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激进左派理论。 上述势态也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张一兵教授带领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在2000年前后率先提出重新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试图将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新的动向理论化。⑥张一兵教授的研究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反响,也引发了诸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划分和评价等众多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