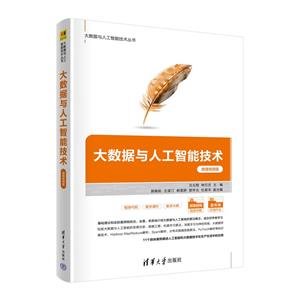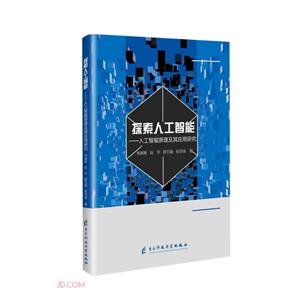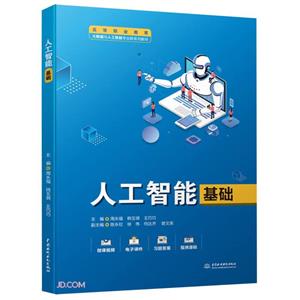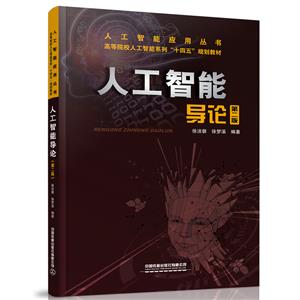作者:杨庆峰
页数:265
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6714001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对1960年代以来记忆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状况展开研究,概括出其总体逻辑、转向逻辑和进化逻辑,并进一步对记忆研究的基本问题,如记忆的本质、记忆行为、记忆内容和记忆主体等问题进行哲学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记忆研究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哲学构建的意义。除前言和结语外,总共包括八章,论述了记忆现象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意义,作者指出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将记忆与智能的关系进一步提出来。成像技术导致了记忆研究的推进,与心理学、生物学一起成为记忆研究的核心。书稿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章。
作者简介
杨庆峰,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曾任上海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访问学者(2013-2014)、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访问学者(2017)。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CCF职业伦理和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技术哲学、记忆哲学、数据伦理与人工智能伦理等。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江海学刊》《南京社会科学》《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及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有《技术现象学初探》(2005)、《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体验》(2011)、《翱翔的信天翁: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研究》(2015)等专著及《创新系统的治理》(2011)、《将技术道德化:理解与设计物的道德》(合译)等译著。
目录
第一章 被当代现象学轻视的记忆问题
第一节 心理学对记忆现象的直接关注
第二节 现象学家对记忆问题的间接关注
第三节 后现象学对记忆的错失
第二章 当代记忆研究的复兴
第三章 当代记忆研究的多重逻辑
第一节 记忆研究的总体逻辑
第二节 记忆研究的转向逻辑
第三节 记忆研究的进化逻辑
第四章 当代记忆研究的技术与方法
第一节 记忆研究三剑客
第二节 记忆研究技术演变
第三节 记忆研究的方法
第五章 当代记忆研究中的心理主义
第六章 当代记忆研究的研究纲领
第七章 当代记忆研究的基本问题
第一节 记忆与认知
第二节 记忆内容
第三节 记忆行为
第四节 记忆主体
第八章 记忆哲学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意义
第一节 记忆是理解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重要范畴
第二节 记忆哲学是解码人工智能及其发展的钥匙
第三节 人工智能中的记忆问题
第四节 记忆哲学与人工智能代际发展
第五节 灾难性遗忘与通用人工智能发展
第六节 人工智能改变人类劳动记忆的可能性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节选
《记忆研究与人工智能》: 萨门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有钱人家,从小体弱多病,后来师从著名的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学习。海克尔是当时世界一流的生物学家。受海克尔影响,他也希望在生物学领域内有所作为。他在海克尔的理论框架内抓住了生物遗传过程中的一个问题:一些已获得的东西的代代相传如何解释?他试图从记忆角度去解释遗传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甚至到澳大利亚游历两年(18911893)。回国后写了《记忆》(1904)和《记忆心理学》(1908)两部著作。可惜的是,这两本著作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没有为同时代生物学家肯定。他的第一本著作出来,受到当时生物学家的围攻,第二部著作出版后更是无人问津。 1918年,萨门自杀。斯卡特曾经从兴趣点、术语、立场以及证据等角度分析了萨门作品被遗忘的原因,但是对于他为什么自杀却没有做出详细解释。这引起了我的兴趣。萨门自杀有三重原因:一是学术受冷、中年丧妻和理想破灭。萨门自杀的第一个原因是学术受冷。他所处的时代是达尔文进化论风靡一时的时期,导师海克尔更是进化论的支持者。受其影响他也希望在生物学界产生影响,但是这也是其人生悲剧的源头,他作品发表后恰恰是受到了很多支持达尔文思想的人的批判和冷遇。45岁时学术上的连续受冷使得他开始怀疑自身,这让我们想到了胡塞尔在42岁的时候也依然不停地怀疑自己。导致萨门自杀的第二个原因是妻子的病故。萨门和他的妻子关系很好,他们彼此相爱。但是由于他妻子患有癌症,最后死于疾病。这彻底摧毁了他生活的支柱。萨门自杀的第三个原因是政治理想的破灭。他是一个普鲁士主义者,坚信德国崛起的理想。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战败,四处赔偿。他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在这三重事件的打击下,1918年他用枪指向了自己的脑袋。萨门死的方式充满了理想主义。正如斯卡特在萨门传记中记载的那样,他在卧室的床上整齐地铺好了一面德国国旗,凝视着国旗和他心爱的妻子躺过的地方,然后心里默念着心爱人的名字以及德国的名字,一声枪响过后,一切都结束了。 由于当时学界的不理解,他的这一理论沉睡了近半个世纪。1978年被心理学家斯卡特发现和挖掘,2010年以后被神经科学家利根川进的团队承认。他的成果作为了进一步研究记忆印迹细胞识别、标记和改造的理论根基。 萨门求学的时候受到海克尔的影响。海克尔在哲学上是一个整体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从整体的、统一的原则解释自然现象。这显然是德国古典哲学影响的结果。因此,萨门也开始追求这样一种方式。他关心的问题是遗传学,尤其是生物各代之间遗传的同一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没有采取达尔文式的经验观察方法,而是带有极浓厚的思辨和实验方法。他找到了“记忆”这样一个原则,在他看来这一原则能够解释自然物种之间的遗传同一问题,通过到澳大利亚游历,他能够找到经验证据。在后来出版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印迹概念,其定义是“由刺激物产生的存在于应急物质中的持久的然而是原初潜在的变更”。另一个概念是唤起(ecphory),其定义是“将记忆印迹或者印痕从潜在状态中唤醒进入到明显活动的影响”。这两个概念成为他解释所有自然现象的出发点,而这两个概念也成为后来记忆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萨门的著作没有在同时代的生物学家中产生较好的影响,反而是受到极大批判。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学术共同体范式的不可通约造成的。在19世纪末,达尔文进化论成为生物学领域的标准范式,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淘汰成为生物进化的主要机制,这一范式对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竞争、狼群社会等都是这种影响的体现。而萨门所提出的通过记忆原则解释自然现象,无疑从两个方面向达尔文范式提出挑战:一方面是记忆作为思辨的、同一的原则无法被经验证实;另一方面是强调了不同生物代际间的遗传同一性。此外,除了挑战权威当红范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同一原则的寻求更是对当时实证精神的一种宣战。如胡塞尔所言,整个时代都是为实证科学精神造就的具有实证精神的人。所以,当他的思想与当红的进化论范式和实证精神产生碰撞时,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