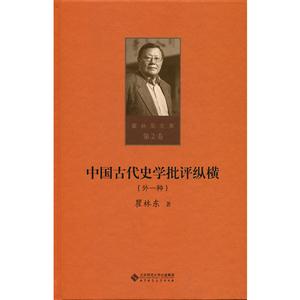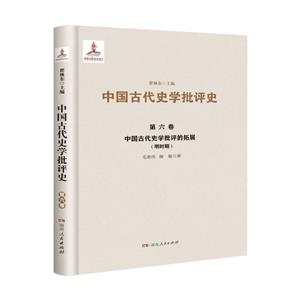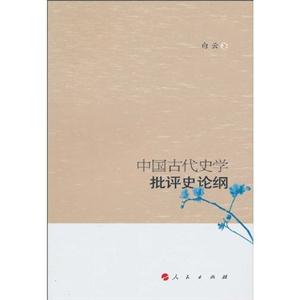作者:阎静
页数:340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56124350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第1卷,即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阐述了先秦秦汉时期史学批评发展的面貌和成就,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作考镜源流的探索。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以先秦秦汉史学的发展为背景,从代表性的学人和文献入手,梳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演进的基本脉络和主要问题,反映孔子、司马迁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揭示古代史学批评在开端时期的一些突出现象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瞿林东,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7年研究生毕业于该系中国史学史专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部召集人、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原主任。主要从事历史学的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版《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等专著、论集;主编《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五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本)、“马工程”教材《中国史学史》、《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三卷本)等书;发表《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等论文、评论四百余篇。201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瞿林东文集》(十卷本)。
目录
一、时代特点与史学面貌
二、史学批评的开端
第一章 诗的时代与史学批评的渊源
第一节 《诗》之史的品格
一、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
二、史学价值
第二节 引《诗》寓意折射出来的史学批评
一、引诗论为政之道
二、引诗论人生修养
第三节 诗教与中国最早的历史教育
一、“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
二、“温柔敦厚,《诗》教也”
第二章 孔子、孟子开史学批评之先河
第一节 孔子论“良史”
一、先秦史官及其记事原则
二、孔子论“良史”与“书法”
第二节 孟子论史书与时代及社会
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三、孟子对《诗》《书》的辩证性认识
第三节 孔子、孟子论事、文、义
第三章 《春秋》三传评《春秋》及其史学影响
第一节 《左传》“君子日”评《春秋》
第二节 《公羊传》《毂梁传》评《春秋》
一、评《春秋》的体裁与书法
二、评《春秋》的信史原则与思想旨趣
第三节 《春秋》三传评《春秋》的史学影响
第四章 司马迁奠定史学批评发展的基础
第一节 家学渊源与史学批评
一、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对司马迁史学批评的启示
二、司马谈临终遗言对司马迁史学批评的影响
第二节 司马迁对《春秋》的全面评论
……
第五章 皇朝史撰述与史学批评的展开
第六章 刘向、刘歆的文献整理与史学批评
第七章 先秦两汉思想家与史学批评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节选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在司马迁看来,孔子作《春秋》,首先,是时代变化的反映。司马迁对于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有着深刻的认识,即如“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周道衰废”“周失其道”,这也是他在《史记》中所再三致意的。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对这一时代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解说:“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他讲到了王室的衰微,纲纪的坏乱,礼义的废弃,诸侯的专政,并重点指出了齐、晋、秦、楚四国霸权的转移。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局面,司马迁指出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悼礼废乐崩”,这里的“闵”与“悼”字,反映出孔子对于时代的关注与担忧。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指出“周失其道而《春秋》作”。司马迁的这些认识,与孟子所讲“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有相通之处,都道出了孔子作《春秋》的时代原因。 其次,是孔子社会责任感的表现。瞿林东先生指出:“中国史学家对史学工作历来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这种崇高的责任感不止表现为对历史的重视,还表现为对现实的关注。”司马迁是体察到孔子对于现实的关注及其内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唯其如此,他在指出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政治悲剧命运后,再三强调孔子作《春秋》。在司马迁看来,孔子虽然多次感叹“吾道穷矣”“吾道不行矣”,但从未改变信念,始终锲而不舍,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作《春秋》,其中自然包含着“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欲以立言“自见于后世”的感慨,但更为重要的是寄托自己的治世理想,为后世立法,即司马迁多次指出的“明王道”“以当王法”“以为天下仪表”“以达王事”等。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所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时,曾引用孔子之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对此,唐人司马贞指出:“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清人王先谦认为:“谓空言义理以教人,不如附见诸侯大夫僭逆之行事。垂诫尤切。”结合前人所论,可以认为,孔子是从经世的角度作《春秋》的,而司马迁也正是从以史经世的角度来认识孔子作《春秋》的。 其二,关于《春秋》的编撰。 根据《史记》所述,司马迁关于《春秋》编撰的认识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春秋》的编次与断限。按《史记》中的《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年表》序以及《孔子世家》所载,孔子所作《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这里,司马迁指出了《春秋》的编次与断限,即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之时,以鲁国十二公即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为序编年记事,而且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 二是《春秋》的取材。司马迁多次提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因史记作《春秋》”等,这实际上说明了《春秋》的取材所自。在司马迁看来,西周王室的文献、各诸侯国的史记及其旧日的传闻等都在孔子参阅之列。在博览这些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孔子“去其烦重”,以鲁国史记(即《鲁春秋》)为主作《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