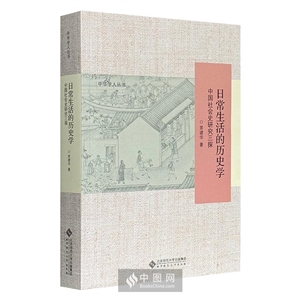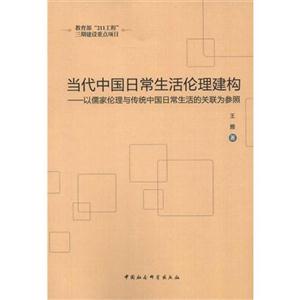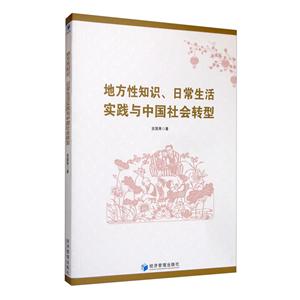
作者:吉国秀著
页数:206页
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ISBN:9787509650196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地方性知识, 从微观社会的视角探讨普通人经营和运作日常生活实践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以及参与、建构与塑造宏观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路径和内部机制, 进而提出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微观模式, 认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如何在中国社会转型中交织在一起, 演化成为共时性的并置和叠加。
作者简介
吉国秀,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日常生活实践与中国社会转型、技术民俗学。在《社会学研究》、《民俗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等项目9项。曾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中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奖、“五个一工程”优秀文化作品奖、冰心儿童图书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目录
第一节 地方性知识的当代意义
一、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
二、从环境决定论到民族生态论
三、从地方性知识到民俗学的知识体系
第二节 地方性知识的生产
一、民众的知识与民俗学者的知识
二、个体的知识与民众的知识
三、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国家
四、地方性知识与日常生活实践
第二章 婚姻习俗变迁与中国社会转型
第一节 婚姻习俗研究的多重视角
一、亲属制度转向
二、阈限的象征意义
三、宗族世系与姻亲关系
四、社会转型的视域
第二节 族际通婚的变迁
一、民族社会学视野中的族际通婚
二、时空坐落及其民族构成
三、从族内婚到族际通婚的转变
第三节 婚姻支付与社会变迁
一、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姻亲关系
二、地方性知识、亲属制度与空间实践
三、婆家婚姻支付的变迁
四、娘家婚姻支付的变迁
五、婚姻支付流动方向的变更
第三章 日常生活实践的时空路径
第一节 时间表达的多样性与中国意义
一、时间的意义
二、中国人的时间框架
第二节 节日传承与集体记忆
一、舅甥关系的凸显
二、节日食品的象征意义
三、个体时间与自然时间
四、记忆的碎片化
五、行为禁忌的地方性
第三节 行动者与空间实践
一、宗教性的空间
二、村落化的空间
三、民族化的空间
四、符号化的空间
第四章 信息技术、职业群体与社会变迁
第一节 信息技术的自然化
一、为日常生活所熨平的信息技术
二、知识扩散的社会结构
三、专家系统术语的社会化
四、常人经验的内化
第二节 网络社会中的新民间叙事
一、信息技术笑话
二、新叙事文本
三、IT笑话叙事的生产
第三节 技术阶层与社会结构变迁
一、IT职业群体的崛起
二、知识分布的类型学
三、职业群体的内部分层
四、对权力的幻想
第五章 民间社会网络、生存策略与社会转型
第一节 民间社会网络与社会转型
一、以个体为中心的亲属路线
二、化解社会冲突的非正式规则
二、新叙事文本
三、IT笑话叙事的生产
第三节 技术阶层与社会结构变迁
一、IT职业群体的崛起
二、知识分布的类型学
三、职业群体的内部分层
四、对权力的幻想
第五章 民间社会网络、生存策略与社会转型
第一节 民间社会网络与社会转型
一、以个体为中心的亲属路线
二、化解社会冲突的非正式规则
三、转化个体风险的社会扶持体系
四、民间社会网络的功能释放机制
第二节 农村民俗与生存策略
一、传统与现代框架下的农村社会
二、农村社会运作逻辑的独特性
三、以民俗为核心的农村社会
四、社会转型中的农村民俗
第三节 民俗文化与区域社会转型
一、区域社会转型的文化维度
二、作为社会整合力量的民俗文化
三、民俗文化的区域性
四、区域转型的精神动力
后记
节选
《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实践与中国社会转型》: (一)“陪送”的弹性与不确定性 与婆家相比,Q镇居民对娘家的婚姻支付没有固定而具体的期望。遵循的原则具有相当大的伸缩度,娘家可以根据意愿与具体情况,“有多陪送多陪送,没有多陪送少陪送”。就传统而言,新婚家庭的经济与物质准备基本上来源于婆家,而娘家的作用微乎其微。双方家庭在婚姻支付上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差异,源于对结婚的不同理解。对于娘家而言,结婚就等于“把姑娘给别人家了”,是“帮别人过日子”。即便是“陪送得再多,也带到别人家去了”。女儿帮助婆家延续家庭,生育的子女也是婆家的,陪送的财产也是婆家的。一句话,“姑娘大了外向”。对于婆家而言,结婚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娶媳妇”本身就意味着媳妇的加入,家庭成员增多,劳动力增加,人口繁衍,家庭延续。即便是婚姻支付再多也都是儿子的财产,最后都是流向自己人而非外人。里外的分类方法始终把女方放在“外人”一边,女性没有财产继承的权利。将这种分类方法应用到结婚仪式中去,就出现了视具体情况而定的“陪送”。“陪送”一词的名称本身,就隐含了当地民间对嫁妆的解释,把女儿嫁出去是“送姑娘”,陪送就是与女儿一同送去的财物。既然是送给婆家的东西,多少也就随意了。这种地方逻辑一直支配着传统娘家的婚姻支付。 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彩礼可以作为嫁妆返回到新郎家庭中,古迪(Goody)就此提出“间接嫁妆”(indirect dowry)的概念。这一概念得到阎云翔的赞同,他认为间接嫁妆用于描述中国社会中的婚姻交换十分贴切。但是,用间接嫁妆来解释20世纪40年代Q镇的婚姻支付实践有些困难。在那一时期女方除了在“包包”时可以带走少量的随身衣物外,基本上不带走任何家庭中的财物,情况稍好一些的家庭会陪送一套被褥。此时婆家没有负担新娘被褥的责任,如果娘家没有做被褥,女方只能接受婆家的准备。一般情况下,“养钱”用来给娘家“解决实际问题”,例如买一石粮食或者养老等,而不是为女儿置办嫁妆。确实如国外学者所说,可以把“养钱”视为姻亲家庭之间的礼物流动,但这种流动是单向的,即便是有一些双向行为,其程度也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用间接嫁妆来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陪送更加困难。困难之一在于,20世纪50年代“养钱”的形式在Q镇逐渐消失,双方家庭之间的现金交换基本上停滞。娘家陪送的来源不是婆家的彩礼,而是家庭内部的直接支出。困难之二在于,陪送的流动方向是夫妇单元而不是婆家。在一个1950年结婚的案例中,娘家陪送的物品为:一套被褥、一套棉衣服、几件衣裳、镜子、洗脸盆、雪花膏、木梳、胰子;1953年的一个婚礼中,娘家陪送了10万元①,并直接交给了女婿。与婆家相比,娘家的陪送有略微上升趋势,例如妆奁与现金的增加。此外,这一时期结婚的案例很少有向婆家索要“养钱”的情况,因此这里的陪送并不是间接嫁妆,它说明Q镇的“陪送”与间接嫁妆的解释相去甚远。 20世纪60年代的陪送延续了50年代的基本框架,并且新增了家具、炊具与餐具,而且被褥似乎转化成为娘家第一的种类。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期间,陪送没有受到影响,依然保留了下来,并且起到了重要作用。男女平等思想的渗透不仅取消了“养钱”,而且引起了娘家权力结构的变化。同时,它也说明了女方对家庭经济依赖的增强。由此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女方在婚姻中得到娘家的经济支撑,并且在婆家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期受到压抑的男方婚姻支付重新抬头,现金和实物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陪送的增长则显得相对缓慢。 (二)“陪送”与婆家婚姻支付的趋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陪送”的种类与金额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在其中的两个案例中,娘家为男方买衣服与皮鞋。如果将其与前述男方婚姻支付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它是对婆家“买衣服钱”的一种借用和颠倒。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买衣服钱”只存在一种关系,关系的两端分别维系着婆家与女方;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买衣服钱”则包含着两种关系,除了前一种关系之外,又新增了第二种关系,它的两端维系着娘家与男方。这说明,“陪送”不仅仅是送给女儿的礼物,同时也是送给夫妇单元的礼物。通过对婚姻支付形式的借用,娘家对待女婿的态度与婆家对待儿媳的态度正朝着趋同的方向努力。更为确切地说,娘家正在试图提高在夫妇单元中的影响和地位。“陪送”中的构成,例如现金、家具、大件与婆家中的婚姻支付越来越相似。到20世纪80年代末,部分娘家也采用了现金支付的形式,这些都与婆家的同期行为极为相似。同工同酬的政策让男女获得了同等的工资收入,女儿对于家庭的贡献与儿子已经相差无几,有些女性的工资收入甚至高于男性。这些贡献包括为兄弟娶媳妇、为家庭添置大件等。女儿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受到重视,“陪送”的增长也可以理解为是娘家对女儿贡献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