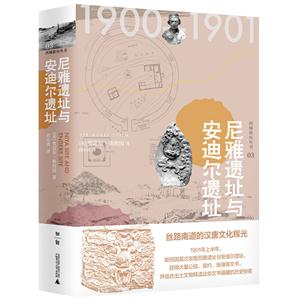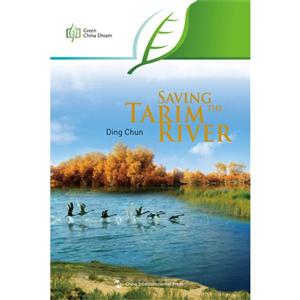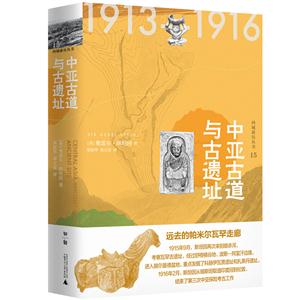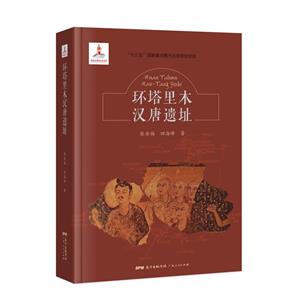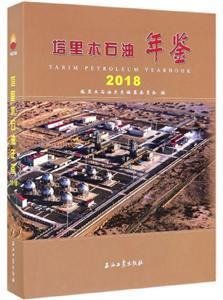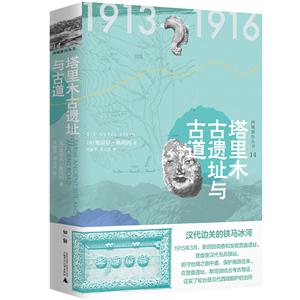
作者:(英)奥雷尔·斯坦因著
页数:233页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49558797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分孔雀河沿岸的古道、从库尔勒到库车、库车古遗址、从库车到喀什噶尔、穿越帕米尔。内容包括: 营盘遗址 ; 孔雀河的古河道和注滨城 ; 尉犁和现代喀拉库木等。
作者简介
奥雷尔·斯坦因(1862—1943),英国人,原籍匈牙利,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者。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三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考古探险。根据其考古探险经过及成果,先后撰写出版了《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巫新华,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内陆亚洲考古。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秦立彦,出版译著《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目录
第一章 孔雀河沿岸的古道
第一节 营盘遗址………………………………………………………………….1
第二节 孔雀河的古河道和注滨城……………………………………24
第三节 到库尔勒去的古道沿线烽燧………………………………..37
第四节 尉犁和现代喀拉库木…………………………………………….59
第二章 从库尔勒到库车
第一节 沿着天山脚下走…………………………………………………….72
第二节 都护治所………………………………………………………………..79
第三节 从轮台到库车………………………………………………………..91
第三章 库车古遗址
第一节 绿洲的地貌及境内古都的位置………………………….102
第二节 木扎特河以西的遗址…………………………………………..110
第三节 在库车东南遗迹的收获………………………………………132
第四章 从库车到喀什噶尔
第一节 拜城的古代遗存…………………………………………………..142
第二节 经阿克苏和巴楚到达喀什噶尔………………………….152
第三节 唐代对阿克苏至喀什噶尔的道里记………………….158
第五章 穿越帕米尔
第一节 在喀什噶尔做准备………………………………………………165
第二节 沿着阿赖谷地走…………………………………………………..171
第三节 沿着帕米尔的西部边缘走………………………………….187
第四节 经过阿利丘尔和大帕米尔………………………………….212
节选
第一节 拜城的古代遗存 5月6日,我从库车出发西行,去调查喀什噶尔地区。从 4月初开始,总领事一职由帕西·赛克斯上校充任,马继业先生则回英国休假,当时我得知他打算在 6月的头一个星期从喀什起程。最要紧的是我得在他动身之前到达喀什噶尔,以便我在俄国帕米尔和奥克苏斯河最上游沿岸的既定旅行,在准备工作上确有把握得到他的帮助。库车与喀什噶尔相距近 500英里,至少得连续走三个星期才能到达,加之沿途经过几个区政府时,总得做短暂停留,这样就剩不了多少时间再匀给路上使用了。我只好满足于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大致地调查一下古代中国的北道上我未曾问津的若干路段。我初拟将剩下来可供文物调查的有限时间用于巴依区的两个小遗址,据库车的知情人说,以往欧洲的考古学家从未对此两地作过调查。
从库车城前往克孜尔河,头两天我们走的是大路。这条路爬上一连串贫瘠的山冈,沿着曲折的峡谷向木扎特河延伸,峡谷的入口距库车城约 10英里。在向峡谷走了将近一半路程的时候,我们经过了克孜尔伽哈的一座高大的废塔楼和几座小窟寺,这些遗迹证明这一段路线有着古老的历史。峡谷中最便于防御的地点叫作喀热勒,在这里我看到 4座塔楼的基址坐落在险峻的悬崖上,显然是一座古老的丘萨的标志。
在越过一座光秃破败、高度约达 5 600英尺的高原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到达了克孜勒欧乐堂村。接着于 5月 8日,我对木扎特河左岸山沟里的一大群佛教窟寺做了一次匆忙但很有意义的考察(图 30)。这个极其重要的遗址叫克孜尔明屋(即石窟寺——译者),以往俄国、德国和法国的几支考古队曾反复对它进行调查和勘察。石窟寺的许多极有意思的壁画,已由格伦威德尔在其相继出版的两部著作中作了充分的描述;而转移到了柏林的一大批壁画,也将在勒柯克教授的出版物中得到真实的再现。因此,这里无需赘述这些窟寺的地位和性质。在新疆地区,再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个遗址那样使我联想到敦煌千佛洞留给我的印象。
5月9日,我离开通往巴依区的大路,走上了更靠北面的路线。一路上先后经过了兴旺的拉帕尔村庄、灌溉村庄的河道的河床沿线,以及萨依拉木村庄,然后来到特扎克喀格明屋遗址。这个地方的名称源自处于该河出山口正下方的耕种区,遗址就在出山口附近。从图 31的平面示意图上可以看出,宽阔的河床从天山山麓丘陵伸出,一条山嘴沿着河床的右岸往下延伸,而遗址的位置就在它最南端的支脉上。在这山嘴的尽头,悬崖壁立,河道经过崖壁脚下,蜿蜒约 60码。这里,一群小山洞开在密集的岩石丛中,其中向河而建的约有8座,其余的大体也是这个数量,见于一条小山沟的两侧,山沟揳入一块小高地,高地上残留着一座塔楼和一座附属建筑(标号为 I)。
大多数小洞的石壁上暴露着形成石壁的粗石块,大概由于施工草率,壁面很不平整,原先敷抹的灰泥面已经剥落。因此不可能究明这些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室到底是佛堂还是僧房。有两座石洞面积稍大,直接开在上述附属建筑的下方,其平面图见图 29。
洞壁上保留着部分灰泥抹面和破损严重的壁画痕迹, iii号洞内还建有环形回廊,可见此二窟应系佛寺无疑。洞室的前壁和隔出一个小间的隔墙都是粗糙的砖砌体。这两个洞和其余各洞都有迹象表明,在朝拜断绝之后,它们曾一度或再度被用作栖身之所。
I号建筑遗址坐落在一座人工扩建的小山顶上,高出河床约 120英尺。破败不堪的夯土砾石墙围圈着面积约 40码 ×26码的场地。西南角附近有一墙段残高约 9英尺;其余几段残墙只有低矮的砾石墩保存下来。据说在贝道拉特统治时期,人们为挖取泥土中的硝石,曾将围墙内部翻掘一遍。这说明古时遗址上曾建有住房。
这座高原形状的山顶是上述山嘴向南和西南方向延伸的尽头,山顶上散布着伊斯兰时期的低矮坟丘。这个事实或许表明当地的崇拜曾在这里沿袭下来。山嘴的东南端有一个小镇遗址,它的周围留有严重毁坏的围墙,唯一容易攻破的北面和西面修有防御工事,当年的壕沟至今仍清晰可辨。壕沟通贯山顶,长约 40英尺,东北角上深达10英尺,凿岩而过。围墙用取自河床的大石块砌成,北面厚约 3英尺,遗迹最为明显。在其他地段,由于南面和东面有河水流过悬崖陡壁,围墙建得草率,几乎已无踪迹可寻。墙内的面积计约 140码 ×100码,但见石堆遍地,都是房屋石墙的遗存。整个外貌酷似印度河畔的卡里夫科茨和印度西北边省丘陵地带附近的其他城址,只是那些城址的规模要大得多。
出于对殷勤的汉人区长的尊重,我在巴依区区政府停留了一天,然后再次离开我们走过的大路,去调查明屋。这个地点我在库车时听说是在木扎特河南面贫瘠的丘陵地区。我们先是在有喀普萨浪河灌溉、精心耕种的田地间走了大约 10英里,然后在温巴什小集市越过木扎特河到了右岸。有趣的是,这里的河床虽然足有1英里宽,实际上河水分成了三条小渠,总流量不过 580立方英尺 /秒。这个水量同不到两周之前我在该河流入平原的出山口上测得的2 000多立方英尺 /秒比较起来,可谓十分有限。这说明当时测量的河水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木扎特河在巴依区下方汇纳的几条支流供给的,而罕腾格里峰一带作为主要河源的冰川则尚未开始倾泻其夏季洪水。不仅如此,木扎特河的实际水量在流经巴依盆地时可能有不少已被亚喀阿里克一带沿河两岸耕地的灌溉渠道吸收了。
我们在吉格代里克村扎下营帐。 5月 13日,我调查了当地称之为明屋的石窟寺群。它们的位置在南偏西南方向约 5英里外,正当一条狭窄曲折的山谷口上,山谷从荒瘠的山梁上节节下降,将巴依盆地与塔里木河北面的荒原分隔开来。在这条小谷延伸到谷底约200码的地方,两面都是松脆的砂岩形成的悬崖陡壁,这里我们发现三股小泉彼此靠近。山泉在西面崖壁上一块突出的矮台地脚下自芦苇丛中流出。泉水清冽爽口,不过到了承接泉水的小溪里就变得略带咸味,再往下流动不远就干涸了。拜城的这一地带,到处是严重侵蚀的砂岩或页岩,山脊上寸草不生,然而却有可以饮用的水源,这想必便是为数众多的石窟佛寺和僧人住所能够存在的缘故。这些石窟中至少有 6座是在西面的峭壁上沿着不超过 0.25英里的崖面修建的。东面稍稍低矮的山嘴(图 32)上有 4座,彼此靠近,还有几座隐蔽在侧面的窄山沟里,或者埋在碎石下面。前面提到的那座谷底小山梁或台地,上面似乎曾建有若干佛塔,但因“寻宝人”反复挖掘,就连塔基也难以寻找了。
西面的石窟中有一座小窟高出平地约 30英尺,最容易登临。窟内有一道环绕的回廊,故而可以肯定它原是佛寺。它的前部已经陷落,由于雨水的冲刷,内部大部分填满了板结的淤泥。中央岩块上开有5个小龛,龛内和侧廊入口上方均留有壁画残迹。由此往南约 200码有一群主要的洞窟。其中最高的一座(见图 29中标作 Jig.I的示意图及图 32左侧)据说曾出土写本,那是大约在 7年前,萨希布阿里即印度驻库车的阿克萨喀勒,由他的一名当地勤杂工领路,在这里挖到一大包写本,后来交给了马继业先生。这座石窟在大约 120英尺的高处,内有一个房间,开有一扇窗。它的门道有3英尺宽,位于一条走廊的尽头。从地上和上方岩石上留下的沟痕可以看出,入口有木门可以关闭。房内北壁有一排火龛,上方有 5个小壁橱。
房内的地面一部分尘封土盖,一部分铺满了废秸秆和残席子。这些垃圾中发现有大量各种碎纸片,上面写着中亚笈多类型的婆罗米文字。另有约 20张的碎纸字迹相似但字形较大,说明萨希布阿里的清理工作做得颇为草率。有可能此洞早先就曾被挖宝者翻查搜索,或许还不止一次,使写本遗存遭到破坏。在走廊里发现6张较大的纸片,一张棕榈叶及一张桦树皮写本的两张细碎残片。这些纸片虽然作为文献遗存意义不大,毕竟有助于断定由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或由印度政府派人,在不同时期收购的以及曾由霍恩雷博士保管的那些写本均系来源于库车。
往北,在地势约低 50英尺处,也有一座石窟寺(图 29)。窟内有一间小室,宽 17英尺,进深 10多英尺,两侧及中央岩屏背后绕以回廊;廊道内有一壁龛(台座,台座前面有壁龛——译者),龛内原有一尊灰泥造像。小室的前部以及顶上的抹面均已塌陷。但顶部残留着彩绘的菱形图案;它与造像龛内所绘坐佛残迹一样,显得古朴工巧。小室和回廊中均未清理出遗物。再往北约 60码,在地势又稍低一些的部位,有一个穹窿顶大洞,残宽约 31英尺、进深超过21英尺。它的外观像个厅堂,可能供僧人聚会之用。前部已塌,落下的大量岩石覆盖着地板,堆积甚厚。由此再往北约 50码,又有两个石洞,其间仅以薄薄的一道岩石墙相隔,但如今已有豁口相通,显系近世所开。草率打凿的洞壁已被烟火熏黑,盖住地板的泥土和废秸秆层表明这里曾被反复挖掘。较大的一座宽约18英尺、进深 12英尺,看上去像是自然洞窟,只是洞壁已经整平。地板上有一个洞穴,现已部分塌陷,由此往西穿行,可以进入另一个类似的洞窟。
山谷东面的洞窟都是小穴,由于雨水不时从岩石分解的山坡上倾泻而下,洞里遭到了水流的冲刷和淤泥的堵塞。山坡上的岩屑层大概把某些开凿的山路也一起盖住了,因而高处的山洞有的极难攀登。保存最好的石窟是一座精心开凿的小室,位于溪岸上方约 80英尺处。我发现洞内的地面曾被全面清理过。从这里往山嘴的北端攀登,好不容易才穿过一个完全坍塌的石窟而到达窄小的山巅。在这约 200英尺的高处,我发现两个石窟,洞内大部分已被淤泥填塞,两个石窟都是僧人的住所。其中一个(图 29)的入口开在一个角上,进入石洞得先经过一段凿岩而建的走廊。石窟里没有清理出任何遗物。在该洞下方的一块小台地上,我看到一些烧焦的木料,木料下面的黏土地面已被烧成红色,可见这里原先建有木构小寺,后来毁于大火。在攀登这座东山坡时,一路上陶器碎片随处可见,说明这里曾长期有人居住。
朝向山嘴东南端的山沟里的较小洞窟,可能是被雨水冲下来的碎石堆积层盖住了。埋没一半的洞口很难与水流冲刷出来的自然凹穴区别开来。但这样的洞穴我的向导只知道一个。它的位置在一道窄山沟的高处,沟底仅几英尺宽,我们爬了约 0.25英里,又攀登了一段陡峭的碎石坡,才到达那里。这是一个小石室,后面有 4英尺宽的回廊。洞壁上仍然保留着白灰面,但无论在洞壁上还是在中央方形岩块各面的壁龛内均无彩画痕迹可寻。小室和走廊的地面过去曾被挖掘过。除此之外,我还在西山坡较低处几条山泉下方约 0.25英里的部位调查到一个石室。它的前部已完全被毁坏,洞内填塞着几层板结的淤泥,堆积高度约达 6英尺。但在后壁上方还保留着一条饰带的彩绘痕迹。它的装饰线条向洞顶方向逐层收缩,形成木料顶板构件的效果。
总的说来,我在吉格代里克的这个明屋所得到的印象是,在这个荒凉贫瘠的山区,由于有山泉存在,因而在佛教时期这里成为一处自然外道类型的圣地。此后,当地的自然条件似无重大变化。这个观察结果在地理学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佛教时期以来的干旱作用,对天山的这条外围山脉并未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