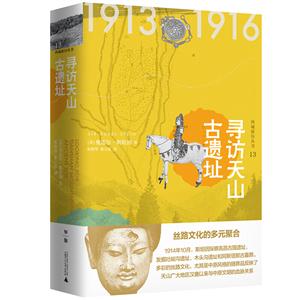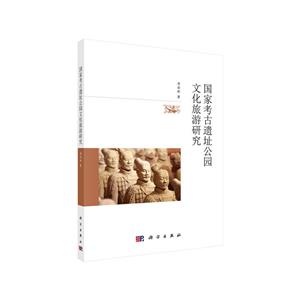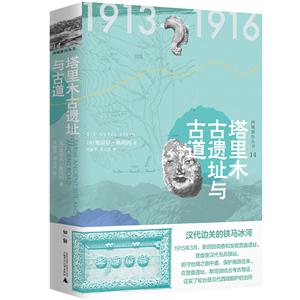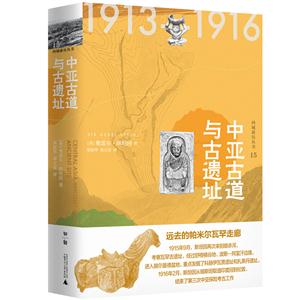
作者:(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
页数:279页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49537129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分五章, 在阿姆河上游地区、在呼罗珊的东部、锡斯坦圣山、波斯境内锡斯坦绿洲的遗址、锡斯坦的沙漠三角洲。瓦罕的古代遗址 ; 穿过伊什卡什米和加兰等。
作者简介
奥雷尔·斯坦因(1862—1943),英国人,原籍匈牙利,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者。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三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考古探险。根据其考古探险经过及成果,先后撰写出版了《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巫新华,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内陆亚洲考古。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秦立彦,出版译著《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目录
第一章 在阿姆河上游地区
第一节 瓦罕的古代遗址………………………………………………………1
第二节 穿过伊什卡什米和加兰………………………………………..29
第三节 舒格楠谷地…………………………………………………………….49
第四节 从罗申到达尔瓦孜………………………………………………..63
第五节 从喀拉特金到布哈拉…………………………………………….96
第二章 在呼罗珊的东部
第一节 从阿什哈巴德到马什哈德………………………………….111
第二节 经过波斯—阿富汗边界………………………………………114
第三节 进入赫尔曼德盆地………………………………………………125
第三章 锡斯坦圣山
第一节 锡斯坦的历史地位………………………………………………134
第二节 科赫伊瓦贾的遗址………………………………………………139
第三节 壁画……………………………………………………………………….163
第四节 山顶的遗址…………………………………………………………..180
第四章 波斯境内锡斯坦绿洲的遗址
第一节 沙利斯坦及其附近的遗址………………………………….190
第二节 锡斯坦坝以及赫尔曼德河的古名………………………199
第三节 扎黑丹遗址以及西北方的晚期遗址………………….203
第五章 锡斯坦的沙漠三角洲
第一节 古代和近代的遗址………………………………………………220
第二节 史前居民遗址………………………………………………………240
第三节 一条古代边境线遗址…………………………………………..258
第四节 从锡斯坦到印度和伦敦………………………………………274
节选
第二节 经过波斯—阿富汗边界 我从马什哈德到锡斯坦共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这使我对所经过的山区和谷地的自然状况、生活条件有了个总体印象。这些山区和谷地是现在的呼罗珊的东部边境,北边是海里鲁德地区,南边是一些内流沙漠洼地,波斯—阿富汗边境线就从这些洼地中穿过。但由于我只能走得特别快,所以对当地的地理和居民状况都没有进行仔细的考察。在大战后期,印度的考察队系统测量了这里的地面,在此我就没必要说这些地方的地貌特征了。从那以后,我也没有时间研究和这些地区的历史有关的资料。再加上写作的时间和本书的篇幅都有限,所以在记录这段路程的时候,我只限于说一下我们走的是什么路线,并简短描述一下我在路过的时候,注意到了什么有考古学和民族学价值的东西。
走了两天后,我来到了法里曼,它位于从马什哈德到赫拉特的主干道上。途中我们在桑巴斯特村停留了一下,这使我有机会访问了附近的古城遗址。据说这座古城是阿亚孜建的,他是加兹尼的马哈穆德的一位瓦齐(伊斯兰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译者)。那里仍矗立着的建筑遗存只有坚固的圆顶建筑和高塔,塔上有雕刻精美的花砖装饰。据说这两个建筑都是阿亚孜建的,因此,它们就称得上是伊朗现存最早的伊斯兰建筑了。研究近东艺术的学者迪埃孜博士曾经仔细研究并描述过这些有趣的遗址,所以在此我只是提一下罢了。
在去法里曼的途中和过了法里曼之后的很多地方我们都容易看出,在俄国占领里海地区之前,居住在呼罗珊这部分地区的爱好和平的波斯农民,由于北边土库曼人抢劫奴隶的活动和劫掠,遭受了长期的苦难。这里肥沃的可耕地大部分虽然不需要灌溉,但只有一小部分被实际耕种了。另一方面,村子里和田野中仍矗立着很多座塔。这些现象都反映出以前那些劫掠的影响。从前,当席卷山区和谷地的土库曼人突然出现时,人们匆忙之中就躲到塔里。在法里曼,一个叫米尔·穆罕默德的年老的台克土库曼人,在领事馆的命令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陪我们走了两天(图 63)。我满怀兴趣地欢迎了这个人,他可以说是那个劫掠时代的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遗物”。1885年的潘加德赫之战后,他和 20多个本部落的人追随了英国,离开了后来成为俄国领土的那个地方。
他和这些流放者中的其他6人如今被雇作信差,每周从赫拉特给领事馆取信件,这些信件是从杰曼(在今巴基斯坦——译者)那个印度铁路的起点经过阿富汗领土到马什哈德的。他年轻的时候曾多次参与劫掠活动,很乐意谈起他帮着扛走的一个个奴隶,以及在这些活动之前的长期夜行军。
我从他那里得知了这些劫掠的细节,这才知道为什么劫掠者走了那么远的路,为什么他们的行动总是很秘密(他们的成功就有赖于此)。他们得穿过边境线上的那个山区。由于山区临近土库曼人的牧场,是毫无人烟的,所以这些劫掠小队给自己的人马带的口粮只够前三四天用。之后,他们从事先定好的波斯村子那里获得物资。这些村子的居民如果答应保守秘密(突袭是成功的基本条件),就可以幸免于难。有了这样周密的计划,再加上土库曼人的马跑得特别快,特别有耐力,使他们完成了很多“壮举”。在一次著名的劫掠中,他们一直来到了南边的锡斯坦,劫走了很多战利品。有趣的是,米尔·穆罕默德有一种不露声色的优越感,说明他很自豪自己所属的是几百年来伊朗人谈虎色变的一个部落。同时他的五官很俊美,完全没有蒙古人的特征。这表明整个土库曼种族中都已经掺杂了伊朗人的血统,西亚的许多其他突厥族入侵者都是这样。在这位令人愉快的土库曼人的陪伴下,我意识到波斯史诗传统中的图拉尼亚人和拜火教典籍中的图尔亚人,很可能和耕种着伊朗肥沃绿洲的那些邻居是同一血统,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而伊朗人却世代把他们看作敌人。
之后的两天中,我经过骷髅塔山口,翻越了南边的山脉。这条山脉的两坡分别被哈扎拉蒙古人和俾路支人占据着。他们仍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上可以看出,波斯过着定居生活的农民,一次次缓慢地同化了本来过着游牧生活的入侵者。我们穿越了巴哈尔兹大谷地,从南面的山脉中有不少水流进这个大谷地中。11月15日,我们经过了西玛塔巴德、喀拉伊瑙、阿伯尼亚等村子,它们都掩映在果园中,比我们在去锡斯坦的途中看到的任何村子都吸引人。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这条山脉的南坡。我们在 11月17日来到了南坡上荒凉的鲁伊哈夫城。它破败的泥围墙里面已经被废弃,奇怪地使人想起了穿过疏勒河河谷大道沿线的废“城”。鲁伊哈夫这条小河流入了那些宽阔的沙漠洼地中最北边的那个。这些洼地中有盐湖或沼泽,南北连成一线,把呼罗珊的山区和高原与东边阿富汗高原的脚下隔了开来。在鲁伊哈夫,我满以为今后几天要连续穿过荒凉的地区。然而仅走了 3英里后,我们就来到了小绿洲哈吉尔德,这真使我又惊又喜。在那里的一座古代堡垒和几座圆顶泥屋(就是村子)附近,矗立着一座美丽的马德拉什(意为学校,伊斯兰国家的一种高级教育机构——译者)。这是提木里德·沙鲁克王在公元 1444年建的。这座建筑比例很匀称,是个优雅的四边形(图 64),周围是两层带圆顶的房屋。大门带拱顶,朝东。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建于这一时期的很多大学中的建筑都是这样的布局。迪埃孜博士以前就详细研究了这个遗址,当时这个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即是正面装饰着的精美的彩色瓷砖和正对着方形庭院的墙受到的破坏还比较小。所以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
大多数地方的土坯烧得很硬,质量极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瓷砖保存得也很好,它们拼成优美的植物图案或蔓藤花饰,色彩和谐,盖住了大部分墙面。但不幸的是,这种美丽的装饰也吸引了那些想要迎合西方人贪婪口味的人的注意。由于土坯特别硬,而嵌在土坯上的瓷砖特别脆,所以那些人在剥下一部分墙面装饰的时候,必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我发现方形庭院里的地面上,全都是散落的土坯碎片,碎片上仍保留着色彩鲜艳的釉质。当地人说大部分损坏,都是驻扎在巴拉巴德村,以及俄国与阿富汗边境线上其他地方的哥萨克军官让自己的手下人干的。高高的拱形大门两侧矗立着两个圆顶大厅,它们的墙上和龛中装饰着富丽的彩绘泥塑(图 65)。这里淡蓝色或镀金的精美植物图案处理成浅浮雕,受到的破坏比较少。以寸草不生的小山为背景,旁边是一片小绿洲,这个色彩绚丽的高贵建筑集中体现了波斯艺术和文化的最优秀特征。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紧迫,我没能访问西南方 24英里外的祖赞村,那里的遗址是沙鲁克王的又一个马德拉什。
我们从鲁伊哈夫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地带,这个地带的农业几乎完全依靠坎儿井来灌溉。我们在进入纳马克萨尔盆地的途中,经过了巴拉巴德和桑甘这两个美丽的村子。从这两个村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波斯农民凭着自己的勤劳,依靠坎儿井,在干旱的荒野中取得了怎样的业绩。这两个地方的一个醒目特征就是美丽的柏树林。这些柏树是人们精心栽种的,以便抵挡住从东北方刮来的大风,否则大风就会毁坏庄稼和其他植被。现在这里的风之所以是这个风向,并且这样猛烈,是由这个低洼的沙漠盆地中的对流作用引起的。大风、光秃秃的砾石平原、极少的发咸的地表水,这些都使我不由得回忆起罗布泊南边荒凉的缓坡。
这个环境中同样也有被废弃的遗址。当我们接近破败的小堡垒木吉纳巴德周围那些简陋的小泥屋时,经过了一片碎石区,像常见的塔提那种类型,延伸了约 0.5英里。当晚我们就在那里宿营。根据从当地人那里获得的信息,这个遗址本是座“古城”,一直沿用到阿巴斯王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捡到了几块上釉的陶器碎片和带装饰的青铜碎片,这些遗物都完全与当地人说的年代相符。据说这个地方以前叫马尼加巴德,是以阿夫拉西阿卜的一个女儿命名的。
11月20日,我们走了 35英里路,越过纳马克萨尔盆地边上的一条光秃秃的低矮山脉,来到了巴姆鲁德。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人家,只在一个地方看到了牧人偶尔使用的水井。巴姆鲁德小村坐落在一条荒凉的宽谷中,谷地朝东汇入另一片洼地。那片洼地中在阿富汗边境附近有一片咸水沼泽。从阿富汗方向来的强盗经常走穿过那片洼地的路,巴姆鲁德却一直能安然无恙。人们怀疑巴姆鲁德给阿富汗强盗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物资供应站,这种猜测也不是全无根据的。最近有一伙人在卡伊恩和托尔巴特海达里耶之间的大道上抢劫了一支大驼队,据说这伙人正在回去的路上。根据当地人的建议,我们在这个安全的地方休整了一天。
之后我们朝正南方走了两天,穿过阿辛加恩和古莫,来到了盖兹克宽谷地。在穿越的山脉北坡上,我们路过了三个小村子,其中古莫村居民的相貌和语言像阿拉伯人。这使我想到,我所钟爱的中亚土地这下真的在我们身后了。从人口比较多的盖兹克村出发后,我们在 11月24日来到了宽阔的高原谷地塔巴斯依马泽纳。这个谷地的自然特点和考古学价值比较值得注意。谷地十分开阔,看起来够荒凉的。无论谷地上流有什么水,早在谷地汇入第三处沙漠洼地(名叫大石提瑙麦德)之前,水就消失在覆盖着土和砾石的大准平原上了(准平原两侧是光秃秃的小山脉)。但以前广泛采用的坎儿井灌溉体系可以维持大面积的农业用水,比现在塔巴斯地区400多户人家耕种的田地面积要大得多。
那座很大的带围墙的古城(图 66)就证明了这一点。它周围有很多破败的民居遗址,说明这座古城以前只是一个大得多的居民点的核心部分罢了。从考古学角度来讲,围墙里面那一层又一层带圆顶的土坯小建筑的确能给人不少启发。底层“房间”大概以前某个时候曾被当作马厩,里面垃圾一直堆到圆屋顶。这些垃圾大概是从上面房间地板上的大洞掉下来的,把底下的屋子变成了垃圾箱。在很多地方,上层的房间也发生了同一现象,于是人们在顶上又盖上房间。这个遗址是个很好的例证,它告诉我, 1907年我在米兰公元8—9世纪的吐蕃戍堡拥挤的营房中挖掘的那些垃圾堆是怎样慢慢积累起来的。显然,那里的人们也发现,在顶上新盖泥屋子比清理越来越多的垃圾更容易。
这座城如今大部分地方已经被废弃了。离开它后,我们沿着去达斯特吉尔德的路走。在 5英里多的距离内,我们经过的是一块块精耕细作的农田和光秃秃的砾石高原交替出现的地方,还有不太古老的被废弃的村庄遗址。在胡鲁马克村西边,我看到了一块塔提的碎石区域,看起来比那些村子要古老得多。南边另一个村子的居民把它叫作萨赫里劳坎。人们说在这里曾偶尔发现过文物。但除了大量有釉和装饰的陶器碎片,我没有发现别的遗物。它们表明这个遗址沿用到了中世纪后期。值得注意的是,安德鲁斯先生指出,有些碎片属中国制造的陶器。如果能确定这样的碎片的大体年代,就会有助于我们判断多数当地陶器的年代。
当晚,这个地区的老奈伯穆罕默德·玉素甫汗在他城堡般的大宅院中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关于为什么塔巴斯如此荒芜,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据说,现在人们用的 12个坎儿井中的水足够灌溉如今耕种的农田了。只要有钱,很容易就能建更多的坎儿井。这个地区的不安定状态使人们无法筹集到必需的资金,而由于以前土库曼人时常劫掠,人口一直难以增长,所以还没有什么压力使人们想建坎儿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