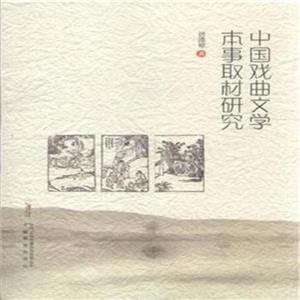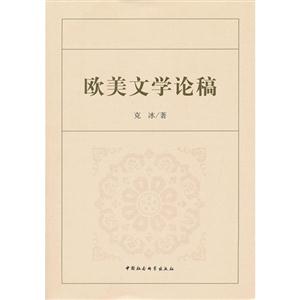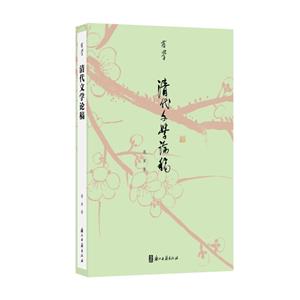作者:颜长珂
页数:376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ISBN:9787503934834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戏曲文学的历史回顾、戏曲文学的艺术特征、札记三部分,收录了“难登大雅之堂—戏曲文学的历史回顾”、“元杂剧中的吏员形象”等内容。
作者简介
p> 颜长珂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湖南涟源人。1 933年出生予长沙。1951年
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戏剧普通班。长
期从事戏曲工作。著有《戏曲剧作艺术
谈》、《古典戏曲名作纵横谈》、《中国戏曲
文化》等。曾任《戏曲研究》主编,《中国
大百
目录
节选
曲文学论稿》序
颜长珂同志将他在“文革”后的部分研究成果结集《戏曲文学论稿》
出版,我谨以此文表示祝贺。
1951年起,我曾与从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戏剧文学专业毕业的颜长珂
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那时我们都是二十上下的青年。五十多年过去了,
我的工作单位几经变化,专业上也无所建树,而长珂却一以贯之地从事
戏曲研究工作,在戏曲文学、戏曲史、戏曲理论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
就,成为实至名归的戏曲理论专家。
长珂说,在戏曲学校(沈阳和北京)工作的五年,是他进修戏曲知
识的重要阶段。这也是我同他共事的五年。他聪颖,好学,有才华,文
笔也好,是那时同事中的佼佼者。起初,他并不真正了解戏曲,更谈不
上热爱戏曲,甚至对戏曲还有某些隔阂。戏曲学校集中了一批艺术造诣
很高的京剧名家。他经常同这些老教师交谈,观摩他们的教学和学生的
实习演出,还参加其他一些专业活动,在那弦歌之声不绝的环境中耳濡
目染,逐渐了解和喜欢了戏曲,为他后来从事戏曲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建国初期,青年人的个人理想总是同革命的大
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无所谓属于个人的事业追求。长珂说得好:
“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在工作中学,边干边学,需要什么就学什
么。个人的目的、方向不可能很清晰、很明确。草鞋没样,越打越像。”
长珂的戏曲研究工作始于组织上分配的任务,是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把一
个时称“新文艺工作者”的青年打造成有突出成就的戏曲理论专家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强戏曲理论建设的任务主要由中国戏曲研
究院承担。在张庚、郭汉城两位前辈主持下,调动全院戏曲史论研究力
量,编写《中国戏曲通史》。这是一部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评介我国古代戏曲发展历史,探索戏曲发展规律的
戏曲史专著。作为基础理论建设科研项目的这部专著,1980年出版以来.
又经过一次修订重印和一次再版,长珂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1980
年的第一版,长珂主要撰写有关评介元清两代作家作品的章节;十年后
修订时是集体参加而由长珂执笔;二十年后(2006年)再版时,当年参
加编写的同志都已先后退休,有的还离开人世,在沈达人、龚和德两位
兄长的参与下,由长珂完成了全书的修订工作。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
版的这部《中国戏曲通史》(上中下三卷)被中国出版集团选入荟萃20
世纪文化经典标志性出版工程的《中国文库》第三辑。2007年11月6
日,我出席《中国文库》第三辑出版座谈会翻阅入选书目时,不由得想
起已故的张庚前辈,想起健在的郭汉城主编和其他参与编写的同志,想
起长珂对中国戏曲史论学科建设的贡献。
长珂的另一重要学术实践,是参加国家大型出版工程《中国大百科
全书》第一版《戏曲》卷和第二版戏曲学科的编纂。参加《中国大百科
全书》编纂工作的都是我国各学科著名专家学者和中青年学术骨干。
1983年出版的《戏曲》卷编辑委员会由张庚任主编,长珂作为中青年学
术骨干出任戏曲文学分支副主编(主编郭汉城)。经我粗略考察对比。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与《中国戏曲通史》有着一定的连续
性,不仅主要编写人员有衔接,内容上也是相关联的。长珂在张庚、郭
汉城指导下,负责编审元代、清代戏曲文学条目,撰写高明《琵琶记》
等重点条目。计划于200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在各学科
专家修订编纂后按字顺统编,由长珂接替前辈担任戏曲学科主编。诚然,
《大百科》第二版是在第一版基础上修订的,但也体现了对原版不足之处
的改进和知识的更新,戏曲学科一二版主编的变更,不能不说是人才成
长和学科建设的某种历史性跨越。
长珂的学术实践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数十年来戏曲史论“两门
抱”,理论与实际结合,成果丰厚,撰写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1988年中
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戏曲剧作艺术谈》,可以称之为戏曲编剧古今谈,
是探知戏曲文学殿堂的入门书。1993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文
化》,则是中国戏曲史简明通俗本,对宋、元、明、清戏曲文学发展衍变
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均有深入浅出的剖析,为学习中国戏曲史者所必读。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拟于2008年出版的《中国京剧百科全书》,长珂
作为编委会副主任和京剧文学分卷主编,撰写了京剧文学和其他有关条
目.是学习戏曲知识的又一基本读物。由长珂主编的《戏曲研究》丛刊,
理论联系实际,纵论古今,二十年来发表千余篇文章,不少篇章影响广
泛,成为学界公认的高品位学术刊物。
体现长珂学术研究另一重要成果的,应该是这部在“文革”后写成
的《戏曲文学论稿》了。我看了其中的几篇。各篇都写得深入浅出,大
雅若俗。《难登大雅之堂——戏曲文学的历史回顾》、《悲欣交集——(中
国十大悲喜剧集)前言》、《元杂剧中的吏员形象》,记述了数百年戏曲文
学的发展历程,剧作者与“梨园院体”关系之演变,最有代表性戏曲文
学作品的成因及其影响等。《京剧文学简论》(为《中国京剧百科全书》
所作)和《戏曲文学的艺术特征》(为亚洲传统戏剧国际研讨会所写论
文)是全面、科学论述京剧(戏曲)艺术及其美学特征的权威性与普及
性相结合的论著。
本书作者是怎样看待他的这部《戏曲文学论稿》的呢?长珂说,在
完成《中国戏曲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两项国家任务
过程中,也“读了些相关的书,有些研读心得写成文字,就是这个集子
里《元杂剧中的吏员形象》、《衣锦还乡的变奏》……自己命题自己做。
有解数学题的感觉,心态比较轻松,甚至能享受到一些写作的愉悦,这
是把写作当任务时不大容易得到的”。长珂如此珍视“自己命题自己做”,
并由此获得远非赶任务所能得到的轻松和愉悦,这犹如“由必然王国到
自由王国”那样,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宝贵的。
前不久,长珂写给我的信中说:“专题论文,作者往往付出更多心
血,故敝帚自珍。但在图书市场,销路却难看好。”依我看,值得珍视
的,不仅是作者付出的心血,更由于书中的学术含量。至于学术著作市
场销售不畅,则反映着当今社会的文化缺失。像《戏曲文学论稿》这类
学术著作,理应归于小批量、常销售一类。此书的及时出版,应该说是
文化艺术出版社及其主办主管者的远见卓识。
为写序,我阅读了有关书、文和资料,深感长珂——我青年时代的
朋友,思想和文笔都很老到。可喜,可敬!
2007年12月初写于北京寓所
“京师尚楚调”析
——京剧史上的一个问题
人们常说,京剧是在徽、汉两种声腔的基础上形成的。“四大徽班进
京”的故实;是人们经常提及的;谈到汉(楚)调与京剧的关系,常被
引用的史料,则是粟海庵居士《燕台鸿爪录·三小史诗引》中的这两句
话了:
京师尚楚调,乐工中如王洪贵、李六以善为新声称干时。
从这个材料,史家往往得出如下结论:一、楚调(汉调)是在道光八年
至十二年(即粟海庵居士在北京居住的这段时间)才由王洪贵、李六等
传至京师,被视为“新声”;二、徽班的二黄腔与楚调中的西皮腔也是从
这时才开始结合,进入了“皮黄剧”(京剧)的新阶段。如王芷章先生
《腔调考原》(1936年出版)中说:
粟海庵居士留都之日,即楚调抵京之岁,故谓为以新声称于时
者,即表其前无此调,而今日始至京也。虽未确定某一甲子,但始
于八而终于十二,折中言之,谓之(道光)十年前后,当无多大出
入处。
周贻白先生也说:“……而汉剧到道光八年至十二年(1828—1832)才有
王洪贵、李六两人加入京班演唱,一时目为新声。”(《谈汉剧》,载《中
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又说:“所谓‘楚调’‘新声’,也许竟是‘西皮
调’。”(《中国戏剧史长编》)这种观点在京剧史研究中比较流行,但值
得进一步探讨。
我以为《燕台鸿爪录》中的这两句话中并没有后人所理解的“楚调”
即是“新声”的意思。“京师尚楚调”只是说北京的观众注重、爱好楚
调。至于王洪贵、李六擅长的“新声”究竟有何特点,我们可以从这篇
“诗引”对他们的徒弟汪一香的描述中看出一些眉目来:“一香学而兼其
(王、李)长,抑扬顿挫,动合自然,口齿清历。”在另一首题为《赠汪
一香》的诗中,粟海庵居士还具体描写了这个演员的演唱特点是“回腔
入破摧藏久,煞调添声顿挫多”。这里强调“抑扬顿挫”、“煞调添声”,
说明汪一香的演唱艺术富于变化、讲求技巧;这是他向老乐工王洪贵、
李六学习所得,也是王、李之所长。因此,如果说他们“以善为新声称
于时”,是指在唱腔、唱法上丰富多变,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也许更为贴
切。这也难怪作为旦角演员的汪一香兄弟,却向这两位演老生的“老乐
工”讨教了。至于楚调的演唱特点,据叶调元《汉皋竹枝词》的描述是:
“音须圆亮气须长”;并有附注说明:“腔调不多,颇难出色,气长音亮,
其庶几乎?”早期徽、汉演员也都具有这样的特色。如《梨园旧话》讲到
程长庚时,说:“乱弹唱乙字调,高亢之中,别具沉雄之致,而又四平八
稳,无所谓行腔,更无所珍惜,忌人学步。”王、李的演唱,则已越出了
这种讲求实大声宏的传统风格,是很有创造性的。看来,把“新声”与
“楚调”等同起来是不见得合适的。
要说楚调是在1828年以后才由王洪贵、李六传到北京,这也缺少充
足的根据。他们是不是来自湖北的艺人,什么时候开始在北京登台献艺,
并没有其它材料可以说明。如果说,他们的确是在1828—1832年间来自
湖北,只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就使得这种“新声”很快地风行于北京,
<节选内容>=形成“京9币尚楚调”的局面;在素以发展迟滞和保守为特点的封建社会
中,可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奇迹了。试看当初四大徽班浩浩荡荡来到京师,
也没有能使“二黄调”迅速地轻而易举地夺取首都舞台上的主导地位;
二黄调是在与昆曲、秦腔、京腔等声腔的并存中,在长期的艺术交流与
竞争中,才逐渐得到发展的。假如说,楚调一到北京,便立即成了京师
的时尚,得到长足的发展,连北京出生的演员(如汪一香兄弟等)也纷
纷学习这种新的外来的声腔,并在演唱中开始采用北京语音,赢得“鄄
曲声声妙,燕言字字清”的赞誉,看来是不大可能的。
在“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楚调”二字早已见于记载。乾隆五十
年(1785)吴长元所作《燕兰小谱》中,提到北京有位昆曲演员四喜官
(时瑶卿),兼唱乱弹,即所谓“两头蛮”;作者有诗赞同:“本是梁豁队
里人,爱歌楚调一番新”。可知他所演唱的“乱弹”多为楚调。可惜书中
对于声腔、剧目、表演等记录甚少,只说到他“尝演《打樱桃》”。现在
京剧中还保留了《打樱桃》这出戏,唱吹腔。论者以为这种唱腔可能是
从弋阳腔发展变化而来的①,接近二黄系统,据说源出于安徽石牌。徽班
亦有《打樱桃》剧。如果当年四喜官的演出与此相去不远,却被称为
“楚调”,倒是耐人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