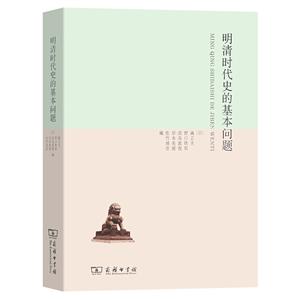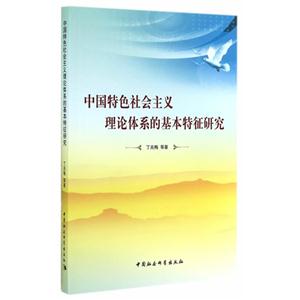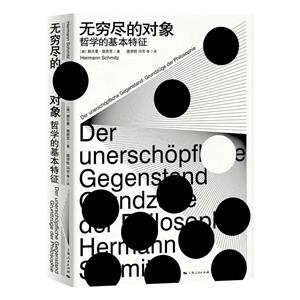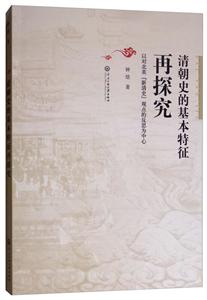
作者:钟焓著
页数:215
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56601576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较为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北美地区出现的“新清史”学派的知识背景,进而将其学术观点概括为“同君联合体理论”、“共时性君权说”、“族性的晚生理论”、“帝国的疆域扩张说”、“清朝统治的东北亚本位主义”等五大基本命题,再结合对相关史实的深入辨析,对它们采取各个击破的剖析方式,论证它们在史实上全无成立的余地,纯属国外学者为了迎合某种错误思想,曲解我国历史而杜撰出来的不实之说,从而在结论部分强调指出正是缘于上有以汉制为突出特点的官僚制度的强大联结整合功能,下有底层各族人民之间在长期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两个离不开”,从而才把内地和边疆维系塑造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血肉整体,这也促使在清朝统治结束以后的共和时代下,清帝国原有边疆的大部分地域依然能够顺利自然地转化为现代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钟焓,1976年出生。相继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与中国古代史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已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目录
第一章 北美“新清史”研究兴起的学科背景及其学风
第一节 “新清史”崛起前的学术背景:“旧清史”研究的一度辉煌和旋即衰落
第二节 内亚史的知识一立场就与“汉化论”截然对立和冲突吗?——来自伯希和等学者的反证
第三节 并非上游——北美“新清史”学派在国际满学界所处的位置
第二章 “新清史”学者构建的历史命题平议——从族性晚生论到东北亚本位论
第一节 “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
第二节 试析《两个佟氏》所建构的历史叙事及其谬误
第三节 试析《清朝始祖神话序论》所建构的历史叙事及其谬误
第四节 柯娇燕对《满洲源流考》的误读与其构建的学术命题之间的关联
第五节 柯娇燕臆造的汉军旗人的错误叙事与其学术命题的关系
本章结语
第三章 君权总是选择特定的语言来发声——对“共时性君权”理论的反思与批评
第一节 清朝官修辞书中“君部”所见君主称谓的排序先后问题
第二节 论“皇帝”(huwangdi)在清朝君权中地位上升的历史过程
第三节 文殊菩萨和转轮王为何会在“御制”类辞书的君主名称中双双缺席
第四节 清朝君主的终极政治理想是“合璧”还是“同文”
本章结语
第四章 如何从非汉文史料的角度回应”新清史“学派”
第一节 从满文史料中所见的”中国“看清朝与中国的同一性
第二节 对清代蒙古缺乏”中国(dumdadu ulus)意识的反证
第三节 中亚非汉文文献里指代“中国”的两大名称:秦一契丹
第四节 论察合台汗国时代以来作为“契丹”(中国)组成部分的天山北路
第五节 论准噶尔汗国时期作为”契丹一秦“组成部分的天山北路一带
本章结语:非汉文史料的引入在跨国界学术批评中的作用何在
结语 从学术与政治的交集看“新清史”学者的意识形态倾向
节选
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欧洲阿尔泰学下的内亚史研究毕竟在战后半个多世纪里依然延续了由伯希和、海尼士等拓展深化的强调语言训练、注重考据史实,淡化理论运用等相对求真笃实的学风,虽然后起者在多语种史料互证对勘方面难以达到伯氏等前辈学人的研究深度。相比之下,“新清史”的学风却与之差别迥异,与“旧清史”的分道扬镳及对其的忽视与批评就已经暗示出“新清史”不会再像“旧清史”那样以实证研究为中心,而是改为更加注重社科理论的运用(此点以后还要详细剖析)。虽然“新清史”确已提出了要重视运用以满语为主的非汉语史料的响亮口号,但要落实到具体学术研究中仍面临诸多知识上的困难。因20世纪70年代以后北美大学中国学专业训练的重心普遍趋向社科理论化,再加上北美考据学风积累的程度本来就不如欧陆深厚,同时其高校在读博士生的阅读节奏又显得过快,以适应阅读量飞速增长的教学要求,遂导致像劳费尔、伯希和等大师的务须耗时精读方可入门的考据学成果早已淡出多数学生的阅读视野,①对于即将进入学术职业市场并面临成果发表压力的他们来说,社科理论显然比专深考据之作更有助于在短时期内将自己习得的书面知识体系化,为将来作为晋身之阶的专著写作奠定不可缺失的理论基础,同时也省去学习巨量历史与语言知识(尤其是涉及内亚与中国互动这样令人生畏的研究领域)所必需耗费的宝贵时间。故我们一方面看到,“新清史”学者群多出道不久,即能在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中推出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使之成为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为将来在职场上的更大成功树立较高起点;而他们的前辈如范福和与傅礼初即使天资聪颖得让人羡慕不已甚至五体投地,却在生前均无任何专书传世;更不用说其学问更为精深的老师柯立夫去世之前也只有一册《蒙古秘史》的译本聊以行世。然而另一方面,他们采取的这种明显有别于厚积薄发的成长途径虽然能够更便捷地通向事业上的成功,却终究使自己严重地偏离了以考据为主的实证路线,因此其成果也就很少能发表在较受欧洲满学界认可的前面那些学术出版物上。此为既兴一利则必生一弊。 在“新清史”快速发展的最近20多年,欧洲的满学界研究阵容相对稳定,就笔者对前述刊物和论集泛览之后的总体印象,个人发表成果最多的三位学者应该是斯达理、魏汉茂和俄国学者庞晓梅(T.A.Pang)。1946年出生的意大利学者斯达理是职业满学家,同时还长期担任《中亚杂志》的主编之职,为推动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满学界的前沿性研究成果在该专业刊物上的发表做出了积极努力。斯氏曾于20世纪70年代前去西德师从已届晚年的福华德(1902-1979),后者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满学界的发展贡献与影响最大的学者。他的科研与教学活动使得西德作为西方世界满学研究中心的地位在半个多世纪内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挑战。而就学风而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严格追随伯希和的研究路数,高度关注文献学和语言学的考证类题目,并在清代满汉舆图的研究上开风气之先。同样他也像伯氏一样,论文纯为解决某个具体科研疑难而作,几乎从不针对普通读者发表普及性文字。①从学风承袭的角度上看,伯希和等更老一代学者的实证风格正是通过福氏传承给了战后欧洲的满学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斯氏已逐渐成为欧洲满学界最高产的满学家,到2005年时已用英文、德文、意大利文等公开发表论文上百篇(不含书评),而其刊布的各类著作(含合著、翻译、编著)现已超过20部。其涉猎范围囊括了满族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等多个方面,所发表的论述也多为实证性的研究成果。②如此恢弘可观的数量恐怕在整个国外满学界都不做第二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