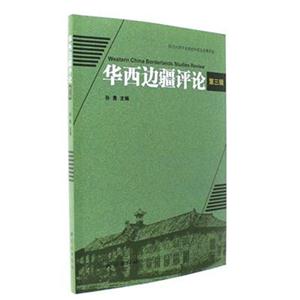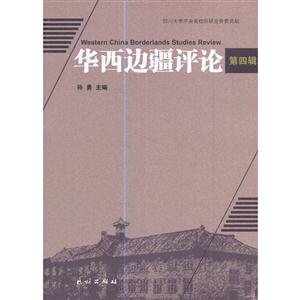作者:周蜀蓉著
页数:390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101133295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1922年3月,以美国学者莫尔思(W.R.Morse)为首的12位西方学者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以下简称学会)。学会以研究华西(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甘肃等)政治、人文、风俗、环境以及对当地民众影响为目标,计划通过调查、出借设备、举行讲座、发表论文、出版刊物等方法来促进研究。后来有英、美、加、法、德、中、澳等国学者加入,会员一度达540多人。中国学者自1930年加入,至1950年时,先后有120人参加。40年代中国学者逐渐成为华西研究的主力。学会是中国近代靠前个以华西边疆为宗旨的靠前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国近代学术目前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中国边疆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是由个人为主研究方式向着专门化学术机构研究行为转化的重要标志。本项目抢先发售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本身做全面系统的基础研究,将弥补学界有关学会本身研究无学术专著的空白。不仅纠正了1950年以后视学会为“反动的西方学术机关”的提法,以学会档案及出版文献为依据对学会进行重新评估,更将学会置于优选政学、政教语境中讨论其创办及发展,综合评价学会历史作用、价值、贡献及影响,乃至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边疆史、靠前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华西基督教传播目前的重要地位。
作者简介
周蜀蓉,四川大学博物馆研究馆员,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先后从事中国古代女性、四川古代移民、华西基督教及近代华西边疆研究。编著有《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合编,巴蜀书社2004年版)、《巴蜀移民史》(合著,巴蜀书社2006年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影印本》(合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在《史学月刊》《四川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本书特色
中国近代成立z早、影响z大、历时z久的研究西南边疆的专业学术机构。
详细爬梳档案资料,系统勾勒发展历程,展现近代学术机构本土化的演进脉络
1、本书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进行全面研究,该学会是中国近代成立z早、影响z大、历时z久的研究西南边疆的专业学术机构。该学会关注华西地区的政治、人文、风俗及自然环境,尤其关注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
2、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的难点在于史料缺佚,相关档案文献资料较为分散,不易获取。本书作者详细梳理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的三千余件该学会档案,并结合该学会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研究。
3、本书不仅全面系统勾勒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创办过程、研究活动及社会影响,还在全球文化殖民与20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及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演进过程中考察该学会的价值和意义,体现了作者的学术视野及功力。
目录
目 录
序
绪 论
第一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创建的背景
第一节 传统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
第二节 近代基督教在四川的传播
第三节 世界范围内国际汉学的发展
第二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创建与发展
第一节 创办与发展1922年—1937年
第二节 繁荣与衰落1937年—1950年
第三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组织结构
第一节 章程与细则
第二节 执行委员会
第三节 会员制度与会员
第四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附属机构
第一节 葛维汉图书室
第二节 博物馆
第五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学术活动
第一节 面向西南边疆的学术考察
第二节 以学问服务社会:学术演讲
第三节 会刊及其他出版物的出版、发行
第四节 跨出封闭的地域:面向全球的学术交流
第六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边疆研究
第一节 学会的人类学(民族志)、考古学研究
第二节 学会针对华西边疆的自然博物学研究
第七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特点
第一节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领域、方法与特征
第二节 边疆研究的合作与传承:以葛维汉、林名均为例
第三节 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以闻宥为例
第八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与近代边疆研究
第一节 作为现代学术机构:近代西南边疆研究的奠基
第二节 “帝国想象”与“国族意识”:政学关系语境中的西南边疆研究
附 表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历届执行委员会名单(1922-1950)》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员表(1922-1950)》
《1922年-1950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历次讲演目录》
参考文献
一、论文
二、专著
三、报刊
四、档案
后 记
节选
“帝国想象”与“国族意识”:政学关系语境中的西南边疆研究
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西南边疆研究兴起于19世纪中后期,这一波的边疆研究浪潮主要由外国学者所开拓。外国学者群体以学者、军官、传教士为主。民国边疆史学家徐益棠回顾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历程,对此深有感慨,他说:“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而尤以法国之天主教徒及英国之基督教徒为最有贡献。”李绍明在回顾西南民族研究时亦说:
在国人应用现代科学体系研究西南民族以前,西南民族研究的领域主要是由外国学者开拓的。近代,一些外国人先后进入西南地区,除了有的是直接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或传教外,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虽然他们的调查研究均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但他们对于西南民族研究引进了现代科学的方法,所形成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十分有用,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区别对待。
从根本上讲,外国人对东方的调查与研究,是西方殖民国家对世界范围的“未知”之地探险的一部分,它自19世纪上半叶时兴起以来迅速席卷了全球。宏观上看,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无疑还是资本主义全球范围内殖民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欧洲资本主义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开始了全球性的扩展与征服,在军事领域其表现为殖民征服,而在宗教领域,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宗教的全球大奋兴。基督教在华的传教运动也因其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密切关系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帝国主义对华的“文化侵略”。上世纪20年代,瞿秋白就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四大方式,“文化侵略”即其中之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也指出“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形式之一,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在学术领域,宗教、学术与殖民之间的话语模式也在这一逻辑之内得以建立。马长寿在新中国成立前论人类学的发展的文章中就清晰展现这一内在逻辑:
人类学的发生原系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欧洲先进国家莫不迫切需要了解殖民地与民族、特别是野蛮民族的一切状况,这便成了如何控制殖民地的主观要求。调查、探险,成了一时的风尚,商人们的日记和传教士的报告等,就是当时人类学原始的资料。他们用白种人的尺度,来测量有色人种的体质和文化,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判断异教徒的信仰、道德和制度,以为统治殖民地民族的凭借。所以人类学最初实际只是一种蛮族学(Barbarology)而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范发迪对此更有清醒的反思,他指出在帝国征服的背景之下,19世纪在华兴起的博物学研究是“科学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学术研究事实上与帝国政治有紧密的联系,科学与帝国殖民事业两者存在着共生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两者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回馈圈。范氏描述在帝国主义时代博物学的研究事实上反映出在“西方中心观”支配下对世界范围内认知体系的塑造过程,他说:
……
具体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发展历程上看,如果说早期学会的发展明显带有以传教士群体为核心,带着典型的“帝国想象”展开对西南边疆研究的特征的话,那么30年代的学会会员明显表现出一种更大的包容度、混杂性,而其学术风格则更多带有强烈的“国族意识”。这种转变过程事实上是多年潜移默化、相当复杂的历程,不过从较宏观的视角上看,也不难看出一些基本的轨迹。
其一,抗战军兴、国府西迁的政治大背景,使文化的中心从北平、上海转移到内地,这为华西边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人员储备。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殖民地国家民族意识随之高涨,民族意识日益强化的国人以民族运动冲击着外国人在华的各种事业,基督教更是首当其冲。30年代初期,学会传教士因应时代潮流对其组织机构进行改革,尽可能地吸纳众多来源的学术力量,使其在30年代看起来更加多元化,更加开放与宽容。随着大批文化、学术机构的内迁,葛维汉表示说:“在华西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学会欢迎更多的中国学者成为我们学会的会员,这将给学会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帮助将学会发展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组织。”刘延龄说:“对于中国成员的加入以及中国同事们表现出的研究热情,我深感喜悦。对于一个一开始由西方人组建的组织而言,学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这也是学会自创始之初赖以不断成长的原因和动力。我们还将继续致力于与我们的中国同事一道开展更多的活动,发展更多的会员。”黎富思提出应鼓励那些还没有与学会有所联系的中国年轻人参与到学会的工作中来。部分传教士更认识到“华西的问题只有华西的人们才能解决”。这些思想的转变,促使学会不断地以开放的姿态朝着国际化的学术机构迈进,学会新章程第三条规定,“(学会)对该领域的科学研究感兴趣的任何人都开放”。这表明学会的态度是,不论其国籍和居住地、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学术背景乃至立场观点诸多不同,只要对华西边疆研究感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其中。学会逐步从华西基督教旗帜下的一个传教士人类学社团嬗变为一个国际化、学术化、综合性的社团。“国际化”取代了“区域化”,“学术化”代替了“基督化”,“全盘西化”迁移为“中西融合”,科学研究与传教活动逐渐剥离。
抗战以来,随着大量政治、经济、文化机构的内迁,大批的中国知识精英来到华西,为西南边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也为学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学会也审慎地同意部分优秀的中国研究者加入学会,到30年代后期,学会已拥有中国籍会员五十六人。40年代在学会成员总体呈下降趋势之时,入会的中国学者呈上升态势,例如1940年新增七人,1941年新增五人……截至40年代后期,新增中国会员六十一人。在学会历史上有一百一十八名中国人入会,占会员总数的21.6%。这些入会的中国学者大多有西学背景和留学经历,在民族意识驱动下活跃在华西研究领域。他们善于运用西方科学理论方法去考察边疆,从不同视角去研究华西社会,在与西方同人的交流中提升自身学术水平,以期弘扬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学者几乎“失语”的现状。中国籍学者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会的面貌。40年代,学会的会刊(第12卷至第16卷)共发表九十五篇文章,其中西人三十七篇、本土学者共五十八篇,本土学者发表文章数量占总数的61%。1943年学会秘书郑德坤致函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无比自豪地说,学会现在拥有数量多、质量高的学术文章,其中部分是西方学者的,而大部分是中国学者的。中国学者的研究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借鉴西方先进的思维理论与方法,在对华西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研究,其研究结果是本土化的成果,且不乏该领域的开拓之作。与之同时,本土学者积极推进与国民政府合作、与国内学界的互动,以期让更多的四川乃至华西的中国学者聚集到学会中来,共同研究边疆,使之成为该地区的学术重镇。中国学者在学会的崛起,与抗战前夕“中国学术界曾一度呈现突飞猛进的进步”的学术潮流相因应。
其二,西南边疆在国家抗战复兴的历史使命中的地位日益上升,这使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30年代的地位、研究的内容、学术的宗旨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学会的本土会员服务国家、服务民族的“国族意识”日益强烈。整个国家,包括学术机构都统一在“抗战建国”的主题之下,因而确定了学会研究的母题与本色。
抗战时,西南边疆的地位陡然上升,华西地区成为“民族复兴”基地和“抗战建国”后方,倍受政府与学界的关注。边疆研究与“其它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成为当时学术领域中最流行的学问。一些学术机构、政治团体纷纷将边疆研究纳入“爱国救亡运动”之中,“各地学术专家亦在响应政府倡导,从事边疆问题之研究”。受此刺激,众多学者投身研究边疆问题,边疆研究机构及学术刊物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也组织了不少边疆考察和研究活动。
本土学者尤其容易受到社会局势的影响,也更倾向于与民族主义思潮结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本土学者积极参加政府、社会及学界组织的考察和研究活动,希望能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抗战建国”的历史使命结合,为国家、为抗战、为民族的复兴出力和服务。观察学会中杨少荃、方叔轩、李安宅、于式玉、李方桂、刘承钊、侯宝璋、陈耀真、刘恩兰、胡秀英、蓝天鹤、吴金鼎、郑德坤、冯汉骥、闻宥、方文培等本土学者在30年代的思想动态与研究旨趣,当不难看到许多研究中都反映出深沉的民族情感。以植物学家方文培为例,1932年,已经在四川做过四年有余植物考察和采集的方文培发表了《中国植物学发达史略》一文。在该文中,方文培把中国植物学史追溯到神农时代,并以不少篇幅梳理道咸以降在华采集植物的西方植物学家。尽管方氏承认西洋人对中国近代植物学有重要的贡献,但他认为“西洋以科学方法研究之植物学输入中国,学校课程中始列入植物学,惟其材料,最初大部分系采取欧美及日本之适合我国情形者用之耳。仍非纯粹之中国植物学也”。有鉴于此,方文培呼吁应该建立“以中国植物为材料”的“纯粹之中国植物学”。方氏致力建立的“中国植物学”明显蕴涵着学科独立的民族情感。而另一位植物学家胡秀英则撰写有《植物学与民族复兴》,彻底将人们日常观念中纯粹的植物学研究与民族意识联系起来。胡秀英在文中谈到植物学与民族复兴的基本问题——优生学的问题。胡氏指出欧美国家利用基因遗传原理来避免先天疾病,胡文说:“这些急进的思想我们暂且不提,可是别国所实行有效之优生方法,我们不能再漠视之。这次的国难虽使我们觉产生优良健壮国民之重要,因为优良健壮之国民,就是建国的基础,所谓优良健壮之国民,必须身体强壮,精神丰富,智力充足,脑筋健全。”无论是方文培提倡的“中国植物学”,还是胡秀英基于民族复兴提倡的优生论,都可以看到在30年代抗战复兴的历史语境下,科学研究与国族意识的紧密结合。
此外,不少的西方学者亦融入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事业。1937年,葛维汉代表华西协合大学参加由四川省政府组织,瑞典考古学家安德生、中央研究院考古所祁延霈、国立四川大学周晓和等人组成的西康地质与考古考察团前往西康地区考察。这是中外学者第一次与当地政府合作进行科学考察,收集到的文物资料归国立四川大学保存。1941年、1942年,葛氏又加入中国教育部、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联合组织的边疆服务团前往川西考察羌人礼俗宗教,为羌人修建了一所学校。他对羌人、川苗进行田野调查(1933-1948)和研究,成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制定部落民政策的基础。1937年,丁克生在华西协合大学开设农业基础课程,为华西地区培养科技人才,长期进行华西传统农业与畜牧业改良,开拓该地区近现代农业与畜牧业,又与化学教授徐维理联合领导华西天然食品研究项目。徐维理教授染色学,研究华西天然染料,支持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为抗战军用毛毯解决染料退色难题,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奖状。
过去人们曾经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反动学术机构”,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南边疆研究的第一个近代机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对于促进近代西南边疆研究的转型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的作用。学会强调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人类学与汉学共冶一炉的学术风格,都为近代西南边疆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了解、互动与整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华西边疆研究学会都无疑是中国近代学术史及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