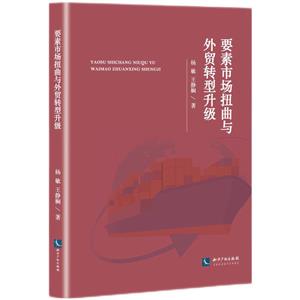作者:刘晴
页数:221页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543228795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沿着“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逐步展开。首先对二元经济结构与外贸转型升级、国际贸易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及评述,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其次, 通过建立一个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和出口贸易事实为依据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贸易成本的角度剖析企业区位分布和贸易模式选择共同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机制。
作者简介
刘晴,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以及China Agriculture Economic Review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一本。
本书特色
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经济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内外贸分治和双轨制海关监管等特殊因素。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所言,“直接将新古典模型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为此,近三年来作者的研究团队以经济全球化最趋势为研究背景,结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情,通过借鉴和拓展现代异质性企业国际贸易理论模型,潜心研究“外贸转型升级”议题。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二元经济结构文献
第二节 国际经贸新规则相关文献
第三节 贸易转型升级文献
第四节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第三章 二元经济结构与外贸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基准模型
第三节 模型稳健性:引入纯内销企业
第四节 扩展模型:放松同质劳动力假定
第五节 本章小结
第三章附录
第四章 二元经济结构与外贸转型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机制分析
第三节 实证分析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国际经贸新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国际经贸新规则主要内容及典型特征
第三节 我国对外贸易的微观典型事实
第四节 国际经贸新规则对中国企业贸易边际的影响
第五节 国际经贸新规则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
第六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国际经贸新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数据与估计模型
第三节 实证结果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七章 融资约束、二元贸易与转型升级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理论模型
第三节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经验证据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七章附录
第八章 结语
第一节 结论
第二节 政策含义
第三节 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节选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Lewis(1954)为了刻画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摒弃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要素市场的假设,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引入理论模型,进而在一个两部门经济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dual-economy model)。
Lewis(1954)通过归纳发现:不同于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传统农业部门仍普遍存在,经济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了描绘发展中国家这类独特的经济发展现象,Lewis刻画了一个两部门经济体: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于同一经济体中。为了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形,Lewis假设现代工业部门虽然生产技术较为先进但在整个经济中占比很小,而传统农业部门即使生产技术落后、劳动边际生产率很小,但却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为了刻画发展中国家大量剩余未就业劳动力的存在,模型还假设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Lewis认为在一个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封闭二元经济中,无限的劳动供给会促使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化,直至所有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纳。而随着现代工业部门蓬勃发展,不断吸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经济中的剩余劳动力数量下降使得劳动力不再趋向于无限供给,劳动边际生产力逐渐提升,进而提升了整体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实现了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而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的点称为“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该点意味着劳动力由过剩转为短缺,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Lewis二元经济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规律性的理论基础。
Ranis和Fei(1961)基于古典主义学派视角,改进了Lewis模型,通过将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特征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现代工业部门以不变工资水平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第二阶段特征为现代工业部门仍继续吸纳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但此时劳动力已经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过剩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逐步增加;第三阶段特征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纳,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相同;模型强调了农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Lewis二元经济理论。随着经济学的发展,新古典学派的流行使得后续有关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研究大多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如Jogenson(1967)则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下,反思了Lewis等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Jogenson指出如果经济中不存在隐蔽性失业,工业会占据二元经济结构的主导地位,工业就业和工业产出最终将控制整个经济。Ramanathan(1967)则基于非中性的技术进步和技术进步依赖于过去投资的假设,进一步推演了Jogenson模型。Dixit(1970)通过比较古典和新古典两种视角下的二元经济理论,发现新古典主义框架下的Jogenson模型经济增长路径与古典主义Lewis模型相一致。Todaro(1970)的研究则发现在城市部门存在大量失业,且农村部门没有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非但不会刺激工业化进程,反而会加剧城市失业,同时危及农业发展。
Lewis(1979)重新回顾了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并着重探讨了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两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剩劳动力的来源和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距的持续性。Fields(1993)则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研究了收入增长的不均等,并将整体的不均等分为部门内部收入增长不均等和部门间收入增长不均等。Banerjee和Newman(1998)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引入了信息不对称,通过假设现代部门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传统部门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由代理费引致了一个效率与信贷约束的权衡取舍,进而指出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进入现代工业部门,自由放任的现代化难以最大化社会福利。Fields(2004)、Kirkpatrick和Barrientos(2004)分别从劳动力市场二元性视角和经济结构二元性视角重新检验了Lewis二元经济结构,发现模型的核心结论仍然稳健。Islam和Yokota(2008)则在Lewis的二元增长框架下考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重点探讨了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中国正迈向刘易斯拐点。Zhang等(2011)指出中国工资水平快速上升,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
国外学者的近期研究致力于从微观角度解释二元经济。Wang和Piesse(2013)尝试为二元经济结构建立微观基础,分析了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和人口增长,证明并区分了剩余劳动力,内生了现代部门工资决定机制,考虑了劳动力转移的动态并定义了两类“刘易斯拐点”。Fergusson(2013)强调农村地区存在不止一种产权制度,通过内生化产权制度选择,说明了劳动力的流动惰性与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性。Gollin(2014)通过人力资源在部门间的分配刻画了二元经济,并指出农业部门工作者受教育程度更低。Wingender(2015)的研究同样证实了人力资源分配的影响机制,指出正是由于农业部门中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强可替代性导致了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低于非农业部门。Yuki(2016)则动态化了二元经济结构,指出经济体的长期产出如何依赖于最初的财富和部门生产率分布。Diao等(2017)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部门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或结构调整式的增长,其中结构调整式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由低生产率行业到高生产率行业的重新分配,是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
国内学者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我国经济是否越过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指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是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分水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依赖于密集的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享受人口红利,其是否步入了刘易斯拐点在国内外学者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蔡昉(2007,2010,2015)发现中国经济转型的新阶段,正面临由劳动力供给过剩转为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困局,如果刘易斯拐点不仅仅特指一个时间点而是描绘某一个时间段,那么中国已经迈入了“刘易斯拐点区”。曾国平和曾三(2008)考量了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服务业与经济开放,发现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是服务业增加的主要原因。姚上海(2009)根据近期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变现情况推测我国正在迈入刘易斯第一拐点,尝试为我国农民工的“用工荒”现象提供解释。张永丽和景文超(2012)则认为我国已经迈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已经由过剩转向短缺,并不断向充分就业,劳动力供给不足迈进。
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学者认为我国目前劳动力供给充足,并没有迈入刘易斯拐点。樊纲(2007)认为我国农村仍存在大量劳动力剩余,因此我国将会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阶段,步入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刘洪银(2009)的经验研究证明我国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张广婷等(2010)也认同了这一观点。周燕和佟家栋(2012)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行业和地区间的工资差距仍然存在,经济并未越过刘易斯拐点。王必达和张忠杰(2014)同样证实了我国传统农业部门中仍存在剩余劳动力。周建锋(2014)认为“民工荒”浪潮并未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我国并未迈入刘易斯拐点。薛继亮(2016)则认为中国部分区域步入了刘易斯拐点,另一部分区域仍存在充裕劳动力供给,比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由于不同的原因都已经迈入了刘易斯拐点,而东北地区仍然处在劳动力净流出的状态。杨帆等(2017)认为我国经济中仍存在巨大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并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Lewis(1954)为了刻画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摒弃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要素市场的假设,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引入理论模型,进而在一个两部门经济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dual-economy model)。
Lewis(1954)通过归纳发现:不同于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传统农业部门仍普遍存在,经济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了描绘发展中国家这类独特的经济发展现象,Lewis刻画了一个两部门经济体: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于同一经济体中。为了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形,Lewis假设现代工业部门虽然生产技术较为先进但在整个经济中占比很小,而传统农业部门即使生产技术落后、劳动边际生产率很小,但却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为了刻画发展中国家大量剩余未就业劳动力的存在,模型还假设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Lewis认为在一个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封闭二元经济中,无限的劳动供给会促使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化,直至所有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纳。而随着现代工业部门蓬勃发展,不断吸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经济中的剩余劳动力数量下降使得劳动力不再趋向于无限供给,劳动边际生产力逐渐提升,进而提升了整体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实现了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而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的点称为“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该点意味着劳动力由过剩转为短缺,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Lewis二元经济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规律性的理论基础。
Ranis和Fei(1961)基于古典主义学派视角,改进了Lewis模型,通过将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特征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现代工业部门以不变工资水平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第二阶段特征为现代工业部门仍继续吸纳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但此时劳动力已经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过剩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逐步增加;第三阶段特征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纳,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相同;模型强调了农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Lewis二元经济理论。随着经济学的发展,新古典学派的流行使得后续有关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研究大多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如Jogenson(1967)则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下,反思了Lewis等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Jogenson指出如果经济中不存在隐蔽性失业,工业会占据二元经济结构的主导地位,工业就业和工业产出最终将控制整个经济。Ramanathan(1967)则基于非中性的技术进步和技术进步依赖于过去投资的假设,进一步推演了Jogenson模型。Dixit(1970)通过比较古典和新古典两种视角下的二元经济理论,发现新古典主义框架下的Jogenson模型经济增长路径与古典主义Lewis模型相一致。Todaro(1970)的研究则发现在城市部门存在大量失业,且农村部门没有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非但不会刺激工业化进程,反而会加剧城市失业,同时危及农业发展。
Lewis(1979)重新回顾了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并着重探讨了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两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剩劳动力的来源和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距的持续性。Fields(1993)则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研究了收入增长的不均等,并将整体的不均等分为部门内部收入增长不均等和部门间收入增长不均等。Banerjee和Newman(1998)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引入了信息不对称,通过假设现代部门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传统部门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由代理费引致了一个效率与信贷约束的权衡取舍,进而指出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进入现代工业部门,自由放任的现代化难以最大化社会福利。Fields(2004)、Kirkpatrick和Barrientos(2004)分别从劳动力市场二元性视角和经济结构二元性视角重新检验了Lewis二元经济结构,发现模型的核心结论仍然稳健。Islam和Yokota(2008)则在Lewis的二元增长框架下考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重点探讨了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中国正迈向刘易斯拐点。Zhang等(2011)指出中国工资水平快速上升,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
国外学者的近期研究致力于从微观角度解释二元经济。Wang和Piesse(2013)尝试为二元经济结构建立微观基础,分析了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和人口增长,证明并区分了剩余劳动力,内生了现代部门工资决定机制,考虑了劳动力转移的动态并定义了两类“刘易斯拐点”。Fergusson(2013)强调农村地区存在不止一种产权制度,通过内生化产权制度选择,说明了劳动力的流动惰性与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性。Gollin(2014)通过人力资源在部门间的分配刻画了二元经济,并指出农业部门工作者受教育程度更低。Wingender(2015)的研究同样证实了人力资源分配的影响机制,指出正是由于农业部门中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强可替代性导致了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低于非农业部门。Yuki(2016)则动态化了二元经济结构,指出经济体的长期产出如何依赖于最初的财富和部门生产率分布。Diao等(2017)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部门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或结构调整式的增长,其中结构调整式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由低生产率行业到高生产率行业的重新分配,是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
国内学者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我国经济是否越过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指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是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分水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依赖于密集的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享受人口红利,其是否步入了刘易斯拐点在国内外学者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蔡昉(2007,2010,2015)发现中国经济转型的新阶段,正面临由劳动力供给过剩转为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困局,如果刘易斯拐点不仅仅特指一个时间点而是描绘某一个时间段,那么中国已经迈入了“刘易斯拐点区”。曾国平和曾三(2008)考量了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服务业与经济开放,发现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是服务业增加的主要原因。姚上海(2009)根据近期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变现情况推测我国正在迈入刘易斯第一拐点,尝试为我国农民工的“用工荒”现象提供解释。张永丽和景文超(2012)则认为我国已经迈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已经由过剩转向短缺,并不断向充分就业,劳动力供给不足迈进。
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学者认为我国目前劳动力供给充足,并没有迈入刘易斯拐点。樊纲(2007)认为我国农村仍存在大量劳动力剩余,因此我国将会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阶段,步入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刘洪银(2009)的经验研究证明我国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张广婷等(2010)也认同了这一观点。周燕和佟家栋(2012)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行业和地区间的工资差距仍然存在,经济并未越过刘易斯拐点。王必达和张忠杰(2014)同样证实了我国传统农业部门中仍存在剩余劳动力。周建锋(2014)认为“民工荒”浪潮并未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我国并未迈入刘易斯拐点。薛继亮(2016)则认为中国部分区域步入了刘易斯拐点,另一部分区域仍存在充裕劳动力供给,比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由于不同的原因都已经迈入了刘易斯拐点,而东北地区仍然处在劳动力净流出的状态。杨帆等(2017)认为我国经济中仍存在巨大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并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