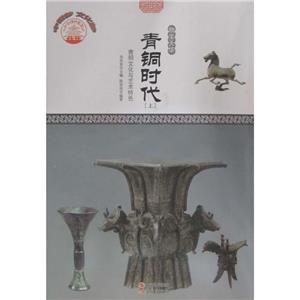作者:谢崇安
页数:387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ISBN:9787105085286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中国壮学文库: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笔者将今壮侗语族原生发祥地的先秦两汉时期之青铜文化考古发现,即把桂、滇、黔地区许多具有鲜明地方民族风格特点的上古青铜文化遗存界定为“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应似无大碍。 《中国壮学文库: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是立足于现代的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古发现而撰写的一部有关壮侗语族先民的上古青铜文化艺术史和文明史(约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1世纪)。其中叙述的内容实有部分的年代与铁器时代相重合,原因在于:当中原内地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的蓬勃发展期,但铁器时代文明对西南边区的影响还是微弱的,后者却伴随着铁器及冶铁术的输入而步入了其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鼎盛期,此后才逐步走向衰落。
作者简介
p>谢崇安 男,1953年生于广西柳州,
祖籍广东郁南。曾因“文化大革命”失学,
做过多年工人。恢复高考以后以同等学力
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广西
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
少数民族史、专门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专业硕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曾兼任广
西高级职称评委、广西学位委员会第九、
第十次学位授权学科评议员、广西社会科
学院特约研究员;为中国考古学会会员、
广西民族研究学会理事。
长期从事中国与东南亚文化艺术史、
民族史、艺术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代表
作有:《中国史前艺术》、《商周艺术》、《雨
林中的国度一一追踪东南亚古代文明》
等。曾在《考古学报》、《考古》、《中国美
术研究》、《学术论坛》、《四川文物》、《广
西民族研究》、《殷都学刊》等学术期刊上
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和承担过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三项、省部级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两项;曾获
本书特色
本书是立足于现代的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古发现而撰写的一部有关壮侗语族先民的上古青铜文化艺术史和文明史(约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1世纪)。主要内容包括:壮侗语族先民地区青铜文化艺术的起源,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年代分期,青铜文化艺术遗存所见的古代社会性质,青铜艺术的文化构造等。
目录
第二章 壮侗语族先民地区青铜文化艺术的起源一、广西地区古瓯骆族青铜文化艺术的起源二、云南地区古越族青铜文化艺术的起源三、贵州地区古越族青铜文化艺术的起源第三章 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年代分期一、云南地区古越族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年代分期二、贵州地区古越族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年代分期三、广西地区古越族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年代分期第四章 青铜文化艺术遗存的族属及其族群关系一、广西地区上古青铜文化艺术遗存的族属二、滇池地区上古青铜文化艺术遗存的族属三、贵州地区上古青铜文化艺术遗存的族属四、青铜文化艺术图像所见的族群关系第五章 青铜文化艺术遗存所见的古代社会性质一、国家文明产生的基础二、滇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性质三、青铜时代的社会缩影——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四、青铜艺术中所见之社会生产关系五、社会时尚:追求财富权势与奢华六、礼俗的形成与礼制性的建筑七、结论:壮侗语族先民地区进入方国的时代与政权
第六章 青铜艺术的文化构造一、艺术与原始宗教信仰二、以铜鼓为权威中心的方国社会三、有关农业的祭祀礼仪四、艺术是社会生活的记录五、青铜艺术中所见的民族习俗六、青铜艺术中所见的民族乐舞与节庆七、青铜艺术中所见的民族服饰
第七章 青铜艺术所反映的文化关系一、桂滇黔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二、西南上古社会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三、东亚南部青铜时代的族群与文化交往
第八章 壮侗语族先民青铜艺术的风格特征及其美学观一、青铜艺术繁荣发展的原因二、青铜艺术风格特征的形成和演变三、青铜艺术的美学观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节选
nbsp; 言
本书开宗明义首先要阐释的问题,应当说就是何谓“壮侗语族
先民”。
通常一般的论著和教科书都指明,“壮(僮)”族这一名词首见
载于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朱辅《溪蛮丛笑》等古籍。若往上
追溯,壮族在历史上还有俚、乌浒、僚、囗等许多不同的称谓,这些
称谓实际上已广泛包含了今壮侗语庞大族群的许多来源错综复杂
的原始先民,这些族称之间不仅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且同上古
先秦两汉时期之百越系族群(如西瓯、骆越等)更是有着不可分割
的族源联系。这一点,应当可说是今天学者们达成的一般共识(参
见《百越民族史》①等)。
有鉴于此,笔者将今壮侗语族原生发祥地的先秦两汉时期之
青铜文化考古发现,即把桂、滇、黔地区许多具有鲜明地方民族风
格特点的上古青铜文化遗存界定为“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
术”,应似无大碍。
本书是立足于现代的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古发现而撰写的
一部有关壮侗语族先民的上古青铜文化艺术史和文明史(约公元
前7世纪至公元1世纪)。其中叙述的内容实有部分的年代与铁
器时代相重合,原因在于:当中原内地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的蓬勃发
展期,但铁器时代文明对西南边区的影响还是微弱的,后者却伴随
① 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313~3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着铁器及冶铁术的输入而步入了其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鼎盛期,
此后才逐步走向衰落。
对于本书的命题和写作,可能还会有学人提问:面对桂、滇、黔
地区上古青铜文化考古的丰硕成果,本书的完成将会履行哪些学
术任务,具有哪些特点和价值呢?
首先,我们认为,目前需要一部综合论述壮侗语族先民的上古
文明史和上古文化艺术史的专著。因为,在传统民族学和历史学
的领域,尚未产生过广泛利用青铜文化考古资料来具体阐明壮侗
语族先民上古文化艺术丰富内涵的专门史。我们需要把许多零星
的相关考古发现及研究材料作系统的梳理整合,由此为人们提供
和充实壮侗语族先民从有限的文献史料无法了解到的许多历史的
真实图像和民族精神风采。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仅次于汉族的大族群,壮侗语民族也
书写过其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篇章,但限于史载的缺乏,在半个多
世纪以前,人们对此还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有在新中国建立后,考
古学取得卓越成就的今天,它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认识。这些
发现迫使我们要修改、补充和不断完善我们的西南民族史,“文明
的再发现”,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前人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明研
究的一些基本前提。
考古发现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中国文明的起源犹
如满天星斗,国家文明事实上是经历了从古国、方国到帝国的历
程。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除了
中原地区的汉族之外,周边民族都有其自身文明运动的轨迹,最后
才汇成中华民族文明的大实体。①过去那种夸大中原古文化,贬
低周边民族古文化的陈旧学术观点正不断地被考古新发现所扬
弃。这一真知灼见无形中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开
①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拓了创新的思路。因此,我们不仅是需要对过去的考古发现和研
究作全面的综述,也需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壮侗语族文明史
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判断和理论阐释。
通过本书的论述,人们会意识到,壮侗语族先民的上古文明史
已经能够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下,置于东亚南部历史
民族区的大背景下进行时空比较的考察。这对于研究中国文明史
和世界文明史的一般进化模式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国西南民族
古代文明史是前两项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阐明学术理
论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然而,这里笔者还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的研究仅能说是一个初
步的讨论和综述。2004年,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聘请著名学者严文
明、孙华、赵辉等教授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制订新的长期发展
规划书时,他们在规划书中就尖锐指出:中国边疆地区考古工作极
为薄弱,空白很多,迄今为止,甚至在国内也尚未能见到一部较为
全面系统的关于西南地区考古的专著。以此观点对照本书的论
述,人们也不难发现:事实上,西南民族上古青铜文化考古仍存在
着不少缺陷。例如,根据目前的出土资料,我们还无法建立完整的
西南民族上古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和年代分期框架,这也是后来
的研究者首先尚需直面的课题。细心留意的读者也会发现,本书
所作的青铜文化的年代分期,与部分学者的分期观点的确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此外,本书对中国西南民族上古青铜文化艺术遗存
所作的族属判断、文化阐释及种种理论分析概括是否得当,也可能
将会引发更多的讨论。
笔者还需要向读者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为何本书将侧重点放
在对青铜艺术品及其文化内涵、审美意识等方面的阐释上。这是
因为,考古发现中的西南民族上古青铜文化遗存,大多也是精美的
工艺品和艺术品,只有这些艺术创造才能成为西南民族上古文明
的伟大象征。本书对它们作出力所能及的诠释,不是为了将其读
者局限在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上,而是希望能获得社会各界人士更
多的认识和理解。
例如,在我授业的民族学专业学生当中,常有人会问道:“民族
学专业学生为什么要学习考古学课程?”这一提问使我回想到了二
十多年前的学习经历。那时严文明先生给我们四川大学1978级
考古专业的学生们讲授了一整学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是该
课程为我们奠定了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等知识的基础。然而,严
先生在课间却给我们放了不少民族学的教学录像片,其中的佤族
部落打冤家、猎头习俗、傣族制陶、烧陶器、西南民族的民居长屋等
片断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还记得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德麦琳女
士、云南民族学院的汪宁生教授也曾为我们举行过关于云南石寨
山文化及民族考古学的学术讲座。
不仅如此,除了繁重的考古、历史专业课学习,李绍明先生还
为我们讲授了一学期的“民族学概论”课程。李先生与宋蜀华先
生,都是在华西大学及其博物馆这一充满人类学(含考古学、民族
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人类语言学)学术氛围的环境中走上
了从事民族学研究的道路。在他们的师长前辈中有像冯汉骥、郑
德坤、闻宥、梁钊韬诸先生那样的著名学者。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
院系调整合并,使华西大学文科及其博物馆成了四川大学的重要
资源,其中早年在美国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冯汉骥教授,不仅是
我国西南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更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
的创始人,他后来培养了不少像冉光荣、童恩正那样能兼治考古
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优秀学者。梁钊韬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也
成了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和人类学系的创始人。他们的学生后辈,
许多人今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和民族学界的中坚。从上述的学术
师承就不难发现,人类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
而一度被打入冷宫或者边缘化,但其学术传统并没有中断。也就
是说,如果没有人类学的综合基础训练和人才培养,西南民族考古
就不可能会取得今天的丰硕成果,西南民族大部分已失落的古代
文明史就不可能重现天日;笔者若要完成本书的命题及任务也是
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过去老师们的教导下,笔者在多年的研究中,
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应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去从事美术考古学
的研究,在科研的实践中才深深体会到,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三
者并治对于解决民族学术问题的重要性。民族社会留下的“活化
石”能够从许多方面帮助对无言的考古学对象作出较合理的诠释。
反过来说,考古学家能够帮助阐明民族学现象的起源和发展;考古
学材料对于民族学家认识文献缺载的许多古代民族的现象,也是
重要的知识、研究方法和手段。“民族考古学”应说就是在考古学
和民族学研究相结合的趋势下而发展出来的一个学科分支。①基
于这样的认识,可以说,本书既是为研究民族美术考古而作,更是
出于为复原失落的壮侗语族先民上古文明的目的而写作的民族史
专著。
①何力编:《考古学民族学的探索与实践》.1~2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杜,
2005。 .
《中国壮学文库》序
壮学是在传统壮族研究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新兴的概念,是
一个新时代的学术话语。它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西壮学
学会的成立,而逐步步入学界视野的。它的产生和成长是学术发
展的必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它的构建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一、壮学: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
壮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据第五
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有壮族人口16,178,811人,占全国
少数民族人口105,226,114人(不含台湾省的少数民族人口)的
15.38%。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壮族最集中的地方,共有壮族
15,600,854人居住于广西各地,占广西少数民族人口的85.7%,
占全国壮族人口的96.43%。其分布状况为桂西稠密,桂东、桂
北稀疏。在广西,壮族人口占总人口90%以上的县,有靖西、天
等、德保、大新、隆安、龙州、平果、忻城、那坡等县;壮族人口占总人
口90%以下、80%以上的县市,有田东、田阳、邕宁、武鸣、东兰、上
思、凭祥、扶绥、上林等;还有14个县市区的壮族人口占总人口
80%以下60%以上。除广西外,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云
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麻栗坡、马关等县,西双版纳州勐
腊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云县,贵州省从江县,四川省宁南、
木里、会东、会理等县,陕西省柞水县红岩寺兰家湾等地也有少量
壮族分布。
壮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族源不仅可以上溯到有史时期的“西
瓯”、“骆越”,而且可以追溯到岭南的史前人类。千百年来,壮族及
其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或镌刻在祖国的锦绣河山,或以“西瓯”、“骆
越”、“乌浒”、“俚”、“僚”、“囗”、“僮”等名义,甚或是以“蛮”的名
义,记载在历代史籍当中,凭由人们对之考证和探究,为之感叹和
自豪。
然而,对壮族及其先民进行研究的历史并不长。严格的科学
意义上的壮族研究是在19世纪末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的脚步而到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如同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产
儿”(the child of colonialism)一样,壮族研究也是殖民主义的产
物。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沿印度洋和太平洋自西向东扩张,在瓦解
了印度、瓜分了东南亚之后,把贪婪的目光盯向了中国大陆。为了
巩固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统治,打通一条由东南亚直人中国腹
地的通道,他们开始研究我国南方各省的历史、地理、民族、语言、
习俗等问题,以作为军事侵略的先导。这些研究当中就包括了对
壮族的研究。1885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柯奎翁(A.R.Colquhoun)
著的《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ns)及伦敦大学拉古伯里
(Tettien de La-couperie)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导言《掸族的摇篮》
(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是目前所见的涉及壮族的最早论
著。此后,法国人邦德里(Pierre Lefevre Pontalis)1897年在荷兰
发表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 invassion Thaie Indochine)、英
国人戴维斯(H.R.Davis)1909年在英国剑桥出版的《云南:联结
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美国人杜德(W.Clefton Dodd)1923年在美国依俄华出
版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英国人吴迪(W.A.R.Wood)1926年在伦敦出版的
《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都论及壮族的族源和分布。
继西方人研究壮族之后,泰国人也加入了此项工作。有“暹罗
历史之父”之称的泰国共丕耶吗銮拉查奴帕亲王在1925年出版的
《暹罗古代史》中,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壮族。接着,泰国拍耶亚奴曼
罗阁吞写了《泰掸族系考》一文,大量论述了广西等地壮族的情况。
然而不论是西方人,还是泰国人,这时的壮族研究仅限于族源和分
布,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比较单一,所论证的材料主要是语言学材料
以及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基本上局限于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畴。
由于研究者都是以东南亚泰族为参照系,当他们发现壮泰民族有
密切关系后,即先人为主地把壮族归为泰族。因此,长期以来,壮
族研究在许多外国学者眼中,只能算是泰族研究或泰学的一部分,
这就决定了壮学概念的产生不可能来自外部。
壮学概念的提出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也是对“泰学”的反
正。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边疆
的蚕食,中国政府积极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富有爱
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以忧国忧民的情怀投入边疆少数民族的研
究。同时刊载于1928年7月号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
的钟敬文的《僮民考略》和石兆棠的《僮人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
开始壮族研究的标志。随后,丁文江于1929年《科学》杂志发表了
《广西僮语研究》,魏觉钟在1931年2卷3期《新亚细亚》发表了
《广西的民族——苗瑶僮囗》,石兆棠于1934年12月号《艺风》月
刊,刊登了《柳州僮人的片断的纪述》,刘锡蕃于1934年在商务印
书馆出版了壮族研究的最早论著《岭表纪蛮》,徐松石先后于1935
年、1946年、1947年出版了《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泰族
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香港东南亚
研究所发行),外国人对壮族的研究从此退居次要地位。此时的壮
族研究,范围上突破了前一阶段外国人的研究,涉及了壮族历史、
语言、习俗、宗教、婚姻家庭及壮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在研究手
段和方法上,田野调查兴起,实地调查材料与历史文献得到了较好
的结合。以学科的投入来看,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紧密配合,
共同研究,使壮族研究别有洞天,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成就最
大的要数徐松石,他不仅灵活地运用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创造
了“地名研究考证法”以论证壮族的历史,而且以民族的田野调查
方法、语言对比法、风俗对比法对壮族的族源、历史、社会、文化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潜心于壮族研究者人数较少,其贡
献能与徐松石相提并论者,更是凤毛麟角,研究的深度不够。更重
要的是,受中原汉文化中心史观的影响,即便是当时壮族研究最有
成就的徐松石、刘锡蕃亦不能免。“僮佬也确是千真万确的汉族”、
“僮族非但是远古岭南的土著,而且是今日最纯粹的汉人”等因汉
文化中心主义偏见而导致的含混不清或自相矛盾的观点,大大局
限了他们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成果的深化。因此,当时的壮族
研究顶多只能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一部分,
不可能有壮学概念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民族
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壮族被确认为统一的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
平等的一员,享有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随着壮族历史新
纪元的到来,壮族研究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1951年,中央
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到壮族地区进行慰问,随团的专家、学者调查
研究壮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和现状。最著名的例子是广西分团副
团长费孝通教授根据调查撰写了《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
考》,发表在《新建设》1952年第1期,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
学、考古学的资料对壮族的起源进行推考,认为壮族是古代东南沿
海越族“余留到现在的一部分”。此后,在1953年开始的民族识别
和1956年开始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过程中,政府都派出工
作组或调查组对各地壮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整个20
世纪50年代,由政府支持和组织的大规模的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取
得了大量的资料,为壮族研究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基础。在此基础
第四章青铜文化艺术遗存的
族属及其族群关系
一、f-西地区上古青铜文化艺术遗存的族属
经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许多学者都认为,两广地区与
越南北部先秦两汉时代青铜文化遗存的主人都分属于古代百越民
族的几个支族,如广东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其族属是为
南越族遗存。
在今广西地区,蒋廷瑜先生认为,本区域的越族似可分为西瓯
和雒越两部分。西瓯越人主要是分布在南越之西,雒越之北,楚国
之南,恰当今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其代表性遗存是广西平乐
银山岭战国秦汉墓地的青铜文化遗存,它们的文化面貌与发现于
广东西江中游的德庆、肇庆、四会、广宁、罗定等地的战国秦汉墓地
的青铜文化遗存相互类同。①
蒋廷瑜先生认为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可进行分区的观
点,近年得到了李龙章先生的进一步阐发。然而,李龙章在对考古
学文化遗存进行文化区系、类型和分期断代研究的基础上,却改变
了上述的一些关于广西青铜文化族属的传统看法。
他认为,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的文化遗存的属性,因其地
理位置关系,当属云南青铜文化和两广越族文化的过渡类型。李
①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载《考古》,1980(2)。
龙章明确指出,广西武鸣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出土的夹砂圜底器与
两广青铜越墓所出土的陶器判然有别,但与滇池地区、云南元江流
域青铜文化墓葬所出土的陶器就很相似,其他一些文化因素亦然。
谈到这些青铜文化遗存的族属问题时,李龙章总结前人的观
点认为,西瓯越人分布在桂东,而雒越分布在其西南。而且,雒越
不属于百越族群,应与滇族一样同属于百濮族群。
他特别引述了前人关于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的发现及其相关
族属的考证。该文强调,西林普驮铜鼓墓的出土物,去除其中的汉
文化因素外,基本上与两广的青铜越墓无共同之处,而与滇文化有
较密切的关系。今广西西林普驮地望古属西汉时期的“句町”,《:华
阳国志·南中志》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也,其置自濮,王姓毋,
汉时受封。”故李龙章从张世铨等学者之说,认为西林普驮铜鼓墓
的族属当为濮族。①
然而,笔者细审西林普驮铜鼓墓发掘报告,②认为其中若干重
要文化因素,仍可在桂东及越南北部的青铜遗存中找到它们彼此
间的相似之处。
首先是铜鼓,它属石寨山型,此型式铜鼓在广西与越南北部都
有着广泛的分布,它们分别见于百色田东锅盖岭、③宜州冲英村、④
桂东贺县龙中岩洞、⑤贵县(今贵港)罗泊湾⑥诸战国秦汉时代遗
存中。
①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载‘考古学报》,2004(3)。
②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载《文物》,1978(9)。
③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葬》,载《考古》。1979(6)。
④李楚荣:《广西宜州发现的铜鼓、画马崖画与古代马市、驿铺关系初探》,载《广
西民族研究》,2001(2)。
⑤ 贺县博物馆:《广西贺县龙中岩洞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93(4)。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26~27页,北京,文物出
版社,1988。 此外,它在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诸遗址中也有众多的发现。①
这类起源于滇池西部地区的早期铜鼓在西江中上游与越南北部地
区被发现,再次证明了古越人与西南夷中的农耕民族有着不可分
割的联系。
其次是羊角钮钟。这种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乐器,它们
在广西浦北、容县、柳州、贵港、西林、恭城以及与广西相邻的广东、
越北等地都有发现。
其形制都基本相同,如钟体呈半节橄榄形,上小下大,平口中
空;顶部有两个外撇三角状钮。钟体上多素面;有的面部饰S形云
纹,下部饰弦纹(容县);也有的铸有翔鹭、云雷纹、弦纹或人形图
像,与铜鼓纹饰有共通之处。
在广西宁明县明江河畔的高山及花山等地崖壁画上,也绘有
这类青铜羊角钮钟图形。学者多认为本区域的羊角钮钟流行的年
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铜鼓与羊角钮钟与其说是濮族的文化因
素,还不如说它们是最能代表越族文化的主要特征。相较而言,此
前,我们在濮族的故地,楚国的西部地区却找不到这样的文化组合
因素。汪宁生先生曾指出,楚将庄囗王滇,变服从其俗,正是楚国
“启濮、开濮”的继续和发展。我们认为,桂滇黔地区上古青铜文化
呈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也是一种多族群认同过程的反映,楚将庄囗
王滇,变服从其俗,所认同之当地土著民族应为越族,其所率之楚
人部众当包括原楚西部之濮人。
① [越]黎文兰等编著,粱志明译:《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125、131、134、
122页,河内科学出版社,1963。
②覃义生:《战国秦汉时期瓯骆宗教性青铜器探微》,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