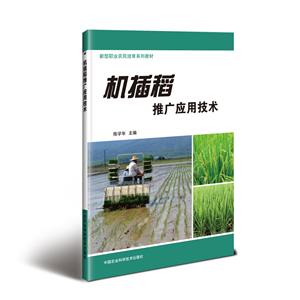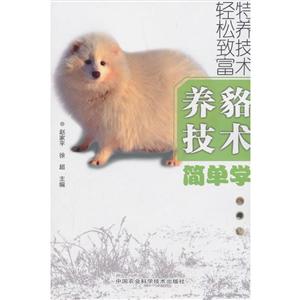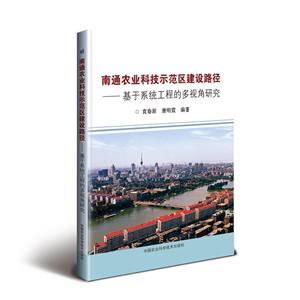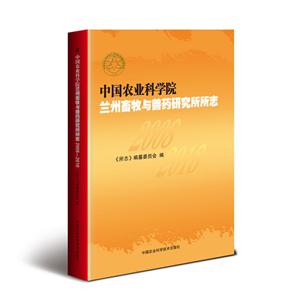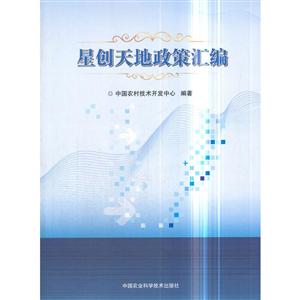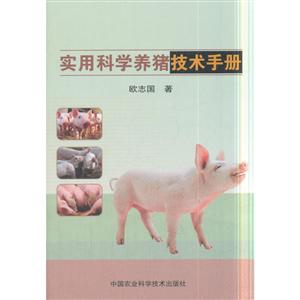作者:邱建生
页数:366
出版社: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ISBN:9787511636690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该书介绍我国乡村建设的起源和发展,介绍了民国乡村建设的情况,重点介绍晏阳初等人的实践及后人实践的经验与成果;介绍了乡村建设思想和乡村建设哲学;介绍了农村现状及期待发展的问题,介绍了作者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的经验和实例。该书对促进农村发展,对更好理解和解决三农问题有建设性意义,可供参与新乡村建设的实践者、研究农村发展的研究人员参考。
作者简介
邱建生,博士,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教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爱故乡计划发起人,一直从事乡村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先后参与了3个重大项目、1个重点项目、1个985项目,主要在研项目3项,发表文章CSSCI核心期刊作者2篇、第二作者1篇,CSSCI扩展11篇。2000年起,在北京、福建等地举办乡村建设沙龙,创办“中国乡村网”,参与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工作;2003年起,到河北定州筹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负责乡村建设试验区的工作,以村为单位开展以组织创新和教育创新为主题的新时期乡村建设试验工作;2006年起,受海南儋州市人民政府邀请,到儋州开展以县为单位的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工作,创办农村型社区大学;2007年起,在厦门工业区创办工友之家,为工友提供包括社区教育在内的各种服务,目前工友之家已覆盖八个城中村,人口30余万;2009年,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培训基地,开始系统培训南方的乡村建设人才;2010年,在福建连城创办培田社区大学,开始农村学习型社区建设及乡土价值的重建工作;2011年,在福建莆田创办汀塘社区大学,推动基层的社会管理创新;2012年,在福州分别创办了金山工友社区大学和故乡生态农园,在江西市民社区创办大湖社区大学;2013年,发起爱故乡计划,推动“发现故乡之美”、“爱故乡年度人物评选”等活动的开展。
目录
在余烬掩盖的火上——遇见民国乡建
为中国找回晏阳初/
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在某些方面的异同简述
——兼说革命与改良/
改良变革中国
——晏阳初及其同仁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
晏阳初的“民力”观/
我们要往哪里去
——写在晏阳初诞辰120周年之际/
荒原颂歌——我的农村
我的农村:理想的生活长什么样?/
故乡力量
——珍视、守护、发扬/
故乡·母亲/
培田的价值/
漂泊者的居住理想/
行动是坚强的翅膀——乡建工作散记
农民如何组织起来/
一场未完成的乡村试验
——翟城乡村建设试验区综述/
乡土价值重建
——培田客家社区大学工作纪实/
农村教育的忧伤和希望
——培田客家社区大学承载的使命及其工作简述/
使无力者有力,有力者有爱
——厦门国仁工友社区教育促进项目介绍/
如何筹备一所乡村社区大学/
乡村图书馆的组织和管理/
平民教育十年散记/
工作总结/
平民教育文化丛书大纲/
《乡村》编辑方案
——乡村,让人类更美好/
关于“我们的乡村建设”的几点意见/
缙云山会议发言/
晏阳初中心的“一二三四五”/
梦想像呼吸——乡建“哲学”
乡村建设是什么/
“乡村建设八问”/
平民教育是什么/
社区大学的理想/
平民教育与新农村建设/
平民的教育怎样才能不沦为口号教育?/
爱故乡的理想/
爱故乡宣言/
爱故乡的未来/
爱故乡行动倡议/
乡村建设随想录/
新乡村建设工作手册/
农者之心/
我们的时代
——《国仁工友之家三周年图册》前言/
青年有理想,故乡有力量
——向日葵爱故乡学社创刊词/
忧郁的自由之火——乡村杂谈
被教育捆绑的村庄/
重建家园
——让“留守”这个字眼消亡/
农村成功学/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乡村思维/
城市精神贫困的根源及其影响/
人民大学,人民的大学/
无教与误教
——罗斯高教授《63%》一文读后感/
和平的知识基础/
乡村振兴,别成为新一轮的折腾/
点点微光——乡土思想
城乡共生与在地化教育系统建设初探/
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探讨/
在地化知识与平民教育的使命/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乡土文化与乡村治理/
乡村主体性视角下的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在真实中追求幸福——乡村参访录
信仰的高度
——印度归来/
美国之行/
中国台湾归来/
梦想像呼吸,行动是坚强的翅膀
——中国台湾社区大学参访报告/
举社区之力
——中国台湾社区营造考察报告/
附录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筹办日记/
后记/
节选
为中国找回晏阳初
2010年是晏阳初先生逝世20周年,也是其开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90周年。但综观国内纸媒、电媒或网媒,却没有一篇纪念性的文字。尽管与10年前我们开始新乡村建设工作比起来,社会对晏阳初先生的认知度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他仍然是故纸堆里头的一个小人物,不为人们所注意。当4年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提出时,人们一窝蜂地往韩国跑,去学习那里的新村运动,却少有人愿意去注意一下供在自己家里的韩国人的老师——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早已是世界的宝贵遗产。
伟大的思想不能为同时代的人们所理解,这是正常的,因为思想在高处,而人们只在平地觅食。可悲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的围栏里,平教会、晏阳初、定县实验……这一思想却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了。
但思想是光,它总要从黑暗中透过来。 晏阳初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是当我们回望20世纪的中国时,能够使心灵感到温暖的少数几束光中的一束。今天,中国并没有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走出来,广大的农村许多地方“愚、穷、弱、私”现像严重,民智尚未全然开化,民力没有得到足够发挥,而民主的建立更是任重道远。因此当我们展望更远的未来,这束光的亮度尤令人兴奋不已,这一思想不应从我们的天空遁迹。
陌生的现代伟人
1928年6月20日,晏阳初出席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典礼,领受荣誉文学硕士学位。赞扬词是这样写的: 晏君自1918年在耶鲁膺学士学位,今已届十周年,极少的毕业生在十年间的成就,可与这位具进取心、富有才能,而且又不自私的人相提并论;他是中国平民教育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东方的贡献可能比战后任何一人都伟大;当他在法国以青年会干事与中国劳工相处时,设想出对中国文盲的教育观念;他在中国雅礼会所在的长沙,开始作平民教育大运动,迅速扩张成为全国性事业;他自繁多的中国文字中简要选取一千字;在这平民教育制度下,200万中国人已经学会读和写本国文字; 晏君实是世界文化中一有效能的力量。
1943年5月24日,是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日,晏阳初在这一天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道被评为“现代对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表扬状上写道: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他又是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这些荣誉虽是加给晏阳初个人的,但正如晏本人所说,这是给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是对其自1920年以来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的嘉许。
1945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全国民众教育委员会,聘请晏阳初为主任委员,并要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南京设立办事处,以便与教育部随时联络。
1945年11月,联合国文教组织在巴黎举行首次会议,晏阳初的助手瞿菊农是中国代表之一。此次会议以中国平民教育的经验为蓝本,制订了文教组织基本教育计划,以在世界未开发地区推行基本教育,以扫除文盲、灌输基本教育为目标。晏及其同仁在国内开展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已然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并开始影响世界。
1989年10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致电晏阳初,祝贺晏99岁寿辰,贺词中称:您一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平民,给了众多美国人极大的鼓舞。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您已使无数人认识到:任何一个人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您是我们人类的颂歌,是你们同行的楷模。
70年,只做一件事
从1918年在一战战场的华工营,到1990年在美国纽约去世,70余年,晏阳初只做了一件事,即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
在法国华工营,晏阳初在服务华工中受到华工的教育,他开始认识中国的“苦力”,他们虽“苦”,但身上却潜藏着巨大的力量,只因教育机会的缺失,这种力量得不到发挥。晏阳初用“脑矿”来形容他的这一发现,对中国来说,这种发现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因为长久以来,中国的劳动阶层被隔绝在知识之外,被认为是“无用的人”,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连劳动阶层本身也看不起自己,总是渴望一个“救世主”来解救自己;而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则高高在上,总是以一种“解救者”的姿态出现在劳动阶层面前。
青年晏阳初则在这些“苦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立下志愿,回国后不升官不发财,只为发扬“苦力”的“力”奋斗终生。
晏阳初1920年回国,当时五四运动之后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农村在资本和官僚的挤压下正陷入衰败,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当时的中国,有85%的人不识字。晏阳初的工作,就从“除文盲”开始。他首先从中国众多的汉字中挑出1 000个常用的,编成《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然后分别在长沙、嘉兴、烟台几个城市进行扫盲试点,成效卓著。
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任总干事,以后几十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晏阳初一直以这个身份在国内开展工作。平教会成立后,晏阳初的工作重心逐步从城市转到农村,因为农村人口占了80%,农村有90%的人不认字,农民普遍在破产的边缘。
1926年以后,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今定州)为根据地,以县为单位,开始了综合的社会改造试验,史称“定县实验”。“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是对“定县实验”较好的概括,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连锁并进,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统筹进行。其逻辑是,农村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全局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谋求综合的解决之道。
晏阳初从国民性的角度,把当时中国人的问题概括为“愚、穷、弱、私”四大病症,这病怎么来医治,晏阳初认为教育是根本之道,所以“定县实验”的核心只有两个字:“教育。”但教育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与建设合谋,教育为建设服务,建设反过来促进教育。所以我们会看到“定县实验”中更多的是建设工作,如品种的改良、灌溉工具的改良、棉花购销合作社的组织、乡村保健室的设立,而教育则蕴含在这些建设工作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备受国际推崇的赤脚医生制度,广受国内NGO采用的参与式社区工作方法,以及国务院扶贫办近些年的“整村推进”计划,联合国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为消除贫困所做的努力,我们都可以看到“定县实验”的身影。
在“定县实验”最鼎盛的时候,定县聚集了近500位知识分子,其中有60余位是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大学教授、校长等,所以当时的媒体把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称为“博士下乡”运动。而让这些既富于创造力,又特立独行,以自我为中心的一流人物一起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晏阳初需要花费1/4的时间“逐渐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服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教会撤出定县,转战湖南、四川,后在重庆北碚的歇马场落脚,创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工作向深处发展,以定县工作的经验为基础,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同时开辟“华西实验区”,直到1950年。
“华西实验区”时期,平教会开始进行“土改”试验,以和平的方式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分给农民。后来台湾的土地改革,直接借鉴了平教会在大陆的土改试验。而台湾土改被认为是世界学习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晏阳初以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其在国内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经验,在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乡村建设人才。
1990年,晏阳初在纽约去世,享年100岁。
爱总会找到一条路
延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晏阳初等人的社会改良工作并不以为然,批判之声不绝。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暴力革命是唯一的选择。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我们会看到革命成功后,那些非革命党基本上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晏阳初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衔”就有“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等,他留在国内的学生也命途多舛。
而晏阳初却在心里认为:“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一段话论及法国大革命:结果,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这段话用在中国的革命上,大抵也是可以的吧。
100多年前,梁启超作《新民说》,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晏阳初无疑对这句话有颇深的印象,他说:一切问题自人而生,欲求问题的解决,自当在人身上来下功夫。所以平教会自始至终,都把“作新民”作为目标。中国要在真正意义上摆脱宿命般的治乱循环历史,在根本上发生变革,唯有走改良的道路。
晏阳初将双脚迈进了饱受欺凌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乡村,他的手里没有枪,只有《平民千字课》,脑子里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民众的疾苦和西方的民主理想。他就这样和他的同志们在河北定县农村一待10年,在湖南、四川农村一待又是10几年,以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一待又是40年。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着晏阳初70年如一日地行走在平民中间?这条路布满了荆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走的,而晏阳初却一走70年,直到生命末了。“具有真正和完全的爱心的人不求自己的益处”,晏阳初的一生正是背着十字架在爱中行走的一生。没有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强大力量,没有人可以持续地如此迈出脚步。更重要的,晏阳初并不是在痛苦中行走在平民中间。在《九十自述》中他说:我愿意化苦为乐,化敌为友。
晏阳初选择了悲悯作为他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他对其时代的贫穷者及其他弱势人群所采取的行动。在这悲悯中,我们看到的是晏阳初舍己的爱。爱总会找到一条路,这是当我们回望历史时,晏阳初留给我们的启示。
晏阳初与今日中国
很多人会以“时代不同了”这句话简单地把晏阳初们的努力对今日中国的启示带过去,认为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这些先辈们仅仅属于过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使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倡导中,也没有这些先辈们的任何身影。
如果把晏阳初们的工作简单地理解为“扫除文盲”,确实,这时代是大不相同了,今日中国已没有多少人不识字。如果把晏阳初们的工作简单地理解为“在农村扶贫”,确实,今日中国的扶贫工作已得到联合国的嘉奖。晏阳初们提出并践行的计划大大超越这些目标,而且这些计划经过实践的检验,切实可行。这些计划的目标被概括为: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建立民主,改善民生。
今天的中国,“人的建设”工作还远未完成,这恰恰是晏阳初的工作核心。“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适合民主,但我知道他们想要民主……在中国,各种力量(包括好的和坏的)正在进行较量。只有人民大众有机会接受文化和公民品德教育的时候,中国才能实现民主。”今日中国,距离晏阳初的理想有多近?
我们这个时代,发现问题的人很多,解决问题的人太少,特别是知识阶层,这个理应天然具有社会使命的阶层,频繁出没于资本和官僚的觥筹交错之间,把自己的“根”——大众——抛诸脑后。80年前的“博士下乡”盛况,已难觅其踪。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女士在《告语人民》的结尾呼吁: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晏阳初及其同事制订的实用的计划的确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晏阳初曾这样描述与他在艰难困苦中始终相伴的妻子的一生:“那美好的仗,她打过了,并始终持守自己的信仰。她留给人们的是一种祝福,她的一生,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激励。”这也是晏阳初生命的真实写照。
原载《南方窗》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