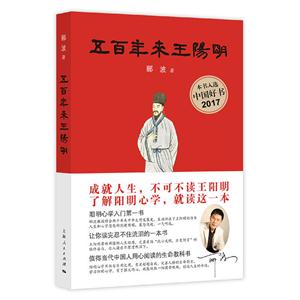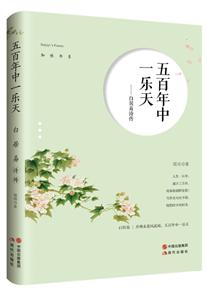
作者:殷靖
页数:249页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514370607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唐代诗人白居易一生的传奇,一个具有胡人血统的平民诗人,让唐诗在国势衰落的轨迹中,再次腾飞向上,不能不说他具有“魔王”一般的功力,而“诗王”、“诗魔”的称谓也应证了他对唐诗的改造过程和承认。白居易拓展了诗歌的体裁,皇室爱情、平民疾苦,都在他笔下被还原,而他生命的波折,也让人感叹时代造就了一个不一般的诗人。 伟大的诗人不会去选择时代,而是在时代中造就自己。白居易适逢乱世,但他并不因为身处乱世而悲哀,而是用他的笔和才思,去忠实记录乱世的根源,并对受苦难的人民给予了无限同情。 诗人终究老去,白居易也在争鸣中走向历史的深处,但诗人的传奇却没有散去,而是随着他的诗歌永远在文学的天空里飘荡,在人们的记忆里不断翻新。
作者简介
殷靖,擅长写人物传记、历史、青春、商战方面的小说,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较多,在《今古传奇》杂志上发表过国际共运人物传记系列,获得好评,也在《知音》、《儿童文学》等全国知名杂志上发表过纪实文学作品,出版过《汇率保卫战》、《100件男孩应该知道的事》等书籍。
本书特色
在唐代,白居易是李白、杜甫之后的伟大诗人,他留下的文学遗产,数量众多,他的人生经历也丰富多彩,品性耿直幽默。 千余年来,人们都热爱着这位大诗人,爱他至真至诚的性格,爱他至纯至洁的心灵。因此,真实还原这样一位刚正不阿,豪放不羁,令人敬仰的诗人,便是一件极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
目录
《日出东方别样红:白居易诗传》 2
第一章 生不逢时运偏乖,才华横溢少年郎 2
第一节 春风吹起诗情 2
第二节 早熟少年,诗书前尘如一梦 4
第三节 烽火乱世,书写丧失的门第 8
第二章 远为江海游的漂泊 11
第一节 长安不易居 11
第二节楚山吴江乱世情 12
第三节 岁月颠簸的洗礼 17
第四节 春风得意的科考生活 20
第五节 抱月远行的人生起落 22
第六节 无法了却的诗愁 27
第三章 百姓优乐只在心 30
第一节 初入官场 30
第二节 寂静的春天 34
第三节 官虽小,心向善 39
第四节 探索沧桑中的柔情 42
第四章 道是无情却深情 45
第一节 断肠泪,辜负人间真情 45
第二节 光阴成就了感情 49
第三节《长恨歌》传奇 53
第四节 最是柔情压不住 62
第五章 诗王的讽喻诗 65
第一节 走进官场死胡同 65
第二节 摆脱固有格律的束缚 67
第三节 诗是反抗的利器 70
第四节 万家优乐在心田 73
第五节 为底层受苦的人歌唱 76
第六章 高山流水觅知音 79
第一节 难以解释的误会 79
第二节 惺惺相惜的知己 82
第三节 以文会友,诗人才情大比拼 87
第四节 超越时代的巅峰之作 94
第五节 才情比拼的谢幕 97
第六节 人间最重是友情 102
第七章 归去,清风明月泛舟游 104
第一节 只留白堤惠天下 104
第二节 诗情画意醉江南 107
第三节 隐,不求闻达 110
第四节 固守属于自己的快乐 115
第五节 怡然自乐的晚年生活 119
第六节 知足长寿,乐而忘忧 122
节选
第一章 生不逢时运偏乖,才华横溢少年郎第一节 春风吹起诗情大唐,带着蹒跚的脚步,来到了生命的中期。此时,曾经拥有的豁达开放的大气,已经被安史之乱所弥漫的胡虏之气虐杀殆尽,只剩下苟安残喘的哀怜。盛唐气象下唐诗的绚烂光华,已经成为昨日黄花,纵有千般诗才,面对着倾颓的国势,也唱不出如花般的面目。唐诗,似乎无可奈何地走向黄昏。此时,一个肩负着唐诗振兴的少年,面对着苍茫古原上的连天碧草,以梦想为帆,抒写着自己的情怀与理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在少年看来,大唐的盛景,如同眼前的原上草,枯荣有命,难以预料。纵使野火焚烧,留下焦土一片,但只要春风又起,一片翠绿又何尝不能重新装扮草原呢?而重新装扮大唐新气象的,又何尝不能是自己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眼前的年轻人也知道,要重现盛唐气象,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他站立在被荒草侵没的古道上,才会发出“晴翠接荒城”的感慨。曾经遍地繁华的大唐城市,如今是肃杀一片,这肃杀的空气里,有着军阀割据的血腥,有着大唐落日的哀鸣,更有着一片赤子之心难以报国的无奈。为什么?因为这个少年是胡人。大唐曾经以豁达开放的风气,成为那个时代最为人向往的国度。那时,唐帝国长安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聚集着从西域各国来做生意的商人、学习的留学生,更多的是来朝拜的西域部落首领。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在大唐朝廷做官,而且还因为仰慕大唐风采,甘愿长留大唐,成为大唐的子民。但是,安史之乱后,“非吾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腐血统论又开始主宰着朝野,虽然还没有明确规定只有汉人才具备当官的资格,但在提拔官员时,对于有着胡人血统的人是刻意提防的。于是,盛唐时胡风满长安的景象,只能留在人的记忆里了。眼前的少年,因为自己拥有胡人的血统而惆怅,但心中的雄心,又让他不甘心就此沉沦,祖先多年羁绊中华,血管里的血液,早就被华夏之血浸泡,相貌举止早就被汉风洗涤殆尽没了胡人气息——胸怀大志的他,又怎能让缥缈的外来民族的基因,阻拦自己奋发向上的进程呢?正因为如此,少年选择了离别,告别了眼神里满是担忧的双亲,踏上了凶险的前程之路,“萋萋满别情”虽然浸泡着难以割舍的儿女情长,但却挡不住少年冲天一怒的豪情。看着眼前被战争摧毁的城邦,回想着在父母膝下安宁的生活,别离的悲伤虽然涌上心头,但儒生报国情怀,让他能按捺住这种悲伤带来的退缩,只求用自己的双肩,能担负起大唐的兴盛。这个少年就是白居易。白居易生长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饱受着战乱的折磨。想当初,自己的祖先就是为了追寻大唐的乐土,才抛家远行,来到大唐这最具吸引力的国土。原本想求得一个世代能永享和平的环境,却不想到了自己这一代,铁马钢甲呼啸,金刀羽箭飞舞,那种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无明天的颠沛流离,让人觉得活着了无乐趣。大唐余荫尚在,白居易的父亲还能做到一些小官,虽然无法大富大贵,但养家的能力还是有的,只不过不能留守家庭,需要在外奔波。就这样,白居易的童年很少与父亲相伴,只是跟着母亲长大。白居易的母亲对他期望很高,总希望他能依靠才学,冲破那对胡人歧视的牢笼,好让家族扬眉吐气。于是,只要对他有用的书籍,从不让他错过。诗词歌赋,仕途学问,在母亲的督促下,白居易都没有放松。也正是在慈母严峻地教导下,白居易快乐地成长着。天才少时就展露聪颖之气,似乎不这样,就不能显示其与众不同。白居易也不例外。在他只有七八个月大的时候,乳母就抱着他,来到堂屋的书屏之下。文人之家,书屏是第一之物,而白居易对上面龙飞凤舞的文字大感兴趣。当有人指着上面的字给他看时,他虽然还不会说话,却已经默识了。文人的种子,已经发芽,白氏家族的人,似乎已经听到了未来诗坛文豪踏踏而响的脚步声。白居易生不逢时,大唐的实力江河日下,不但不能以怀柔政策笼络大唐境内的胡人,甚至对胡人严加防范,而愚朽的士大夫那种夷夏大防的观念又开始抬头,在任何场合都开始排斥胡人,羞于与胡人为伍。在这种场合下,有着胡人血统的白家想出头,自然是难上加难,作为朝廷小官员的白居易的父亲,也就没有了高升的可能,只能以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正是这样的境遇,让白居易没有了依仗家庭官位而飞黄腾达的可能。好在大唐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即科举制。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有了做官的可能。而且,这种官员资格考试,基本上是没有门第限制的。科举考试,为白居易及其白氏家族打开了通往大唐仕途的一扇门,哪怕是拥有胡人血统,只要通过了科举考试,做官,还是有希望的。第二节 早熟少年,诗书前尘如一梦白居易的家族好文,家学源远流长,正是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使得天资聪颖的白居易从小就好学苦读,对儒家经典,了如指掌。再加上父辈官职不高,和下层民众比较接近,使得白居易对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更容易产生同情,这对他今后的成长,起到了决定作用。从少年时代起,白居易就和历史上有作为的儒生一样,具备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如果是处在和平时期,以白居易的聪颖,一定能如初唐神童骆宾王那样写下清雅、秀丽的诗篇。但时值动荡,军阀混战的年代,大唐天下之大,却没有一刻安宁,也没有尺寸的平安之地。所以,少年白居易的笔端,只有控诉和愤懑: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白居易《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这是白居易十五岁时写下的一首诗,内容是怀念远在异乡的兄弟。十五六岁的年纪,即使境遇不佳,也应该是欢乐较多、愁怨较少的时期。但战乱把一切的美好都摧毁殆尽,兄弟分离,无法相见,只给他们留下了割舍不断的怀念。在战乱时期,楚水吴山已成天涯,兄弟不能相聚,道路荒芜。一封家信,写不下满腹的关怀,只留下数行相思泪。诗最能反映社会现实,盛唐时候的大唐诗篇,激情飞扬是主流,即使有追求超凡脱俗的人,也多数感叹的是生命短促。而白居易所处的时代,让这个原本处于青春飞扬时期的热血少年的诗篇中,却满是老年的颓唐气息。如果不加考证,我们哪里会想到,这是一个不足十六岁的少年所作呢?虽然残酷的现实,让白居易下笔呆滞,但衰败的大唐,还没有磨灭他那颗少年济世的雄心。白居易的眼光,始终关注着大唐朝廷,仰慕那些出将入相的大员,希望能和他们比肩,治理天下,让大唐重振雄风。白居易转眼到了十六岁的年龄,古人早熟,十六岁已经是一个可以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尤其在战乱的年代,如果不早作打算,要么蹉跎一生,要么沦为军阀残杀的牺牲品。因此,白居易决定离开家乡远行,到帝国的首都长安去开启自己的征程。十六岁的年华,就要独自面临帝国发展变幻莫测的风雨,更要为自己的前程找到正确的方向。大唐今不如昔,风雨飘摇。善于见风使舵的人,会选择抛弃大唐,寻找胳膊粗的军阀作为依附;而白居易胸中安民济世的雄心,让他无法与那些乱臣贼子为伍。正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当年祖先冒死来到大唐的信念,让白居易认为自己能承载起帝国复兴的重任。正因为如此,满怀信念的白居易,坚信自己今后能成为大唐的风云人物。在白居易漂泊四方期间,除了哀怜民生的艰难外,还对卓有建树的封疆大吏尤其仰慕,而这也是其少年壮志的积极反应。当时的苏州牧韦应物是一位诗豪,为人大气,一首“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奠定了他在诗坛中的地位,其诗坛才气已经足够人仰视,而其仕途发达,成为一方郡守,位高人尊,更让文人雅士钦佩。少年白居易,在游历苏州时,远远地望见韦应物大宴宾客时的排场,便不由得羡慕万分,钦佩其“才调高而郡守尊”,认为这才是读书人的楷模。一位不出名的少年郎,能够仰慕郡守的儒雅风流,不正显示了白居易的高尚追求吗?战乱中的渴望,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心境,白居易对诗人兼太守的韦应物的仰慕,等于给自己树立了人生的标杆。如果在盛唐时期,以大唐的胸襟和白居易的才情,做到韦应物这样的官位,应该问题不大。但此时,大唐自身难保,而且引起这样的祸端的就是胡人安禄山,夷夏大防的思维定式,使得大唐的汉人官员开始提防异族人,而这也导致白居易的理想终将成为空想。此时,白居易也敏感地察觉到了大唐用人风气的变化,心里有了隐忧。他在衢州陪伴为官的父亲时,看到父亲以小吏的身份,忙进忙出而不得歇,不由得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两首抒怀诗: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白居易《相和歌辞?王昭君二首》这是两首写王昭君胡汉和亲故事的诗,也是诗坛常见的借古喻今题材的诗。两首诗的诗风充满了肃杀和悲愤之情,全然没有才子欣赏佳人的那种轻松心境。要知道,此时的白居易正是翩翩少年,胸怀雄途之际。但诗中却没有表现出冲天的豪情,反而充满了一种无奈。然而,这却也正表现出了白居易当时怀才不遇的心境。古时读书人与美人的境遇都是一样的,“女为悦己者容”,生就一副好相貌的女子,能走入皇宫大院,成为帝王的妃子,就算是走到了人生的巅峰。更何况在盛唐时,杨贵妃得玄宗专宠,杨家鸡犬升天的事例还在眼前。王昭君色艺双全,论美貌,应该不逊于杨贵妃,但却在深宫无人问津,皇帝美女众多,也不会顾及她的哀怨。所以,她唯一的出路就是远嫁塞外,只求不辜负青春。王昭君作为一个有着非凡容颜的美丽女子,却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虽然和亲的队伍代表着汉天子,但那荣耀却与她无关。一串串远行的脚印,代表着离开了繁华的首都和故乡,那一片漫无边际的沙漠越来越近,谁都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什么,但她却无法回头……草原、风沙,孤独、等待,这就是她的命运,注定与繁华无缘。作为一个南方山区长大的女子,王昭君只见过家乡的山水,面对大漠风情,她有些手足无措。而脑海里根深蒂固的夷夏大防的观念,也让她为自己的不幸命运感到悲哀。站在风沙当中,她抚摸着被风沙吹打的容颜,清澈的眼眸凝视着遥远的家乡,知道这一去,除非有奇迹,否则将不会再有回去的希望。蓝蓝的天空,时隐时现的羊群,牧羊人粗犷的歌声,虽然是见所未见的美景,但毕竟不是农耕生活下的子民所乐见的景色;起伏的绿色、洁白的帐篷,还有缕缕青烟,都让汉宫女子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在白居易笔下,王昭君是草原上的仙子,但是,岁月无情,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容颜失去了色彩,以往的美丽,只能留在画师的画作当中了。这就使得年轻的白居易格外惆怅,因为王昭君本不该有这样的命运,如果她能在宫殿侍候君王,那么她的美丽和光彩会那么容易流失吗?失去了才知道珍贵,但王昭君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虽然草原上的人们惊叹她的美丽,也愿意臣服在她的脚下,但这一切都不是她所期望的,留在汉宫里生活才是她的理想。每当她站在草原上,看着天空上南去的大雁,她能感到内心的挣扎和苦楚。王昭君以弱女子之身,换得了大汉和匈奴边境的数十年平安,孤独和眼泪终得其所。白居易懂得王昭君心里的苦,王昭君对皇宫里那位原本属于自己的男人,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皇帝能接自己回家。只是,几十年过去了,美人红颜老去,还能再博得君王的临幸吗?对此,王昭君自己都不抱希望了。白居易对昭君出塞的心理进行了细致地描写,其实也是为了表现自己心中的担忧。自己身上的胡人血统,也将是羁绊自己命运、让自己难以腾飞的枷锁,或许,自己的悲惨命运还不如王昭君。汉女远嫁,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朝廷的妥协,这不得不说是有失体面的事,而白居易熟读史书,对这一幕如何发生,自然一清二楚。正因为如此,他才对王昭君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并由王昭君的命运,想到了自己。王昭君一个美丽的女子,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虽然姿容绝美,但一样只能远走大漠,在风沙中憔悴自己的容颜。而自己呢?虽有抱负,也在发奋努力,但胡人身份犹如被禁锢的魔咒,似乎已经决定了自己终生不能施展抱负的命运。如果自己真的因为胡人血统而难以走上治国管民的政治舞台,那满腹经纶的才情又向何处挥洒?“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人理想,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居易之所以要与王昭君作比较,是因为在他年轻的心里,也饱含着对帝王的期许,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在君王身边大展宏图,实现自己安邦定国的理想。但想到王昭君的遭遇和自己的出身,白居易不免有些担心自己也会像美人王昭君一样,是在追逐一场镜花水月的梦。到头来,只会落得一声叹息和满身伤痕。年轻诗人的惆怅,无法对人言说;只好走进梦境,向遥远年代的知己倾吐。白居易与王昭君,数百年的穿越,因为境遇相同,使得心意相通。面对着王昭君,白居易甚至认为自己还不如她,毕竟,她是汉人,虽然“愁苦辛勤憔悴尽”,却依然能有“黄金何日赎蛾眉”的期待,而自己呢?胡人的血统和大唐王朝被胡人颠覆的境遇,纵使自己有心报国,也难以遇到知音了。少年心事当拿云,惆怅虽然惆怅,但白居易却并没有因此而消磨掉信心,而是依然在为仕途做着准备。不然,他也不会在少年之时,四处漂泊了。第三节 烽火乱世,书写丧失的门第战乱破坏了大唐以往的盛景,却还是难以让白居易消沉,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是他心境的写照。虽然大唐已经日渐衰败,但白居易仍然信心满满,他觉得依靠自己的能力,完全能够让大唐重现昔日的荣光。大唐的衰败,让很多人都已经对它失望,改朝换代的号角已经吹响,地方军阀都在秣马厉兵,在腥风血雨中扩充地盘,碾压着民众对大唐的信心。但年轻的白居易却不忘初心,即将远行的他,看着古道旁的悠悠青草,它们互相依偎着,就如同枕戈待旦的战士,等待着引领他们出征的大将,为大唐复兴出力。蓝天、白云、青草、孤傲的身影,年轻的白居易遥望着远方的孤城,此时的情绪,就如同荒原上的孤城——荒凉而寂寞,那种寂寥的忧伤,使得孤独的少年更感孤独。此时,离愁别绪涌上心头,谁不想承欢父母膝下?但在这乱世里,团聚是奢望,别离却是家常便饭,每一次别离,甚至都意味着将会是永别。所以,大多数人都会举家逃避,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守着家人过日子。但是,对于白居易这个胸怀天下的年轻人来说,他的使命就是报效朝廷,复兴大唐。对他来说,离别只是出发,是光宗耀祖的起点。看着眼前的青草,回想着曾经对大唐盛世的向往,白居易心中涌起了莫名的辛酸,春风能吹绿野草,自己也不是蓬蒿人,可自己能如同这野草一样,为大唐装点出一片新绿来吗?此时的白居易,知道自己踏上辉煌的起点要比常人艰难得多。大唐,已经不是那个能包容一切民族的大唐了。当年,李白“醉入胡姬酒肆中”的豪情,已经是昨日黄花,大唐因为胡人造反,使得朝廷上下,对胡人防范甚严,白居易要走向仕途,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只有曲线救国,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了。白氏的祖籍,在山西太原,这是一个繁衍高门望族的地方,只是白居易注定与高门大族无缘。作为慕大唐之名,从遥远西域迁移而来的异族,能在此地沐浴华夏文化的高风,已经要算幸运了,更不要说安史之乱后,夷夏大防的观念沉渣泛起,像白居易这样的人家,能得以平安,就非常不错了,哪里能指望高门大族的余荫呢?但熟读儒家经典的白居易知道望族的作用,如果自己要想实现理想,不重演王昭君的悲剧,就只有想办法为自己造一个汉人高门的籍贯了。攀附有名望的古人作为自己的祖先,这难不住饱读典籍的白居易,而此时他人微言轻,又适逢战乱,不会有人把他的攀附当一回事,这也为白居易捏造自己的家族来历提供了方便。白居易的眼光,从浩瀚的历史烟云中划过,选择祖先,也是一种志向的流露,否则,随便向高门大户递上籍贯申请,再献上一篇云霞满纸的贺文,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大唐盛世时的许多文人,都这么干过。只是白居易自有雄心,当不会做如此低三下气的事,就是给自己找一位祖先,也要找一位青史留名、能安邦定国的人物,这样,才不负自己的青云之志。借着为自己的祖父写墓志铭的机会,白居易巧妙地把自己的家族同战国时期的“楚公族”联系起来了,那就是从战国楚国公族白公胜、白乙丙开始,一直延续到秦国战神武安君白起。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说是高官显爵、令人羡慕。但白居易并不是只想攀龙附凤,而是有着更为远大的理想。自古以来,开国平天下,要用武人;治国安邦,要用文人。而任何朝代,承平时期总要多于开国拓疆的拼杀,所以,文人的地位,终究要高于武将,读书人也常以文采傲世,耻与武人为伍。作为读书人,白居易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此时,大唐衰败,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正需要勇武之人扫荡污垢,除暴安良。所以,白居易在为自己寻找祖先时,特意强调“祖先”的武功,用意非常明显,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像这些“祖先”一样,扫荡扰乱大唐天下的贼寇,还大唐以安宁。到那时,白氏家族的后人就不会因为自己有胡人血统而非要为自己安插一位伟大的祖先而奔忙了。对于为白氏家族寻找祖先的事,白居易做得并不细心,这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有志男儿,凡事都要靠自己,活着的、有官职的父亲都帮不了自己,又何况已经死去千年的高门大族人士呢?因此,在诉说白氏家族与这些历史上的高门大族之间的关系时,白居易的考据工作非常马虎,人物来历交待得不清不楚,敷衍了事,以致多年以后,一些有心要为他捧场的名人为白氏家族作传时,都觉得要把白氏家族和古代的高门大族联系起来,实在是难以下笔了。但白居易却不在乎这些,让白氏家族忝列汉人名门,对他来说,不过是权宜之计:今天,我要靠你们的名望走入官场;明天,我的名声会让你们因我而骄傲。否则,野草已经烧尽,在乱世当中,高门大族不是护身符,只能是抢夺和杀戮的标靶,又何来“春风吹又生”?通过攀附高门大族的方法,白居易隐藏了自己的胡人身份,为自己的家族贴上了士族门阀的标签,这使得以后的事就简单多了,也让他离开家乡,到帝国首都长安去寻梦变得不再是异乎寻常的艰难了。是的,白居易已经找到了自己走向荣耀的门径。眼下他所能做的只有等待,只要取得了进士的资格,就有了做官的资本,实现自己的理想就指日可待了。白居易朝着长安而去。长安的荣光,远不是没有出过远门的白居易所能想象得到的。要成为长安城里的一员,而且还不是芸芸众生当中的普通人,他知道自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白居易为了能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的理想,不惜攀附高门大族作为自己的祖先,现在,就要看他是为祖先扬名还是让祖上蒙羞了。“自怜郡姓为儒少,岂料词场中第频。桂折一支先许我,杨穿三箭尽惊人。”多年以后,白居易梦想中的长安之行,不出所料地结出了硕果,不仅仅是他,还有他的两个弟弟。一门三杰,光宗耀祖。此时的白居易,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但正是这种意气风发,让年轻的白居易扬起了生命的风帆,朝着既定的目标远航。只是他没有想到,日后他安邦定国的理想并没有完全实现,反而以诗名著世,成为一代大家。白居易出生时,大唐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和杜甫已经去世了,以诗歌闻名的大唐,在文化上因此而缺少了领军人物。同时,战乱的大唐,文化凋零,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在曾经文化繁荣、诗歌璀璨的大唐诗坛,怎么能没有一个能领军的新诗人呢?在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相继离开人世后,白居易来到了人间,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才华,擎起诗坛领袖的大旗让中唐的诗坛不仅没有因为战乱而倒塌,相反独具异彩,照耀千古。可以说,白居易来到人间,是诗坛之幸,也是上天的绝妙安排,正是因为白居易的存在,才让我们看到了诗歌的另一种全新的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