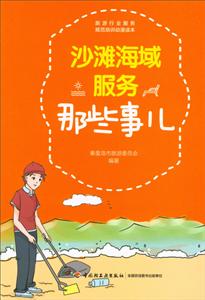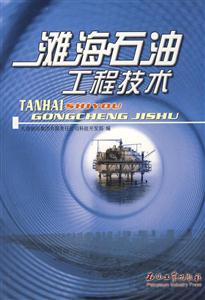作者:刘长青著
页数:146页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ISBN:9787205090722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滩海题释、滩海资源与产业、滩海精神、滩海历史与事件四部分。主要内容包括: 滩海是盘锦发展的依赖空间 ; 辽东湾的海水为什么浊等。
目录
壹滩海题释
(一)滩海是盘锦发展的可依赖空间
(二)辽东湾的海水为什么浊
(三)滩涂的转出、转入
(四)消逝的“河下等”
(五)抛出去的“小林岛”
(六)滩地上的冲突
(七)滩海历史脉延
(八)滩海上的实践主体是移民
贰滩海资源与产业
(一)濒海拥河兴渔捞
(二)卤浓滩阔晒盐晶
(三)河海连运接新港
(四)火灰水碱催珠玉
(五)石油开采起新城
(六)升河降海建蟹都
(七)翩然而来丹顶鹤
叁滩海历史与事件
(一)三次大海侵后,有红山文化先民驻足
(二)临海第一县因受海侵而罢废
(三)慕容觥伐弟践冰滩
(四)隋、唐东征渡辽泽
(五)夯土长城与西平堡之战
(六)甲午、甲辰年战争
(七)张氏父子的国恨家仇
(八)打响民众抗日第一枪
(九)二界沟历史上的渔民大罢工
(十)建市后多元发展
肆滩海精神
(一)视野无障向往崇高
(二)绝地打拼死而后生
(三)向往新地不忘血源
(四)同舟共济团结互助
(五)讲究科学追求知识
(六)浑然融合天人合一
节选
《滩海情/印象盘锦文化丛书》: (四)消逝的“河下等” 滩涂的转出、转入与日月时光并行,从来没有终止。河流带沙而来,落淤成泥滩,这泥滩越积越厚、越高。最初它们是在潮汐中时隐时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慢慢地隆起,沮洳再变为冲击土、草甸土和人居土。 在双台子河人海喇叭口摊开的扇子面上,人类早已介入了,他们一方面享受着这些注入海洋的河流为他们提供生命养源,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遭受不再驯服的老龙口的动怒,给人们带来生命与财产的威胁和祸害。 早些年的时候,一到汛期,双台子下游的河汊在三角洲任意滚动,将从上游携带来的淤泥河沙在此摊开,形成了许多的河心滩、沙坨地,或方或圆或大或小,人们管这些滩坨称为“等子”,分别赋予它们不同象形称谓,叫做“腰岗子”“后腰岗子”“屁股岗子”“王八炕”“王巴尾巴”“拉拉滩”等,这是在滩水河域的劳作者赶海下滩的比况人事、随体诘屈。当他们累得精疲力竭的时候,为了刺激自己的兴奋点,无所顾忌地创造出来的。不幸的是,以其极强的形象化和浓郁的俚俗趣味,被固定下来,让后人难以更换一个新名字。 大洼新兴镇的河下等村,曾是从老盘山城中穿境而过的双台子河滩地“转出”的标志性符号,因此这个村子取名为“河下等”。最初,河边的地主看到隔几年发水就能淤积出来一片片上好的河滩地,他们趁着大水下来前,就像跑马圈地似的在那河道摆动的下游插上一圈圈的桩橛,每一圈大约有15亩的面积,这叫“插套子”。当洪水过后,落淤在插桩橛的套子内的隆起泥沙,闪着光泽的新地就归他们所有了,他们就雇了些人来耕种,这些丝毫没有费力等来的良田沃土就成为他们放租收利的资本。而此时,傍依滩海的河下游等来了大批闯关东的移民,他们大多出卖的是劳动力,而地主收的是地租。 但有时滩地“转出”后会再行“转入”,即滩涂变化的复杂性——生成了消逝,消逝又复生成。这是盘锦中潮型河口的海河交互作用力突变所致。在丰水期,下泄之洪水能造成滩海地形面目全非。1997年,我曾来到“河下等”村落遗址来采访。此前,这个村落遭到废弃。因在1995年8月遭受一场特大洪水袭击,将围堤外的庄稼、菜园全部荡平,又在村北围堤上撕开了个大口子,这个村子的土地、房屋有一大半儿被打入双台子河心去了,即滩地原来的“转出”又复变为了“转入”。村子的老人们谁也不愿离开这个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故园,他们埋怨是河北岸修的导流堤将水导到了这儿,说如果再花点钱把阻水的河心塘豁开,也不至于憋出那么大的水流来……这时,说啥也没有用了。洪水还是从决口处汩汩地往村子里灌,水位仍持续升高,人都搬到了坝顶上去住,猪羔子跑到房顶上哼叫,鸡在漂浮的草堆上下了蛋……县政府、镇政府不得不强令170户村民整体搬迁,并予以在全县整体调剂。分别将其妥善地安排在了新兴镇其他村和赵圈河乡及辽河三角洲等地新落户。 当时,我采访了借住在腰岗子67岁的河下等村民张志文老人,他说他很早就搬到了“河下等”,那时,这儿正大量地出现新生的滩地,河边许多地主都在河边插桩橛圈地,这样插来的地多有上千亩,都是上好的高粱地。1947年发大水,有家地主一次就插了两个套子,大水过后,他等来了30亩地。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个人插出的滩地都分给了农民,经过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等来的滩地都归为国家所有。改革开放后,又分到了老百姓手里,但个人只有使用权。 据张老说,他刚搬到这里时,仅有十户不到的人家,那滩地叫个肥,来的时候,只要把滩上的草一割,种啥长啥。头一年我种了十亩高粱,上秋打了四五千斤。河里的鲇鱼、黑鱼、鲤子、鲢子、导子有的是,河螃蟹遍地爬,出去一趟,就能弄回个百八十斤的。出了上口子,就看见海了,还能打到海鱼,像鲈子、梭鱼和愣巴。 “就是村子名字叫坏了,早先是叫‘河淤等’(滩地的转出),后来人们胡乱叫,叫成了‘河下等’(滩地的再行转入),结果真的等到河下去了。现在,这一切都没了。”(张老的原话) 站在残缺不全的河下等遗址堤坝豁口处,那儿遗留着深深浅浅的人的脚窝和车辙印迹,令人可想当年这儿发生过人与洪水激烈的搏战。钢筋混凝土被生生割开,砖瓦已变成了碎块残粒,它们见证了谁才是胜利者啊!我将丰富想象力扩展到极限,怎么也想象不到水能释放出这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将一个百余年积淀的村庄历史轰然切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