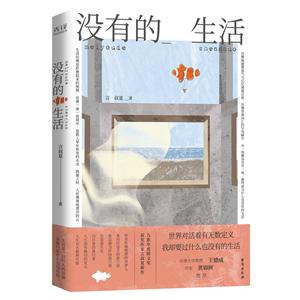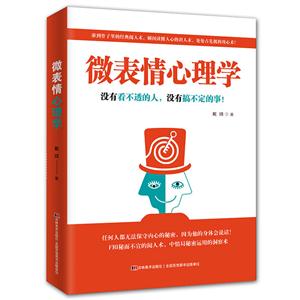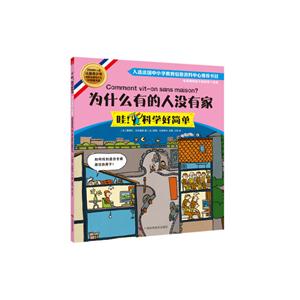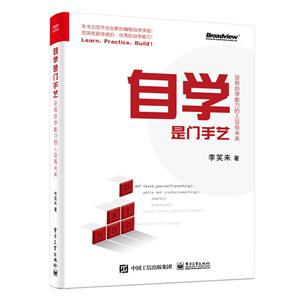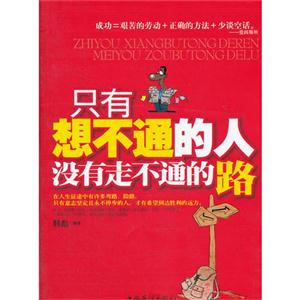作者:(英)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M
页数:432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7
ISBN:9787542655875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克里斯托弗是个信仰骑士时代的传统道德的贵族绅士,正直隐忍,洁身自好。而西尔维亚是个典型的交际花,有着众多情人的她过着终日纸醉金迷的生活。然而意外的怀孕让她不得不为了挽救名声,嫁给了保守的克里斯托弗。婚后枯燥无味的生活和丈夫的冷漠隐忍都让西尔维亚抓狂,她开始用尽一切手段来刺激克里斯托弗。西尔维亚与旧情人私奔成了二人矛盾的开始,然而两人的宗教信仰都不允许其离婚。就这样,这段勉强维持的婚姻让两个人陷入了无尽的折磨中。意外的机会克里斯托弗认识了思想激进,学识深厚的现代女性瓦伦仃,进一步的接触让这两个看似不同世界的人相爱了,可世俗的羁绊却阻挠着两人对这段感情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西尔维亚也意识到了婚姻的危机,开始收敛自己的生活努力的挽救婚姻,向丈夫示好。一战的到来,克里斯托弗参军让这段三角关系爱情面临考验和抉择。
作者简介
福特•马克多斯•福特(1873—1939),英国著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诗人。他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曾与康拉德、亨利•詹姆斯等人齐名。其主编杂志《英国评论》各大文豪都曾为之撰稿,如哈代、托尔斯泰、H.G.威尔斯、康拉德等。福特所著《好兵》一书名列“20世纪百部最 佳小说”第30位,受到格雷厄姆•格林、康拉德等名家的一致称赞。
本书特色
英国现代主义奠基人经典作品
奥登 格雷厄姆•格林 朱利安•巴恩斯 安东尼•吉伯斯 汤姆•斯托帕德激赏佳作
入选“二十世纪百大最 佳英文小说”
第1次世界大战百年纪念 中文版首次出版面世
HBO、BBC、VRT联合制作同名迷你剧集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担纲主演
目录
前言
在英国文学史上,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比他早一代的作家们将其视作惹人厌的新潮人物,而自视为新时代真正书写者的现代派作家又把他划入了令人厌烦的老朽当中。在现代派作家海明威的巴黎回忆里,和福特一起在咖啡馆喝酒纯粹是受折磨。这位年长的作家先点了一杯味美思酒,随口又改成白兰地加水,等到酒上来之后,他却又非说自己点的是味美思酒。不光如此,他的言谈也无聊得很,他邀请海明威去参加自己的聚会,不论海明威重复多少遍自己曾经在聚会的地方住过两年,福特只顾着唠唠叨叨要怎么才能找到地方。他还不忘给海明威指明,曹经是英国军官的自己,自然是一位绅士,而海明威虽然是位好小伙子,但永远成不了绅士。海明威只好回忆诗人庞德是怎么给他描述福特的,提醒自己福特“只有在很累的时候他才撒谎,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他经历过很多很糟的家庭问题”。就算这样,海明威发现自己也没有办法把庞德的评价和面前这个嘟嘟囔囔的大个子中年人联系起来。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里记下的这一笔恐怕是很多人对福特的唯一印象,不过,海明威在回忆录里并没有提到,当时还名声不显的他有三则短篇小说发表在文学杂志《大西洋彼岸评论》上,这份杂志的主编正是福特。海明威担任过一期《大西洋彼岸评论》的特邀编辑,还曾想取代福特成为主编。在回忆录里贬低福特难免让人觉得海明威是在发泄心中积怨,多少有点“弑父”的嫌疑。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也绝非海明威回忆中糊涂无聊的傲慢老作家,如果没有福特,海明威和他的现代派朋友们登场的时间只怕要大大推迟。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原名福特。赫尔曼·休弗,一八七三年出生在英国萨里郡的默顿市(现为大伦敦市的一部分)。福特出身于艺术世家,按照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说法,福特的“出身和幼年经历逼他只能去过艺术家的生活”。他的外祖父福特·马多克斯·布朗是英国拉斐尔前派著名画家之一,他的父亲弗朗西斯·休弗是《泰晤士报》著名的音乐评论家,而他的教父则是英国十九世纪晚期著名诗人阿尔杰衣·斯温波恩。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福特的确被熏陶出了超乎常人的文学才能,十八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棕色的猫头鹰》,一生共出版了七十多本小说、诗歌和评论文集。在他的朋友、美国作家和评论家亚伦·泰特的笔下,福特几乎就是一位文学天才。他通晓古今欧洲文学,从希腊罗马文学到当代的欧洲各国文学无不涉猎。除了母语英语,福特还自如地在法文和德文之间游走,意大利文阅读也不成问题。泰特回忆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一家法国的出版社想出版福特的小说《好兵》,请福特介绍一位翻译,结果两个月之后,福特把自己的小说用法文重写一遍交给了出版社,无怪乎泰特惊呼福特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欧洲文人”。 一九○八年,福特创立了《英国评论》。他自己开玩笑说,创立这份杂志是为了发表哈代那些没人愿意发表的诗歌。不过福特的野心其实不小,他在发刊词中写道,这本刊物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想象文学一次在英国发展的机会”。很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文坛甚至欧洲文坛第一人物都纷纷聚拢到福特和他的评论周围。《英国评论》第一期的作者名单足可以让所有文学刊物主编嫉妒得发狂: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约翰·高尔斯华绥、托尔斯泰和H.G.威尔斯等等。作为主编的福特不仅仅能够吸引这些文坛大豪,他还不遗余力地发掘、提携新作家。后来为人熟知的美国诗人庞德、英国作家D.H.劳伦斯都是在福特编辑《英国评论》的时候被荐入文坛的(用庞德的话说,劳伦斯是福特“从伦敦郊区的寄宿学校里挖出来的”)。在福特故去之后,他对年轻作家的热情在他人的回忆中也常常被提及。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略微夸张地说:“和福特说一次话,就能让年轻作家飘到羽绒一样的云朵之上,出版商和编辑们会争抢他的作品,当他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会有一打出版商和编辑在他家门口扎营等候。”
……
福特在写作这本小说时运用了纯熟的现代主义手法。整部小说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展开,他带领我们从一个角色的头脑中跳到另一个角色的头脑中,而小说的语言也从来不会直接把关键事件呈现给读者,它总是在伸展枝蔓和游移,碰一下,然后又赶紧缩回去,绕开,最后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不经意地提起,绝不用任何确定的语言简单地为事情定性。换句话说,福特用虚构语言重构了生活的朦胧和不确定。故事中没有任何俯视众生的视角,读者必须和角色一起前进,一起选择,一起承认错误。关于福特的语言特色,英国作家V.S.普里彻特有很经典的评价:“混淆是他作为小说家的主要艺术特征,但他迷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展示一切。”
对读者来说,现在重读福特的这部小说,还有超越狭义的文学的意义。虽然历史学的考据、经济学的统计,甚至政治学的阐释都给我们提供了解释百年前战争的种种可能的答案,但是这些理论似乎都没有办法再让我们回到一个世纪前做出决定的那些人的头脑中,无法再直击他们心中的权衡和割含,也没有办法让我们感同身受地体验生活在战火中普通人的压抑和无力。文学作品似乎是唯一让我们有可能近距离触碰一个世纪前那些被战争摧毁的灵魂,和他们一起品尝战争恶魔被释放出来之后人间的辛酸苦楚的途径。从这个角度说,文学作品可以算得上是“主观”的历史,字里行间封存的正是过去世代的心灵历程。昔人已逝,但是保留在文字中的挣扎和痛苦会让后来的我们,面对类似的情景时,多几分谨慎,少几分动辄喊打喊杀的戾气。
肖一之 二○一四年秋
于布朗大学
节选
这两位属于英国公务员阶层的男子坐在精心布置的火车车厢里。拉车窗的皮带簇新,新行李架下的镜子一尘不染,干净得就像什么东西都还没照过。鼓起的坐垫上,华美而规则的曲线精致地勾勒出一条龙的形状,这绯红和黄色交织的设计出自一位科隆的几何学家之手。车厢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洁净而令人赞叹的清漆味。火车行驶得像英国金边债券一样平稳,提金斯记得当时是这么想的。火车开得很快。但提金斯确信,如果火车摇晃了或在铁轨接头处颠了一下,麦克马斯特一定会给铁路公司写信抱怨的。他甚至可能会写信给《泰晤士报》。除非是汤布里奇桥之前的弯道,或者阿什福德的几个岔道上,在这些地方行驶异常是预料之中并且可以容忍的。
他们这个阶层治理着全世界,而不仅仅是最近刚成立的由雷金纳德• 英格比爵士掌管的帝国统计局。如果他们看到警察滥用职权、火车行李员举止粗鲁、街灯不足、公共服务或外交方面的疏漏,就一定会管一管,要么是用他们淡定的贝利奥尔口音,要么就是一封给《泰晤士报》的信,遗憾而又愤怒地质问,“英国的这个那个怎么变成了这种样子!”或者,他们在严肃的评论刊物里撰文,讨论教养、艺术、外交、帝国商贸,或者已故政治家和文人的声望。有很多这样的刊物流传了下来。
麦克马斯特,或许,会这么做。至于他自己,提金斯倒不是很确定。麦克马斯特坐在那里,个头不高,辉格派,黑色的胡子修剪得尖尖的,个子小的人常常留这种胡子来彰显他们已经萌芽的声望。倔强的黑发得用硬金属梳子才能驯服。鼻子很挺,牙齿结实而整齐,衬衣的白色蝴蝶领光滑得如同瓷器。金质领带环扣住带黑色条纹的钢蓝色领带—— 提金斯知道,这是为了衬托他的眼睛。
提金斯,坐在一边,已经不记得自己打了什么颜色的领带了。他雇了辆车从办公室回到住处,套上宽大的西装外套、西裤和一件质地较软的衬衫,飞快却有条不紊地把一大堆东西装进有两个提手的大旅行包里—— 如果有必要可以扔进守车里的那种。他不喜欢贴身男仆碰他的东西,连妻子的女仆帮忙打包整理他也反感。他甚至不愿意让行李员提他的旅行包。他是个托利派,而且因为他也不喜欢更换衣物,还在路上他就已经穿好敲了边、钉了掌的、宽大的棕色高尔夫球靴,坐在那里,坐在靠垫边沿稍向前倾,两腿叉开,一边膝盖摊着一只巨大的白手,茫然地思考着。
麦克马斯特,坐对面,向后靠着,读着一些小张的、并未装订的印刷纸页,体态略显僵硬,稍稍皱着眉头。提金斯知道,对麦克马斯特来说,这是个难忘的时刻—— 他正在修改他第一本书的校样。
出书这件事,提金斯知道,有不少微妙之处。如果,比如说,你问麦克马斯特他是不是个作家,他会抱歉地轻轻耸一耸肩。
“不,亲爱的女士!”因为自然不会有男人问任何一个明显饱经世故的人这种问题,他会微笑着继续说,“没那么好!只是不合时宜的小打小闹。评论家,可能算是。对,一个小小的评论家。”
尽管如此,麦克马斯特仍在客厅走来走去。那房间里挂着长窗帘,摆放着青花瓷盘子,贴有大花纹的墙纸,挂着安静的大镜子,塞满了长发飘飘的文艺界人士。并且,只有在尽可能靠近举办沙龙聚会的亲爱的太太们时,麦克马斯特才会将谈话进行下去—— 多少有点权威姿态。当他说起波提切利、罗塞蒂,还有其他被他称作“早期人士”的早期意大利艺术家的时候,他喜欢别人恭恭敬敬地听着。提金斯在那里见过他。提金斯并没有反对过。
因为,如果这些聚会不直接代表他已经进入上流社会的话,它们至少可以被当作一块通往一流政府工作的那条需要谨慎的漫漫长路上的垫脚石。而且,与自己对事业或职位彻底漫不经心的态度相应,提金斯还对朋友的野心带有讽刺意味地表示同情。这段友情有些古怪,但友情中的古怪成分常常保证了其持久性。
作为一位约克郡绅士最小的儿子,提金斯所享有的都是最好的—— 一流政府公务员工作和上流社会人士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生活。他没有野心,但他所拥有的东西都不请自来,这在英国是理所当然的。他有本钱为自己漫不经心的穿着打扮、身边的客人和表达的观点负责。他有一小笔他母亲账下的私人收入,一小笔来自帝国统计局的收入。他娶了一位家底殷实的太太,而他自己说话的时候,以一种托利派的方式,充分掌握了讥讽和嘲弄的本领。他二十六岁,但是块头很大,像约克郡人那样浅肤色,不修边幅,比他这个年纪应有的体态还要胖一点。每当提金斯选择发表一番关于影响数据统计的公众倾向的言论时,他的上司雷金纳德• 英格比爵士都会认真地听。有时候雷金纳德爵士会说:“你是一本写满准确事实知识的、完美的百科全书,提金斯。”提金斯认为这是他应得的,因此会不作声响地接受这一赞扬。
听到雷金纳德爵士这样的话,如果是麦克马斯特,则会咕哝道:“你真好,雷金纳德爵士!”提金斯认为这样的回答非常合适。
麦克马斯特在部门里的资历稍老一些,因为他很有可能年龄也要大一点。因为无论是他室友的年龄,还是他确切的出身,提金斯都不十分清楚。麦克马斯特明显有苏格兰血统,一般人当他是所谓“牧师住宅里长大的孩子”。毫无疑问,他其实是库珀的杂货店老板或者爱丁堡的火车行李员的儿子。这对苏格兰人来说没什么问题,而且,因为麦克马斯特得体地对他的出身表示缄默,已经接受了他的人不会—— 甚至都不会在心里—— 提出任何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