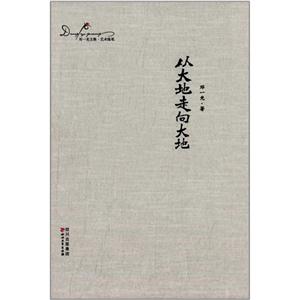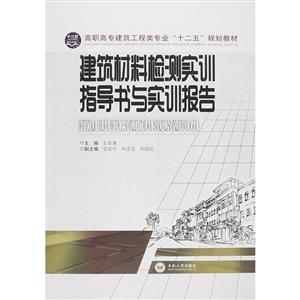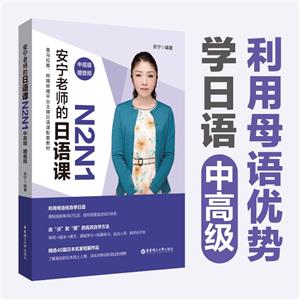作者:左中美
页数:224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ISBN:9787506392648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第三辑):安宁大地》以作者在一座世居的彝族村庄出生、成长的生活经历为背景,将村庄的自然万物以及乡土文化与个体的生命认知相融合,讲述村庄大地上万物的生长与繁衍,人们在这大地上的劳作与生活,对天地自然的遵从与敬畏,对古老美德的认知与修行。
作者简介
左中美,女,彝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个人散文集《不见秋天》《时光素笺》《拐角,遇见》,历史文化集《中国名城?云南漾濞》。曾获第七届云南省政府文艺创作基金奖、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届很好文学艺术奖等。
本书特色
生长,拔节,开花,收获。奔跑,歌唱,生息,传承。在广阔的大地上,村庄以及其间的万物,向人们传递着大地深处生生不息的力量。在那无声的生长、鲜活的生命以及不尽的歌谣里,人们看见大地久远的、安宁的意绪,并且相信,这是我们终究无法离去的、葳蕤的家园。
目录
节选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第三辑):安宁大地》: 果木 “果木”,村庄的人们把它作为一个词语,用来通指那些人工栽植的果树,有时候也用以统称这些果树结出的果子。 向阳少水的山坡,对于果树的生长一利一弊,利在阳光充足,弊在干热少水。在这样的条件下,村庄的果树一直品种单一。在不多的果树品种当中,桃树长久居于主体,大体上每家都有,少则一两棵,多则七八棵,多数就栽植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若是一户人家连一棵桃树都没有,这样的人家在村人眼里便有些不堪,不是懒汉就是寡薄——等桃子熟了,乡邻们相互吃两个,那不也是一份小小的布施么? 我是后来才发现到,这桃树就像孩子(当然,其他的果树也不例外),父母好好地生下来,之后,他们却有了分别,有的长得俊,有的长得丑,有的聪明,有的愚钝,有的丑却有手艺,有的俊却无脑子,有的甚至长出来是个哑巴。我们家有三棵桃树,都在村边干塘子的塘口上。这干塘,听说在大集体时候,里面蓄满了水,水里养着集体的鱼。只是,从我记事的时候,这塘里已经没有水了,塘底变成旱地分到了户,我家和村中另一户人家一家一半,靠西的一半属于我家,靠东的一半属于他家,年年大春,两家都在里面种包谷,包谷间间种着一行一行的四季豆。我家的三棵桃树,两棵在塘口西南,一棵在塘子西北角上。三棵桃树应该是包产到户时与一半塘底一起分到我们家的。 三棵桃树各有差别。塘口西南的两棵,靠西那棵更老更旺一些,也比较好攀爬,靠东那棵更年轻,枝条更直一些,所以比较难上。这两棵桃树的果子品相也有差别,靠西的一棵果子更大,成熟时更红,但果形更平庸一些,吃的时候能裂开果核;靠东的一棵果子更小,果形更清瘦文静,等熟透了,“脸”上也只着淡淡的红晕,吃的时候果核不能裂开。 塘口西北角上的那棵桃树要年轻得多,一根主枝,有大人的手臂那么粗,一条侧枝,有手腕那么粗,一年一年,花开得特别繁,叶长得特别密,可这桃树却是一棵鳏桃,只开花不结果,偶尔地结出三五个来,也是绿绿的、毛毛的,不到成熟便落了。村庄里流传的古训,说是果木不结果子要拿刀来砍,吓唬吓唬它,以后它就结了。有一年母亲就带着我去砍这棵桃树,那是一年中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应该是某个节气吧,我而今已不记得了。母亲拿着一把砍刀,在桃树的主枝上轻轻砍了一刀,问:“你以后结不结?”我要代桃树回答:“结,一定结得又多又好!”事前母亲还交代我,让我不能笑,要严肃。只是,那桃树在那年母亲拿刀砍过之后,还是没有结出果子。 在塘口西南那两棵桃树的下面,隔着一幅窄长的地,地埂下的陡坡上有一棵桃树,地和桃树都是我三姑家的。这桃树的下面便是深箐,且桃树的枝条因为面前陡坡的影响,四五枝差不多同样粗细的枝干全都往箐口上面伸。因为孩子们对下面深箐的畏惧,这桃树上的桃子每年都有许多熟烂在枝头,最后落到了深箐里。 村庄的梨树要少得多,只有三五户人家有不多的梨树。所谓物以稀为贵,孩子们便稀罕梨。村庄后面高远的山上有一个相邻的村庄梨特别多,名叫上吐路么。年少时,每年到了农历六月二十五火把节和七月半节,因为按节俗要给祖先供果子,节日这天一大早,上吐路么的杨有才就会背着一大篮子梨到村庄里来卖,里面多数是个大面黄的黄皮梨。杨有才没有秤,梨论个卖。梨虽有价,买梨的妇女们却大多不依他,连说带赖地,要么在每个梨上砍价,要么是付了十个梨的钱,却硬要拿十二三个,杨有才最后都只有作罢。有时候,买梨的人故意狠狠地砍价,杨有才就拉开他的旧且脏的衣服领子让人看他的肩,看他背着这一篮子梨从上吐路么走到这里来,篮子的背带在他的肩上勒出了多深的红印子。 其实,人们不用看杨有才肩上的红印子,只要看看他头上脸上的汗,看他那半截湿透的破裤脚,就能知道他这一程的艰辛。杨有才每次背了梨来,总是歇在村中井头的大青树下卖。他头上脸上的汗水里带着黑色,汗水已经干了的地方则留着暗黑的印迹。他的头发粘结着,身上的衣服多数时候看不出本色。他脚上的布鞋或者解放胶鞋通着大大小小的洞。上吐路么十多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梨,而杨有才是唯一一个背梨卖的人。买梨的妇女们说笑归说笑,到终了却也不会让杨有才亏了汗水钱。后来,杨有才老去以后,再没有人背梨来我们村庄卖了。 在果木当中,芭蕉算一个例外。所谓果木,原本是指那些木本的果树,芭蕉属于草本,但是它在概念上,也被归为果木。 芭蕉种在沟头箐脑潮湿有水的地方,一棵芭蕉种下去,若是水土好,几年便能繁衍成一小片。一棵芭蕉,一生只结一次果子。所谓芭蕉结果心连心,一串芭蕉,少则结十来个,多则三四十甚至更多。一串青芭蕉,看着它长足个、大多数芭蕉的头上开始出现裂纹,便可以砍回来捂上了。我奶奶捂得一手好芭蕉。一串饱熟的芭蕉,清早去把它砍回来,将它在太阳下晒一天(为此,砍芭蕉也要看天气,天气晴好才能砍),至傍晚,将晒得热烘烘的芭蕉串先用两三层麻袋包裹紧实,之后,把裹好的芭蕉埋进装在大囤里的豆糠或米糠深处,把糠压实。最后,再在囤口上盖上大簸箕,上面用木墩或是石块压住,不让它漏气。捂芭蕉的时日长短要看芭蕉成熟的程度,芭蕉若是在树上长得更熟一些,就捂五天,若是更青一些,就捂七天。捂的过程中,绝不允许孩子们去翻动,使芭蕉透了气。一旦芭蕉在未捂熟时透了气,里面就会有硬心,之后,不管再捂多久,直至把芭蕉捂烂,都无法把这硬心捂回来。 家里捂一串芭蕉是一件隆重的事,往往要赶某个节日,或是家里某位重要的亲戚要来。一串芭蕉稍早一点砍或是稍晚一点砍,往往都是为了赶这个时间。晚一点砍自然没问题,若是早砍,捂这芭蕉就有风险,甚至不小心还会把芭蕉捂坏。好在我奶奶经过一生的实践,对捂芭蕉的技术早已熟练于心,除非是我们这群孩子当中有人憋不住提前偷偷去翻看漏了气,否则极少会出现失误。 芭蕉砍下之后,结过芭蕉的那棵芭蕉树便只剩下一件事:等着主人哪天提着刀子和绳子来,将它砍倒,分成截背回家,剁细后在大锅里煮熟,拌上糠和面,变成一锅猪食。听一个曾经的少年讲起背芭蕉筒子的经历:芭蕉筒子又圆又滑,再加上两头又不一般粗细,绳子总是绑不住,背在身上不住地往两头滑。后来想得一个法子:找两根棍子,将头上削尖,在两边横向穿住两截芭蕉筒子,两股绳子被挡在两边的棍子以内,这样背起来,绳子和芭蕉筒子都不会再打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