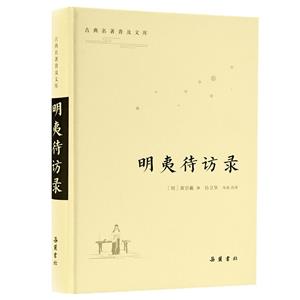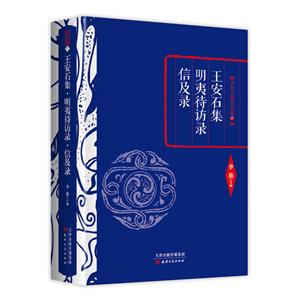作者:董成龙 著
页数:352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
ISBN:9787568948869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明夷待访录》义疏是对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一书的深入解读和注解。本书以原著为基础,对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其核心理念和观点。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理念,主张实行“法治”而非“人治”,提倡“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强调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在义疏过程中,不仅对原著中的字词、句式、典故等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还对黄宗羲的思想背景、历史环境和文化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大量与《明夷待访录》相关的文献资料,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信息。
作者简介
董成龙,北京大学法学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哲学系副教授、经略研究院研究员、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政治思想史》期刊编委。
曾获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北京外国语大学“师德榜样”,专著《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入选儒家网2019年度学术思想类“十大好书”。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省部级课题两项,编译《大学与博雅教育》《德性与权力》两书。研究领域不局限于特定国别或人物,而围绕秩序与重建的基本政治哲学问题展开,代表作《形式化、形式主义与中国历史的政治哲学论纲》《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史记·陈涉世家〉中的“首事”与“矫诈”》《留美时期林同济的中国东北史研究》《内战时刻与举国节庆——林肯与作为政治宗教的感恩节》《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与欧洲文明的战后重建》等。
本书特色
《明夷待访录》的现代注译本不在少数,而文言文被译成白话文,并不能自然帮助读者把握该书用力最深的“政意”与“政制”的探讨。《明夷待访录义疏》的出版就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义解与疏证并非无的放矢地引用,而是依照宗羲本人的提示,择取其中关键人物及其思想论说,以期沙盘推演宗羲的谋篇布局与写作构思。若于义解和疏证外别有心意,则恰如宗羲本人于未来科举制畅想所言,以愚按形式随文附于疏证之后,不至于因个人臆解而破坏正文义疏。
《明夷待访录义疏》以黄宗羲背靠之传统典籍为之作注,以期更好地跟随其脚步,虽然表面上以经典注后人,实则反倒为我辈以宗羲为阶梯踏足经典与故事提供入路。宗羲已逝三百余年,今天重访其文本,化用读经、解经之法,抽绎全书,或可得其提示,重审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目录
凡 例 / 001
自序:《明夷待访录》的通变与法意 / 003
题 辞 / 025
一、原君 / 035
二、原臣 / 057
三、原法 / 071
四、置相 / 083
五、学校 / 099
六、取士(上) / 129
七、取士(下) / 141
八、建都 / 165
九、方镇 / 177
十、田制(一) / 186
十一、田制(二) / 199
十二、田制(三) / 209
十三、兵制(一) / 231
十四、兵制(二) / 245
十五、兵制(三) / 257
十六、财计(一) / 265
十七、财计(二) / 282
十八、财计(三) / 293
十九、胥吏 / 299
二○、奄宦(上) / 315
二一、奄宦(下) / 327
参考文献 / 334
节选
一、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人之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义解
全书凡二十一篇,所论涉及中国政治诸种专门制度,前三篇所论《原君》《原臣》和《原法》,实为政治宪法与君臣大义,意在探究中国政治基础规范。[1]
梨洲起调甚高,全书《题辞》以孟子开篇,正文篇首则以“有生之初”开始,谈人世之初,足见其志不在小,从一般人性处着手,纵贯截至明清之际的中国通史。[2]人生之初的自然原点未必尽是仁人君子的超凡心性,人人都自然地心系一己利益。如此一来,没有人关心天下人的“公”业:天下人的“公利”无法兴起,天下人的“公害”无法破除。[3]
但梨洲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他进而由人人自私的自然原点转向君子为公的人定原点(尧舜)。原来,“天下为公”只是少数君子的作为。梨洲与先秦原儒已颇有距离,然而他的主张却更适合在新时期的作为。必有仁人能挺身而出,使天下得以受享其利,尽收其害,可是这番勤劳必定与前文所述天下好逸恶劳之人情相悖。既是如此,统治者如何产生? [4]
梨洲基于上述人性论,引出三种可能的人生选择:第一种人身怀体量却不愿担当,究其缘故,正在于君主夙夜在公,忧心忡忡,故有意躲避君位,以图清净无扰。此种达能而隐逸者以许由、务光为最,尧让位许由,许由洗耳不受;汤放桀,让位务光,务光亦不受。[5]第二种人曾一度出任君主而终究自行退隐。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均是此种功成身退、不眷恋红尘者。[6]第三种人一开始不愿意入仕,最后无法退出,最重要的例子便是禹。[7]“好逸恶劳”是人所共有的性情,因此,出山执掌天下是一件十分辛劳的事情,人们都避而不做。[8]
疏证
一、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人之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义解
全书凡二十一篇,所论涉及中国政治诸种专门制度,前三篇所论《原君》《原臣》和《原法》,实为政治宪法与君臣大义,意在探究中国政治基础规范。[1]
梨洲起调甚高,全书《题辞》以孟子开篇,正文篇首则以“有生之初”开始,谈人世之初,足见其志不在小,从一般人性处着手,纵贯截至明清之际的中国通史。[2]人生之初的自然原点未必尽是仁人君子的超凡心性,人人都自然地心系一己利益。如此一来,没有人关心天下人的“公”业:天下人的“公利”无法兴起,天下人的“公害”无法破除。[3]
但梨洲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他进而由人人自私的自然原点转向君子为公的人定原点(尧舜)。原来,“天下为公”只是少数君子的作为。梨洲与先秦原儒已颇有距离,然而他的主张却更适合在新时期的作为。必有仁人能挺身而出,使天下得以受享其利,尽收其害,可是这番勤劳必定与前文所述天下好逸恶劳之人情相悖。既是如此,统治者如何产生? [4]
梨洲基于上述人性论,引出三种可能的人生选择:第一种人身怀体量却不愿担当,究其缘故,正在于君主夙夜在公,忧心忡忡,故有意躲避君位,以图清净无扰。此种达能而隐逸者以许由、务光为最,尧让位许由,许由洗耳不受;汤放桀,让位务光,务光亦不受。[5]第二种人曾一度出任君主而终究自行退隐。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均是此种功成身退、不眷恋红尘者。[6]第三种人一开始不愿意入仕,最后无法退出,最重要的例子便是禹。[7]“好逸恶劳”是人所共有的性情,因此,出山执掌天下是一件十分辛劳的事情,人们都避而不做。[8]
疏证
[1]司马迁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梨洲论近人多“不知本末,迷其向背”(黄宗羲:《汰存录》)。梨洲所录元末明初大儒宋濂一文,与其推本求源工夫有异曲同工之妙:“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斯文也,果谁之文也?圣贤之文也,非圣贤之文也?圣贤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犹水与木然,导川者不忧流之不延,而恐其原之不深;植木者不忧枝之不蕃,而虑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也。”(宋濂:《文说》,载黄宗羲:《明文海·卷一三一》)
◎愚按:若以西人《圣经·旧约》开篇“太初”(arche)参照而观,亦知推本求源所念兹在兹者,既是作为起点的原点,又非静止于此,更是规范由此出发以后道路的原则。
[2]唐人柳宗元(773—819年)曾就人世之初发问:“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柳宗元:《封建论》)南宋陈亮(1143—1194年)尝言:“昔者生民之初,类聚群分,各相君长。其尤能者,则相率而听命焉,曰皇曰帝。盖其才能德义足以为一代之君师,听命者不之焉则不厌也。”(陈亮:《陈亮集·问答上》)
◎愚按:追问人世之初的思路,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夫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实际是看中了“作为未来的过去”,在缥缈的远古中看到深远的未来,聚焦的起点并非人的自然原点,而是将三代作为政治起点、文明起点。
[3]狄百瑞将“公利”译作“common benefit”。
◎愚按:须知,梨洲同时代的十七世纪西方哲人所谓“公共福祉/国家”(common wealth/commonwealth),其要害在于“common”与“wealth”合成一词为“国家”,拆成词组即是作为国家的目的“公共福祉”,此中要义或可对勘,相互发明。
[4]李贽(1527—1602年)曰:“夫私者人之 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李贽:《藏书·德业儒臣后论》)陈确(1604—1677年)系梨洲同门,亦曰:“彼古之所谓仁圣贤人者,皆从自私之一念,而能推而致之以造乎其极者也,而可曰君子必无私乎哉?”(陈确:《陈确集·私说》)
王夫之曰:“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王夫之:《读通鉴论·隋文帝一一》)贺麟(1902—1992年)托名梁启超称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语,指出:“以杨子 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点?”(杨海文:《贺麟与“梁任公称费希特语”问题》)
◎愚按:李贽人心自私论颇为激进,梨洲却为公心留下空间,此其根本差异(另须指出,《明儒学案》中并无李贽位置)。再者,梨洲虽然讲明“人各自私”,却非全然无“公”,故曾致信陈确,论及与其不同见解:“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黄宗羲:《与陈乾初论学书》)
[5]《庄子·杂篇·让王》全录“让王”事例,记曰,“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
韩非子论许由、务光等十二人曰:“此十二人者,皆上见利不喜,下临难不恐,或与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则不乐食谷之利?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此之谓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饥饿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有民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之?”(《韩非子·说疑》)梨洲曰:“许由、务光相传遁世之学,孔子之所谓逸民者?”(黄宗羲:《破邪论·从祀》)
◎愚按:许由、务光之类既不为君,也不作臣,实为脱离政治秩序的非政治人,韩非为政治人,故多有抵牾?若揆诸西学资源,可见古罗马贺拉斯(Horace,前65—前8年)诗曰“远离俗务者幸福”(Beatus ille qui procul negotis)?柏拉图戏剧《理想国》中亦有强制有德者出任公职一说,正合此义?
[6]荀子曰:“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刘向:《说苑·君道》)“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霉黑,禹胼胝?”(《淮南子·修务训》)
◎愚按:已品尝到权力滋味而能主动让位者,此例于世界史中难觅?尧、舜皆有乾卦上九“亢龙有悔”之象?揆诸现代政治,美利坚合众国国父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年)连任两届总统后主动退出,实际为美国总统设立不成文之限任制(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后,美国以第22条宪法修正案确认任何人不得担任总统超过两届),庶几近之?
[7]◎愚按:尧、舜、禹齐名,然而又有很大不同,因此梨洲将其分置于两个传统之中?禹不再禅让,而是将王位传子,由此开启政权血缘继承的崭新模式,影响直至明清?
[8]王夫之曰:“夫天下有其大同,而抑有其各异,非可以臆说竟也久矣?其大同者,好生而恶死也,好利而恶害也,好逸而恶劳也?”(王夫之:《宋论·宋真宗三》)陈亮曰:“三代以仁义取天下,本于救斯民,而非以位为乐也?”(陈亮:《陈亮集·问答上》)
◎愚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远超于百姓?既然古人好逸恶劳之情没有差别,重点便不在于这一人情的共通,而在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权变,或曰对人情的矫正?古人之君舍身为人,实乃圣人权变?换言之,三代以上之人君,正是因其大德才不得已就位,日后有德无位和无德有位的处境不可与之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