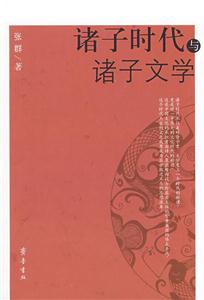作者:蒋原伦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
ISBN:9787559878410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以诸子互评生动呈现百家争鸣盛况之作。视角独特,从儒、道、墨、法、名等学派间的辩论中,深挖其产生背景与发展脉络,达成对各学派思想的更深刻理解。作者以对文本的敏锐洞察力,立足于墨子批儒、庄子鉴孔,韩非解老等论辩与攻讦,指出鲜为人知的有趣现象并给出独到见解,如孔子地位及形象在道家文本中演变背后的儒道争锋、韩非对老子思想的全面阐发和刻薄寡恩化运用。书中呈现出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展现先秦思想多元一体的独特风貌。
作者简介
蒋原伦,1950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聘任教授。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传统的界限》《90年代批评》《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我聊故我在》《观念的艺术与技术的艺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演变》《媒介与修辞》《文学批评学》《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等。主编《今日先锋》《媒介批评》和“媒体文化丛书”等。
本书特色
1.一部以诸子互评生动呈现百家争鸣盛况之作。李春青作序,汪民安、李山、张柠一致推荐!
2.以丰富的内容,呈现多元的思想。书中探讨了庄子、荀子、韩非、墨子、管子、杨朱、关尹子等多位先秦思想家的思想,以及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学派的核心观点及其相互关系,展现了百家争鸣的宏大思想图景。
3.视角独特,将诸子互评作为探究诸子文本与思想的切入点。从儒、道、墨、法、名等学派间的辩论中,明晰其间异同,并深挖其产生背景与发展脉络,达成对各学派或人物思想的更深刻理解。
4.独特的学术散文风格。作者以散文的方式谈论严肃的学术问题,将深刻的学理蕴含在轻松幽默的叙事和议论之中,文字省净确当,行文平实畅达,时有诙谐幽默之笔。
编辑推荐
百家争鸣时代的盛景已逝去,我们也只能从诸子文本中一窥其思想世界。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诸子百家间的异远大于同,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或追求修齐治平,或倡言道德逍遥,或孜孜于循名责实……不同的社会背景、学问关怀、思想文本,形塑了诸子的异彩纷呈。但同时,社会转型的大潮之下,各家以不同的路径窥道之一端,以思想适应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
墨子批儒,孟子非墨,庄子鉴孔,韩非解老,彼此间的论辩与攻讦,既是思想的碰撞,也是对时代命题的不同回应。这种深层的共鸣,犹如潜流暗涌,贯穿于诸子的论辩之中,使得看似对立的思想,实则相互砥砺,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基石。
《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不强调同,亦不只关注异,而是在对文本的解读中呈现出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揭示具体语境中诸子共有的思想资源和共同的时代命题,为先秦思想多元一体的独特风貌提供了生动又饱满的注脚。
目录
庄子心目中的孔子
荀子与孟子
韩非说老
墨子非儒
儒门论管子
一毛不拔,千古杨朱
关尹子释道
白马非马公孙龙
道术为天下裂
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附录
格物致知小议
《新序》《说苑》和刘向的施政理念
《洛阳伽蓝记》及其空间叙事
文物与宝物
灵渠
后记
前言
诸子研究的新思路(序)
李春青
研读古籍是难的,研读古籍且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人云亦云,就更难了。进而言之,研读古籍,不仅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把文章写得让人能够读进去,能乐在其中,那简直就是百不一遇的事情了。蒋原伦教授的这部《诸子论诸子》中所收的就都是这样的文章。其文构思严谨而精巧,文字省净而确当,行文平实而畅达,时有诙谐幽默之笔,令人忍俊不禁。读这样的文章不仅可以得到思想上的启迪,而且可以得到阅读的快乐,可以说是一种享受。把文章写得既有学术上自家体悟出来的独到之见,又有令人轻松愉快的“滋味”,那真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
节选
在蒋原伦的笔下,诸子是作为当代人的形象现身的。他们的观念、个性和行为似乎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沟壑而毫无障碍地顽强地存活在我们的此时此刻。在这本书中,我感觉到历史无论发生何等的巨变,但人身上的某些核心却坚不可摧。——清华大学教授 汪民安 《诸子论诸子》视角新颖,必有可观!先秦诸子虽有百多家,但是真正有恒久价值的也就三五家。其中墨家最值得关注,墨家思想代表的是手工业者群体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尤为可贵!作者认为墨子的“非乐”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而是反对靡费巨资的大型宫廷音乐歌舞表演,因为这是“亏夺民衣食之财”而来,可谓所见略同。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 山《墨经》与先秦名学
据说爱因斯坦在 20世纪 20年代到过中国,认为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不爱做实验。这类笼而统之的评价虽然未见确切,但是大差不差。以儒家理念为主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似乎缺的就是这两大方面。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例外,墨家就是这一例外。要说墨家非儒,以今天的眼光看,恰恰是在爱动手实验与数学、形式逻辑等方面的探究上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其他诸子,就这一方面来说,墨家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异数。有人甚至推断墨家,可能是犹太人中的一支,在公元前 6世纪从巴比伦逃难来到了中土,这实在有点玄虚,也意味着华夏人不能自觉地开辟数学、科学和逻辑研究领域。其实这里有偶然性。历史本身就是修剪师,有那么几次失手,就将形式逻辑和实验精神这一枝条给剔除了,其他的枝叶越茂盛,这一支脉就越受压抑、排斥。
如果说古代中国尚有一些数学著作,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也陆陆续续有科技观察和科技实验方面的记录和相应的著述《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那么,逻辑学著作似绝无仅有,这就是《墨经》。所谓《墨经》,是《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的合称(后人又加上《大取》《小取》,共六篇),其内容丰富而庞杂,包括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等多个领域。西晋人鲁胜将此从《墨子》书中抽取,称之为《辩经》,其重点在于突出其逻辑学的内容。故在《墨辩注叙》文中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这里,所谓“以立名本”,就是开创了名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逻辑学。
笔者揣测,可能是为了回应西方有关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的说法,胡适早年的博士论文的功夫就下在《先秦名学史》上,这部名学史,实际上就是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史。该著述的重点就是告诉读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先贤已经就知识的来源,判断和推理、归纳和演绎等逻辑学现象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自觉的表达。在这部《先秦名学史》中,胡适将惠施和公孙龙归在“别墨”一派中(此乃胡适概念上的误用,“别墨”是墨家内部各派之间以自己为正宗,对其他派别的蔑称)。之所以将惠施、公孙龙等归在墨派,是因为公孙龙等所讨论的问题,如白马论和坚白论在《墨辩》中均有提及和得到关注,可谓一脉相承。不过胡适认为《墨辩》诸篇章肯定不是墨子本人所著,因为墨子不太可能既是逻辑学方面最初的发蒙者,同时又是逻辑体系的创始人,并进一步认为《墨辩》诸篇即使不是惠施和公孙龙等所著,也应该是惠施和公孙龙那个时代的作品。
《墨经》与先秦名学
据说爱因斯坦在 20世纪 20年代到过中国,认为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不爱做实验。这类笼而统之的评价虽然未见确切,但是大差不差。以儒家理念为主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似乎缺的就是这两大方面。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例外,墨家就是这一例外。要说墨家非儒,以今天的眼光看,恰恰是在爱动手实验与数学、形式逻辑等方面的探究上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其他诸子,就这一方面来说,墨家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异数。有人甚至推断墨家,可能是犹太人中的一支,在公元前 6世纪从巴比伦逃难来到了中土,这实在有点玄虚,也意味着华夏人不能自觉地开辟数学、科学和逻辑研究领域。其实这里有偶然性。历史本身就是修剪师,有那么几次失手,就将形式逻辑和实验精神这一枝条给剔除了,其他的枝叶越茂盛,这一支脉就越受压抑、排斥。
如果说古代中国尚有一些数学著作,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也陆陆续续有科技观察和科技实验方面的记录和相应的著述《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那么,逻辑学著作似绝无仅有,这就是《墨经》。所谓《墨经》,是《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的合称(后人又加上《大取》《小取》,共六篇),其内容丰富而庞杂,包括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等多个领域。西晋人鲁胜将此从《墨子》书中抽取,称之为《辩经》,其重点在于突出其逻辑学的内容。故在《墨辩注叙》文中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这里,所谓“以立名本”,就是开创了名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逻辑学。
笔者揣测,可能是为了回应西方有关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的说法,胡适早年的博士论文的功夫就下在《先秦名学史》上,这部名学史,实际上就是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史。该著述的重点就是告诉读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先贤已经就知识的来源,判断和推理、归纳和演绎等逻辑学现象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自觉的表达。在这部《先秦名学史》中,胡适将惠施和公孙龙归在“别墨”一派中(此乃胡适概念上的误用,“别墨”是墨家内部各派之间以自己为正宗,对其他派别的蔑称)。之所以将惠施、公孙龙等归在墨派,是因为公孙龙等所讨论的问题,如白马论和坚白论在《墨辩》中均有提及和得到关注,可谓一脉相承。不过胡适认为《墨辩》诸篇章肯定不是墨子本人所著,因为墨子不太可能既是逻辑学方面最初的发蒙者,同时又是逻辑体系的创始人,并进一步认为《墨辩》诸篇即使不是惠施和公孙龙等所著,也应该是惠施和公孙龙那个时代的作品。
有研究者认为,在《墨辩》诸篇中,作者提出了“名”“辞”“说”等称谓,它们相当于现今逻辑学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三种形式范畴。这略有附会,细究起来,只有“名”相当于现今的“概念”,其他的逻辑学范畴在《墨辩》中并没有很对应的词,亦即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是像今天的逻辑学教材那般一一对应。“辩”、“辞”、“说”、“故”(前提)、“类推”(推理)等都反映了那时的逻辑学思想。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还把《小取》中提及的“或”“假”“效”“辟”“侔”“援”“推”,称为“辩的七法”。前两者“或”“假”是“立辞的方法”,“效”是演绎法,“辟”“侔”“援”“推”,都可以叫作“归纳的论辩”。所谓辩就是分辨、判断和区分的意思:“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墨子·小取》)
逻辑学往往是在辨析和辩论中产生的,惠施与庄子辩,公孙龙则通过自辩揭示了逻辑思维上的某些规律。使公孙龙声名大著的是“白马非马”论。不知为何,一直到现今,还有些学者称“白马非马”论为诡辩,公孙龙只不过是说“白马”的概念不同于“马”的概念,有错吗?没错!有一个故事说,公孙龙骑马出关,有关守接到上峰命令,不让马匹出关,于是公孙龙通过一番辩论,说自己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结果就顺利过关。这样一来,一个逻辑命题变成了一则公孙龙如何善于狡辩,以达成自己目的的故事。其实白马非马只是纯粹的逻辑学探讨,只涉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不是将白马看成一匹马的问题。
非常可惜的是,由《墨辩》和公孙龙等开启的形式逻辑和语言学话题,基本就到此为止,后世的学者并没有大的推进。虽然逻辑问题最初可能来自经验,但是由日常经验所造成的困惑一旦获得解决,那么对于超于经验的思辨,许多学派均不感兴趣。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言:“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了解)其意。”人们更倾向于把思辨方面的困惑搁置起来。所以,胡适说墨翟及其学派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也就是说,不排除有个别智者(如鲁胜等)对于形式逻辑问题有关注,但是像战国时期集中探讨数学和形式逻辑问题的学术团体,在两千年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形式逻辑面前,儒家倡导的礼是没有地位的,因为礼法包含着社会传统和具体的生活内容,而在形式逻辑中,这些具体的内容被抽取了。双方意见相左时,在辩论中决定胜负的是逻辑力量,而在礼法中,决定胜负的是社会地位的高低。由此,纯粹的训练思维能力的辩论就被挤出了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
其时,儒家奉《诗》《书》《礼》《易》《乐》为经典,墨家子弟则“俱颂墨经”(《庄子·天下》篇),这就显示出其不同于儒家和其他各家的品行。前文说了,《墨经》不光探讨逻辑学,它也是当时各科知识的教科书。《墨经》中有丰富的生产劳动方面的知识,有杠杆原理,有针孔成像,有几何学知识,等等。也就是说墨家子弟聚拢在一起,并不是念叨“兼爱”“非攻”这些信条,而是诵习墨经,学习科技知识,以运用到生产实践之中。尽管儒家有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但是真正践行“格物”的是墨家。墨家的强项正是儒家的弱项。儒家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仅是社会分工造成的,也表明社会的主流文化轻视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如果说诸子百家中,别的学派是以观念认识的标新立异非儒,那么墨家则是以参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而非儒。
当然,这里似乎有些悖反,墨家是最注重生计实用的学派,因此《墨经》中包含大量的科技生产知识,但是为何《墨经》也关注形式逻辑这类丝毫没有生计实用价值的知识?其实,科技知识的进展必然依赖背后的逻辑思维。从墨家到名家,是思维拓展的必由路径。可惜墨家在近两千年的时光中一直被封存冷藏,直到清代,才为有识有志之士所发现,经毕沅、王念孙、汪中、孙诒让等一番校勘、注释、间诂,才重新见光。20世纪上半叶,在西学东渐、“打倒孔家店”的语境下,墨学研究遂大兴。
——摘自蒋原伦:《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