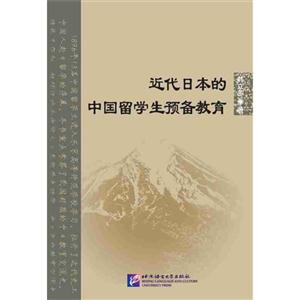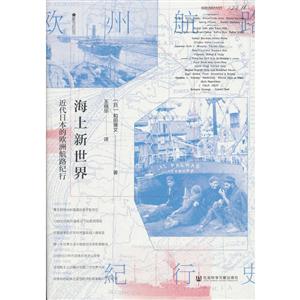作者:坂野润治
页数:212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
ISBN:9787509761656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现实中的政治,虽然不是可计划、可协调的,但也不富有戏剧性。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言人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对于日常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他们又都会采取相当灵活的方式来应对。本书描述了1871~1936年这65年中围绕立宪制或者民主制而形成的保守、稳健、革新三极对立,试图将在计划性协调与戏剧性转换之间所出现的中长期对立与妥协的过程。当作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言人构想政治体制时出现的对立与妥协来加以分析。
作者简介
坂野润治,1937年生,日本国籍。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历任千叶大学副教授、御茶水女子大学副教授,1986年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该书于1997年荣获吉野作造奖。。崔世广,男,1956年6月生于河北枣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松下政经塾特别研究员,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皇学馆大学、上智大学等客座研究员。现兼任中国外交学院兼职教授、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客座所员;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等。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化论。主要著作有《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革与文化建设研究》(主编)等,译著有《从经济看公私问题》、《何为日本人》(合译)等,另发表论文百余篇。。王俊英,女,1965年出生,山西保德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日语及日本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在《日本学刊》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著有《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与文化性格特征》《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一八七一~一九三六)》等。
本书特色
坂野润治著的《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1871-1936)》试图将日本一八七一年废藩置县以后至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发生前的大约六十五年间的政治史,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围绕政治体制构想,相互对立、斗争的过程来进行描述。
之所以把分析的时代限定在这六十五年,是因为在这六十五年间,日本的立宪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人们的尊重,由初期应该引进的制度,最终成为应该维护的制度。代表初期立宪政治构想的,我们可以举出第一章将进行分析的木户孝允一八七三年起草的意见书,即“在文明之国,虽有君主却不擅权专制……为有司者亦保一致协和之民意……人民也戒其超制,有议士者凡事验查,抑制有司随意臆断。此乃政治之美之所以也”。
目录
第一章 强兵、富国、民主化——从“以革命为目的”到“以立国为目的”
前言
第一节 维新目的的再定义与新攘夷论的挫折
第二节 “开发”与“民主化”
结语
第二章 三种立宪政体构想——以英国模式为中心
前言
第一节 明治初期的井上馨——以其立宪政体论为中心
第二节 福泽谕吉的两大政党论
第三节 德富苏峰的议院内阁制论
第三章 《明治宪法》体制的三种解释
前言
第一节 大权政治
第二节 内阁政治
第三节 民本政治
第四章 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崩溃
前言
第一节 民本主义的时代——政党内阁时代的体制构想
第二节 举国一致内阁时期的体制构想——立宪独裁、联合内阁、宪政常道
岩波现代文库版后记
前言
序 言
本书试图将日本一八七一年废藩置县以后至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发生前的大约六十五年间的政治史,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围绕政治体制构想,相互对立、斗争的过程来进行描述。
之所以把分析的时代限定在这六十五年,是因为在这六十五年间,日本的立宪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人们的尊重,由初期应该引进的制度,最终成为应该维护的制度。代表初期立宪政治构想的,我们可以举出第一章将进行分析的木户孝允一八七三年起草的意见书,即“在文明之国,虽有君主却不擅权专制……为有司者亦保一致协和之民意……人民也戒其超制,有议士者凡事验查,抑制有司随意臆断。此乃政治之美之所以也”。本书之所以把一九三六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视为立宪政治的终结,是因为从五?一五事件到二?二六事件这段时期,日本还处在举国一致内阁时代,议会制度尚未从正面被完全否定。关于举国一致内阁时代,我将于第四章的第二节中具体阐述自己的看法,在这里先引用一段二?二六事件发生一年后,回顾事件发生前的举国一致内阁时代的一段文章。
从五?一五到二?二六的四年间,政界经过斋藤、冈田两届内阁逐渐变得无所作为,即政府与政党都在通过政治上的后退来回避与军部的冲突,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军队内部的整肃工作使政治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四年来政界一直处在这样的不抵抗状态,往坏里说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主义状态。……然而,以二?二六事件和广田内阁的成立为契机,军部在事实上展示了其操控政治的能力,从内阁组织的形式到新内阁的施政纲领,如果不采纳军部的主张,任何内阁都无法成立。既然政党内阁遭到排斥,那么即便是中间内阁也得考虑军部的意向。
这段引文的分析尽管有些呆板,但是可以解释本书将分析的范围限定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前的理由。本书把立宪政治由萌芽到终结的这一过程作为分析对象,从一八七一年写起,止于一九三六年,应该是恰当的。
下面,再来谈谈我以“政治体制构想”为基轴,对这六十五年展开分析的意图。
如果以政策对立为基轴来分析日本的政治史,那么,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差异便会变得不那么显著。譬如,在在野党时代反对增税的政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便会断然实行增税政策,这样的情况在战前的日本屡见不鲜。可以说,不论是藩阀政府与民权派政党的对立,还是政党之间,诸如政友会与民政党的对立,都并非本质上的对立。
反过来,如果以运动为基轴来审视日本政治史的发展,那么,体制与反体制、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差异就会被描述成一种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如果站在这样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经与藩阀政府展开正面对决的自由党,在九十年代却加入伊藤博文内阁成为执政党,这样的事态就只能理解为“转向”或是“背叛”。一九○○年,当自由党与以伊藤博文为总裁的立宪政友会合流之际,幸德秋水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典型地代表了这种看法。他说:“岁在庚子八月某夜,金风淅沥,露白天高之时,一星忽然坠地有声,呜呼,自由党死矣,而其光荣历史全被抹杀。”事实上,正如我在第二章第三节中所分析的那样,自由党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四年的这段时间内已经渐进地发生着变化,到一九○○年已经根本不再拥有什么“光荣的历史”。
现实当中的政治史,既不像以政策的对立为基轴所分析的那样,是一种可计划、可协调的东西,也不似以运动为基轴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富有戏剧性的东西。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言人,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自己独自的政治形象,但另一方面,对于日常政治生活当中发生的事件,他们又都会采取相当灵活的姿态来对应。本书试图将在计划性协调与戏剧性转换之间所出现的中长期对立与短期妥协的过程,当作各种政治势力及其理论家们的政治体制构想的对立与妥协过程来加以描述。
描述“政治体制构想”的对立,也就意味着要描述这六十五年间围绕立宪制或是民主制而形成的保守、稳健、革新的三极对立。论及一八八○年前后的立宪政体构想,恐怕大家都会将井上毅、福泽谕吉、中江兆民三人分别视作保守、稳健、革新三种政治势力的代表。然而,在实际的政治史的分析中,这一三极结构却并未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有学者将一九○○年到一九二○年的政治史看成山县派阀与政友会对立的历史,这是仅从保守与稳健对立的视角来看待政治史。相反,也有人把一八八○年代的政治史作为藩阀政府与自由民权运动对立的历史来把握,这是忽略了属于中间势力的稳健派,仅将保守革新对立作为研究政治史的切入点。与前述两种研究方法不同,本书将立宪政体构想作为分析的基轴,并尽可能始终如一地从保守、稳健、革新三极势力的对立中去把握战前日本政治史的发展。即便是在分析穗积八束的天皇亲政论与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的时候也没有偏离这条主线,尽管他们有关《明治宪法》解释的论争很容易被人们理解为二元对立。也就是说本书将北一辉、吉野作造作为第三革新派宪法论的代表人物,放在了与穗积、美浓部对立的位置上。
不过,虽说重视三极结构,但我在大部分时候还是将本书的重心放在了对稳健派的分析上,理由有二。第一,在二元论政治对立的分析中被忽略掉的往往都是稳健派。如果说保守派主张的立宪制的范本是德国,革新派的范本是法国或者苏联的话,那么可以说极易被人们忽略掉的就是以英国立宪制为范本的稳健派了。本书的中心人物井上馨、福泽谕吉、德富苏峰、吉野作造、松冈驹吉等都是在各自不同时代以英国政治为范本的人。虽然不能说是贯穿了本书的全部,但作为一个大致上的框架,以主张英国政体的稳健派为主线,从围绕立宪政体构想而形成的保守、稳健、革新三极对立的视角来描述六十五年间的政治史,可以说是本书的课题。
以稳健派为主线分析战前日本的政治史,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个人在最近十余年间萌生出来的对于稳健派的兴趣,即我很想知道,所谓的稳健派,究竟只是对左右两个极端的反对,还是其原本就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如果稳健派的主张本身即代表着其独立的政治立场,那么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对于他们而言应该不是一件值得悲悯的事情。他们应该对自己稳健派的立场更有自信才对。然而,在这十年中日本所发生的事情似乎表明稳健派的自信在丧失,在衰退。社会主义者不复存在了,接下来如果稳健派也销声匿迹的话,日本的政治该会如何发展,这种不安在自己的历史分析中也曾流露出来,或许就是这种不安才促使我最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三极结构中的中间一极。
上面谈到了自己的兴趣受到近十年来日本政治变化的影响,而本书即是对自己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十年中利用各种机会发表的论文的重新整理和归纳。书中有些部分是原文的保留(第一章以及第二章的第一节),有些则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下面所列举的是本书各章的论文原型。
第一章《明治日本的“立国过程”》,坂本义和编《世界政治的结构变动》第三卷,岩波书店,一九九四年。
第二章第一节 《明治初年的井上馨》,福地惇、佐佐木隆编《明治日本的政治家群像》,吉川弘文馆,一九九三年。
第二章第二、三节《政治自由主义的挫折》,《岩波讲座 日本通史》第十七卷,岩波书店,一九九四年。
第三章第一、二节《作为历史前提的钦定宪法体制》,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现代日本社会》第一卷,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一年。
第三章第三节《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企业民主主义”》,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现代日本社会》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一年。
第四章《政党政治的崩溃》,坂野润治、宫地正人编《日本近代史中的转换期研究》,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这些论文,每篇都会牵出一些回忆。按论文发表年代,第四章最早。《日本近代史中的转换期研究》是我与宫地共同组织的、从事日本史研究的学者与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们的共同研究成果。说得再确切一点,这是研究日本史的学者与以日本史及西欧史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们,试图对战前日本的政治史进行分析的一部著述。从事日本史研究的,除了两名编者以外,还有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威廉姆?斯蒂尔以及现在隶属于京都大学法学部的伊藤之雄。以日本史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学者,有千叶大学的宫崎隆次、都立大学的御厨贵(现就职于东京大学)和现今就职于独协大学的森山茂德。以西欧史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学者,则有东京大学法学部的马场康雄和高桥进参加写作。在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如此阵容有点难以想象,但在当时我才四十来岁,所以每个人都能够从各自专业的观点出发,毫无顾忌地相互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今我依然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个研究会,真是一段难得的体验。
作为构成第三章的两篇论文,是我作为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整体研究”的一员时执笔写成的。“整体研究”是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块招牌。与大学学部里老师要承担教学任务一样,在本研究所里参加共同研究、撰写论文也被视为义务。这种对共同研究的重视,也有批评认为它阻碍了个人的自由研究,但是于我而言,这对于自己专业领域的拓展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前述山川出版社的共同研究也是一样的。我相信,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来说,以跨学科研究之名与别的学派进行切磋,对于扩大自己专业领域内的视野是非常有效的。
第二章的第一节是为了纪念伊藤隆六十岁生辰特意撰写的。回想起来,在我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过程中,伊藤一直是我的指导教师。他不仅手把手地教我学习实证主义史学,而且在艰难的求学时代,还帮我介绍能够赚钱的工作。因为这篇文章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撰写的,所以在本次收录之际,我觉着大部分内容没有修改的必要。
第二章的第二、三节,是对前述《政治自由主义的挫折》一文做了大幅度的增补和修改之后形成的。之所以这样做,最大的原因,是我对德富苏峰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评价有了很大的改变。仅仅时隔两年,评价就有如此大的变化,也许听起来会使人感觉奇怪,但实际上早在这篇论文完成的当时,我自己就已经感到有些困惑。在论文的最后,我当时写了这样几句话:
第二点,苏峰的思想与我原来的预想截然不同,这让我颇感意外。在分析的过程中,有好几次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觉得我是在硬要把苏峰与福泽、吉野等人区别开来。如今,在将这篇论文付梓之际,依然有一些疑点令我难以释怀(《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十七卷,第296页)。
尽管我常常提醒自己,在分析历史人物的时候,应该抛开日本近代历史研究的常识和偏见,要自由地、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评价这个人物,但是对于像德富苏峰这样一个在后世恶名昭著的人物,我还是心存偏见,认为他不应该是一个能够与福泽谕吉和吉野作造相提并论的、主张英国式议院内阁制的论者。为了解开这些让自己“难以释怀”的疑虑,在完成论文的第二年即一九九五年上半年,在研究生院的研讨班里,我与助手及研究生一道研读了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国民之友》杂志。研讨班结束后又与有志者一道共同成立了“明治立宪政治研究会”,研讨班得出的结论作为研究会的共同研究成果,应该会在本书出版发行之前面世(《明治立宪政治的形成过程——《国民之友》的议院内阁制论(一)(二)》,《社会科学研究》四十八卷一?二号)。在本书中,我加入了共同研究中自己执笔的部分,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挫折》一文中的苏峰论做了修正。
第一章是坂本义和教授为纪念他六十岁生辰而编辑出版论文集时,我在其中的一册中撰写的文章。如果是通常的还历纪念论文集,像我这样在学生时代与老师没有接触过的人是不应该参与的,但是因为坂本教授在他亲自编辑的《世界政治的结构变动》一书中,要将我这个日本史研究者撰写的明治政治史收录进去,所以可以另当别论。老师也是出于不同学派间互相切磋的考虑,费了不少的心思。所以,这次我在收录的时候,没有做任何改动。
最后,多亏了岩波书店伊藤修的宽容和督促,我才能够对收录的各篇论文进行增补修正,并使其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在我杂务缠身的时候,伊藤从不会说任何催促的话,但如果我从杂务中解脱出来,第二天他便会来督促我。这让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光靠著者一个人是无法成书的。
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再写几本书已不大可能了。在此,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和孩子,尽管这有悖于日本古来的淳风美俗。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著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