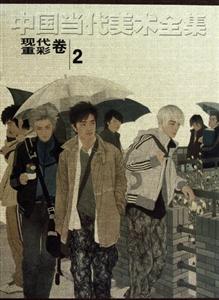作者:高全喜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日期:2014
ISBN:978780769543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独自叩问:漫谈中国当代美术》是高全喜先生继《画与真:杨飞云与中国古典写实主义》之后又一部艺术评论作品集,收录了先生论述当代中国美术的系列文章。高全喜先生在《独自叩问》中分析与解读当代中国美术的独特身位、当代性和处身性,系统梳理当代中国美术的流变;对当代中国油画、国画、雕塑及其他非架上艺术进行纵深分析,并尝试对油画和国画进行分类解读。同时,《独自叩问》对当代一些典型艺术家,如杨飞云、何多苓、潘公凯、吴为山、丁方、张鉴强富有哲理性的心灵解读,对他们在20世纪的艺术历程、绘画风格、绘画题材进行简单梳理和分析,论证其艺术特征形成的重要因素,以及其艺术作品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力量。《独自叩问》既有对当代美术理论的探讨,也有对中国当代美术家的生动分析,对意欲了解当代中国美术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部难得的作品。
作者简介
高全喜
文学、哲学、法学专业背景。由于身染沉疴而游思于艺术,后来沉湎于基督神学,于1998年重新进入学术领域。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相关资料
何多苓正是以其独特的绘画性、灵动的笔触、对造型的把握,以及细微的层次感、微妙的灰色和彩色的交织,来探索写实主义的可能。 ——艺术批评家栗宪庭 多年以来,杨飞云先生手不释笔、勤奋不已,他的语言逐渐得以升华。纯粹语言本身与自然之关系也达到了完美的楔合,不失自然的优美与节奏又兼有语言的高度概括与凝练。 ——知名画家常磊 画家分为两个类型:学究型和明星型,潘公凯属于前者,他的水墨画不为取悦观众和市场而作,格调是高尚和纯正的。 ——徐悲鸿 吴为山的作品与意大利雕塑家曼祖有着精深上的相通,在表现手法上都善于直接用手塑造对象,十分真切。看得出,吴先生所塑的老人是从五千年文化中走出来的。 ——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 三、当代美术的流变
时代与艺术家的生存境况不同,其所赋形的画语世界也就有所不同。中国当代美术在近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平铺直叙,毫无波澜,而是伴随着生存语境的不断深化和流变,呈现出精彩与贫乏之双重景观。那些为艺术而活着的中坚艺术家,他们无论是在艺术的创新、形式的变化、意义的探寻和时代潮流的参与等诸多方面,都以其开放的姿态走在中国新文化的前列,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使他们在变革传统、走向世界的旅途中取得了足可骄傲的成就,他们的作品对此给予了好的见证。我们应该看到,这一两代中坚画家的艺术创作艺术活动所具有的潜在文化意义,便是在他们各不相同的画语世界中展示出与世界文化相遇、沟通和对接的契机。由此可见,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其在朝向新时代的演变中,是完全可以在新与旧的冲中迸发出新的创造力的。
导致中国当代文化流变的,大致包括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画者的生存体验,一是秉承而来的传统,一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必须指出,中国当代文化是发生于汉语本土的文化运动,无论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多巨大,无论所面对的传统有多深厚,当代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上述两个源流的简单继续或重复,而是生发于现时代的属于现代生存之课题的当代文化。也就是说,中国当代美术从根本上是从生存论领域涌现出来并为那些为生存问题所苦恼的艺术家们赋形的当下艺术。任何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西方文化的侵入都无法取消或代替这种关系着每一个艺术家之生存困境的画语言说。传统的东西之所以在这些艺术家身上起着无形的作用,并成为他们力图摆脱的负担,恰恰是因为传统到了今日,已与时代的切肤问题相隔膜;同样,西方文化之所以在当代中国文化中起到不可限量的作用,绝非因为它是西方的,恰恰是因为它所提示的生存与艺术问题在艺术家的心灵产生了共鸣,人类艺术的普遍问题早已超越了地域、时代和种族的界限,而成为当代中国美术本己的问题。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当代中国美术中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即便是同一个类型,其表达的语言方式也各不相同。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美术的流变,构成了艺术家的个性和整个画语世界的丰富性。应该看到,当代美术在保持着先锋性的同时,其处身的基点也相应地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化,它们与中国当代文化的本质性裂变与重铸密切相关。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发展,而毋宁说是流变更为恰切,因为生存的追问在价值性的根基逐渐被消解之后,追问本身也随之失去了意义。所以,一俟艺术的深度与精神的批判退场,代之而起的所谓创新只能是表面的花样翻新,特别是当商品社会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时,灵语中神性之维的缺席,使得繁杂纷乱的艺坛失去了它昔日的真正先锋身位,所谓今日先锋不过是以前卫的狂妄来掩饰其内涵的苍白而已。 三、当代美术的流变
时代与艺术家的生存境况不同,其所赋形的画语世界也就有所不同。中国当代美术在近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平铺直叙,毫无波澜,而是伴随着生存语境的不断深化和流变,呈现出精彩与贫乏之双重景观。那些为艺术而活着的中坚艺术家,他们无论是在艺术的创新、形式的变化、意义的探寻和时代潮流的参与等诸多方面,都以其开放的姿态走在中国新文化的前列,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使他们在变革传统、走向世界的旅途中取得了足可骄傲的成就,他们的作品对此给予了好的见证。我们应该看到,这一两代中坚画家的艺术创作艺术活动所具有的潜在文化意义,便是在他们各不相同的画语世界中展示出与世界文化相遇、沟通和对接的契机。由此可见,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其在朝向新时代的演变中,是完全可以在新与旧的冲中迸发出新的创造力的。
导致中国当代文化流变的,大致包括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画者的生存体验,一是秉承而来的传统,一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必须指出,中国当代文化是发生于汉语本土的文化运动,无论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多巨大,无论所面对的传统有多深厚,当代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上述两个源流的简单继续或重复,而是生发于现时代的属于现代生存之课题的当代文化。也就是说,中国当代美术从根本上是从生存论领域涌现出来并为那些为生存问题所苦恼的艺术家们赋形的当下艺术。任何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西方文化的侵入都无法取消或代替这种关系着每一个艺术家之生存困境的画语言说。传统的东西之所以在这些艺术家身上起着无形的作用,并成为他们力图摆脱的负担,恰恰是因为传统到了今日,已与时代的切肤问题相隔膜;同样,西方文化之所以在当代中国文化中起到不可限量的作用,绝非因为它是西方的,恰恰是因为它所提示的生存与艺术问题在艺术家的心灵产生了共鸣,人类艺术的普遍问题早已超越了地域、时代和种族的界限,而成为当代中国美术本己的问题。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当代中国美术中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即便是同一个类型,其表达的语言方式也各不相同。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美术的流变,构成了艺术家的个性和整个画语世界的丰富性。应该看到,当代美术在保持着先锋性的同时,其处身的基点也相应地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化,它们与中国当代文化的本质性裂变与重铸密切相关。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发展,而毋宁说是流变更为恰切,因为生存的追问在价值性的根基逐渐被消解之后,追问本身也随之失去了意义。所以,一俟艺术的深度与精神的批判退场,代之而起的所谓创新只能是表面的花样翻新,特别是当商品社会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时,灵语中神性之维的缺席,使得繁杂纷乱的艺坛失去了它昔日的真正先锋身位,所谓今日先锋不过是以前卫的狂妄来掩饰其内涵的苍白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中国当代美术的流变仍有着内在的意义,因为中国当代美术本来就只是处在生存边缘上的灵语追问与赋形,历史的传统和西化的侵入都还尚未被这个时期的灵魂创造性地吸收和提升,中国文化的当代性还只是停留在中途的当代性。所以,在一个艺术行进的中途,其流变不仅不可避免,甚至必不可少。况且,我们的文化传统历来就有随缘化形的智慧,众多艺术家的生存处身又有着极大的差异性所以当生存的普遍难题从身心底层向他们袭来时,反应无疑是多种多样的,而似乎每一种又都能在古今中外的学说、画派和手法上找到其合理的说明。
这样一来,对于当代中国美术的流变,就有双重解读,一是表层的文艺学,一是深层的精神学,两个视域的级别和关注点迥然不同。我们认为,中国美术领域十余年的发展流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个阶段是以85美术新潮为代表的中国美术狂飚突进时期,它以其原发的激情为世人所瞩目;第二个阶段是以89-后89美术潮流为表征的中国美术的百家争鸣时期,它在中国式的现代性方面达到有限的极致,并迅速呈现出穷极而衰的特征;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美术,该阶段的突出特征为,在自由的形式下展呈、代美术的多维趋向及歧路盲点,其表现的丰富性、创新性与潜伏其后的精神的苍白和语言的贫乏交错相生。
从文艺学的角度看,三个阶段作为中国当代美术对应西方近当代美术而凝成的缩影,其演变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可以这样说,西方美术近百年来的每一个重大思潮、流派、画风、技巧和观念等都能在今日中国画坛找到痕迹,甚至在有些方面,中国美术由于其传统正反两个方面的多重影响,反而显现出其奇特景观: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边缘理论为前卫性的画家们提供自我陈述的注脚,另一方面,扎根于民族地域的写实主义画家们在顽强捍卫着他们的原则,至于众多的现代画家,则在两种观念及其画语的冲击下逐渐动摇了立足的根基,生存的灵魂颤动似乎在画面的赋形活动中遇到了言说的障碍。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众多各执其辞的画家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当代中国美术在三个阶段的流变中表现出不竭的创造性,这不能不说是文艺学意义上的繁荣。然而,从精神的层面上来透视,中国当代美术的流变过程又是一个艺术精神在赋形中深化与流失的双向互动过程。一方面是精神学意义上的继续发展,一些代表性的画家和作品在生存的深度追问和艺术语言的纯化方面,越来越与人类艺术史上的经典性大师靠近,视觉言说的提升已使有限的自我及其本土语境进入超验之域;另一方面则是精神学意义上的蜕化,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迷失于当下的生活语境,他们的画语与创意看上去自由、潇洒,甚至前卫和具有批判性,实则却相当干瘪、贫乏,其本质不过是调侃后的认同。中国当代艺术近些年来频繁使用着纷乱不同的语题,使人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处身于一个语题缺失的时代。
四、当代画家的两难境地
中国当代艺术主要是指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逾十年的艺术,这里的”当代”并不对应西方20世纪前后现代艺术的”现代”,倒是对应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滥觞期。由于中国的现代艺术是直接从西方现代文化艺术中嫁接而来,又缺乏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像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那样浓厚的精神渊源,因此便形成了如下独特的艺术景观:中国现代艺术既部分吸收了西方古典艺术所具有的品格风范,又吸收了西方现代艺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同时还吸取了西方后现代艺术消解深度的符号样式,这就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只是把诸多来源表面地承接过来。
就中国的现实背景来说,中国当代艺术承揽了西方现代艺术所无需考虑的使命,而这些使命又是原本意义上的”现代艺术”所不能和无法承揽的;再加上与东方传统固有的儒道庄禅思想、文人市井文化、风土民俗情趣的合流,就更使中国当代艺术具有悖逆自身定义的虚假性。这种虚假性表露出以下三个特征:,具有虚幻色彩的表面意味的混合特点。中国现代艺术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无流派性的混乱特征,虽然中国几个断代层的艺术家对所吸收的西方艺术偏重不一,但表面层次上的混合特征却是明确的。比如以知青为主体的艺术家们主要是立足于内在情感的现实批判艺术,稍后的85思潮的艺术家们则立足于精神艺术以及由精神艺术迅速滑落后所谓”当下关注”的政治波普艺术,而更年轻的新潮画家们则干脆立足于市俗波普性质的现世现实艺术。
第二,对西方文化艺术的掺合吸收带有表面的快速流变性特征。中国现代艺术的独特现实背景,使得这种参合吸收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它随着个人的审美情趣或个人在现实生活的遭遇而飘荡,这种状况折射出中国现代艺术的内部结构缺乏一个能够使自身处于”基本信赖”状态的立足点,以致在绝大多数艺术家的作品中几乎都可以看出其平面风格上的滑动性和流变性。
第三,中国当代艺术有着虚假意义上的早熟和早衰特征。中国现代艺术用了十年的时间大致走完了西方大约一百年走过的历程,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缓慢而坚实上升的生命力充沛的艺术形象,而似乎是觉悟成熟于一夜之间,并在此虚幻基础上试图展现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然而这种早熟由于其虚幻性,由于其没有坚实根基的混合流变性,终究难逃肤浅的结果。所以,西方现代艺术中那些令艺术大师们殚思竭虑、苦痛煎熬的根本性灵魂问题,在中国现代艺术历程中并无多少体现,即使有个别人凭敏锐而感触到某些实质问题,也是以机智灵巧的手段浅尝辄止。就这样,那些足以令西方艺术家们精神崩溃、发疯自杀的终极问题被”中国的智慧”化解为无关痛痒的花样翻新和急功近利的粗制滥造。这便是中国现代艺术早衰所必然呈现的症状。
总之,中国现代艺术从一开始就给予读者一种双重感觉-虚假的使命与使命的虚假,也许这仅仅是一个误会,但正是这个误会构成了中国前卫艺术的所谓”前卫性”及其内在的欺骗性。应该看到,中国现代艺术从发轫伊始就是作为非官方的、直接面对现实人生境况的艺术形态而存在的,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均不具有中国现代艺术所具有的那种面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它们大多只是自我的展现,纯艺术形式的标新,或是某种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的直接呈露而已。可是,中国当代艺术一旦作为与过去传统模式和艺术内容截然不同的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出现于中国大地时,便意味着身不由己地被动承负了本身所不应该有或者说不可能有的使命;正是这一”使命”,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更深一层的虚假性。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当代艺术就其本义而言不应该承揽任何使命,其二是中国的当代艺术(由于其自身弱点)也不能承揽任何类似西方精神艺术所曾承负的责任与使命。但恰恰社会与历史的现实境况却硬性要求中国当代艺术必须承揽启蒙的责任与唤醒的使命,因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中国现实的真实状况中的文化误会,它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深刻的两难境地。
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这一误会又在虚假性中展现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时代真实这一另一个视域上的内涵意义,比如知青画家群体、85新潮、现代艺术展等所构成的一系列艺术热点,它们与其说是艺术本身,还不如说是现代艺术具有的社会效应,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生的揭示及至对文化的拓展,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历史的误会恰恰说明了这一两代中国艺术家处身状态的艰难和创作之艰难,他们尽了的努力,但时代总是把他们遗弃在后面。因此,中国的现代艺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两难境地,而这一两难境地又为中国后现代艺术的登场提供了契机。
西方现代艺术本质上的非严肃性在中国(至少是开始阶段)变成了非常严肃的具有社会批判使命及审美价值定位的艺术,兼备了西方启蒙主义所起的功用。即使那些体现个人原始情感宣泄、幻灭的虚无主义、孤傲的个人主义、中国式机智巧慧的艺术作品,也均被虚假地蒙上了思想启蒙的光环。但在这一虚假的光环背后却隐藏着如下事实:由于精神力量的贫乏、品格素质的低下、文化视野的狭窄、发展历程的短浅,中国当代艺术在严格意义上是不能够真正承负那种精神的、文化的、历史的广泛需要的,就如同西方现代艺术也无力承负这些使命一样。如此,中国文化的现实要求和中国现代艺术自身的不足所呈现的矛盾,便导致其向”东方式后现代艺术”的滑落。知青画家群及85新潮画家群的追求,依附于社会给予他们的光环,他们确实认为这一光环是其艺术生命自身赖以生存的基础,就这一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严肃和真诚的,但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他们程度不同地处于自我欺骗之中。产生这样的欺骗是由中国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生长的经历所决定的,这一背景和经历使得他们把社会的责任看得比个人的艺术更为重要,他们把艺术看成陷于痛苦和不幸中的灵魂的表白,是个体心灵与整体社会相流通的途径。他们诚心自愿地沉浸在自我欺骗的罗网之中,而这罗网便是他们的生命本身。他们对于社会人生的真诚,对于艺术的孜孜追求,有别于西方的现代艺术家,这一区别与其说是在作品形式上的,还不如说是在形式之上的”真诚”光环中。
更年轻的、意识更激进的新潮前卫艺术家们清楚看穿了这一两难境况中的虚假性,因此,在”清理人文热情”、”不再被欺骗”、”玩艺术”等喧嚣声中,这批艺术家以看透一切的调侃嘲讽姿态,将旧有的虚假光环抛却。在他们看来,艺术根本不应具有前述的社会功效,社会的功效企图在艺术上有所承揽,完全是找错了门,终只会是历史遗留下的一个笑柄。与此同时,他们本身素质内部的消极因素又与中国传统的市民文化,像《水浒》中的泼皮牛二以及阿Q式的自娱自乐心态,连同民族意识的劣根性合为一体,形成一股没有灵魂的如清仓物质般的大甩卖风潮。这就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当下真实状况。
本书特色
1.高全喜先生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对中国现当代艺术和美术亦颇有研究,曾出版过多部有关艺术、美术理论的书籍;
2.《独自叩问:漫谈中国当代美术》是高全喜先生又一部艺文作品集,既有对中国当代美术理论的探讨,也有对当代美术家的生动分析;
3.《独自叩问:漫谈中国当代美术》精选了当代典型艺术家,如杨飞云、何多苓、潘公凯、吴为山、丁方、张鉴墙,对其绘画风格、绘画题材进行富有哲理性的心灵解读。同时,书中收录了部分当代美术家的经典作品,四色印刷。
目录
一、独特身位
二、当代性与处身性
三、当代美术的流变
四、当代画家的两难境地
五、途中的中国当代美术
六、当代美术的文化意义
当代油画论
一、当代油画导论
二、当代油画分型
1.写实主义
2.表现主义
3.新生代及混成类型
当代国画论
一、当代国画导论
二、当代国画类型
1.新写意
2.新表现
3.形式抽象及混成型
当代美术家片论
杨飞云-古典写实的美质
何多苓-歌咏的忧伤
潘公凯–现代性的追问
吴为山-人文精神的塑者
丁方-精神艺术的变形
张鉴墙-宋庄画家的叙事
后记
附:中国当代美术家画作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