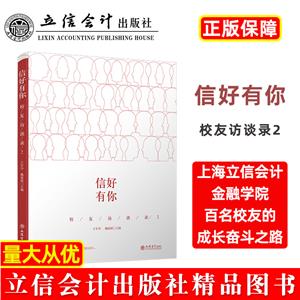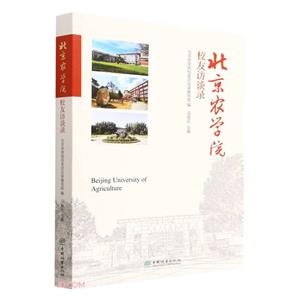作者:陈墨主编
页数:307页
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
ISBN:9787106054816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是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电影频道合作的,以采访和记录老一代中国电影人生平经历并作档案收藏为目的的大型采访工程。该项目于2007年正式启动,2008年全面展开,至2010年为采访工程的第1阶段;2011年起为采访工程的第二阶段。做口述历史,我们是后来者,其便利条件是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汲取先驱者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比较顺利、有效,且有一点特色。 我们的项目名称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而不是“电影口述史”。作为电影资料馆人,我们做口述历史采访的目标,是要作为档案收集,让受访人做生平讲述,包括其电影从业经历、社会人生经历、个人生活与心灵成长经历三个向度,建立电影专业史、中国社会史、个人心灵史三者合一信息档案。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集电影人记忆档案,固然是留赠后人,也应尽可能服务于当下。为此,我们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合作,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将陆续出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30卷。我们采取了四种分卷形式,即单人卷、单位卷(多人)、专业卷(多人)、专题卷(多人),目的是在深度与广度、丰富性与多样性之间获得平衡。
作者简介
陈墨,原名陈必强,1960年生,安徽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文学硕士,退休前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暨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著有“陈墨评金庸书系”,以及《张艺谋电影论》《陈凯歌电影论》《费穆电影论稿》《半间斋影话》《中国武侠电影论》《中国武侠电影史》《黄建新的电影世界》《百年电影闪回》《影坛旧踪》等。从2007年起担任“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访人,采访时长超过1500小时。另著有《口述历史门径》《口述历史杂谈》以及口述史学论文20余万字。
本书特色
采集电影人记忆档案,留赠后人,也服务于当下。 让受访人做生平讲述,包括其电影从业经历、社会人生经历、个人生活与心灵成长经历三个向度,建立电影专业史、中国社会史、个人心灵史三者合一信息档案。 目的是在深度与广度、丰富性与多样性之间获得平衡。
目录
一、家史简述:从山东到陕西
二、人生启蒙:跟着母亲找父亲
三、家乡生活的点点滴滴
四、冒用“吴天明”之名上学
五、初中:在渭南瑞泉中学
六、高中:在西安中学
七、看《海之歌》,报考西影
八、三年困难时期
九、第一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十、第一次演电影:《巴山红浪》
十一、话剧表演:D角及其他
十二、剧团精简及第二次下乡
十三、恋爱、结婚、生女
十四、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红雨》摄制组
十五、从《渭水新歌》到《渔岛怒潮》
十六、受邀参与《生活的颤音》
十七、执导《亲缘》的甜酸苦辣
十八、《没有航标的河流》
十九、拍摄《人生》前前后后
二十、《老井》的创作
采访人手记
穆牧访谈录
一、家庭与家人
二、在北京电影学院
三、到西影
四、恋爱、结婚
五、能演戏我就高兴了
六、没把自己当厂长夫人
七、在美国开录像店
八、对丈夫和自己的简短总结
采访人手记
吴妍妍访谈录
一、童年的记忆
二、回忆在美国的日子
三、爸爸归国以后
四、家人之间的交流
五、对妈妈和爸爸的看法
采访人手记
嵇波访谈录
一、对岳父吴天明的最初印象
二、回顾《百鸟朝凤》的拍摄
三、对岳父吴天明的回忆
四、对岳父吴天明的评价
采访人手记
吴继明访谈录
一、无法接受吴天明“欢乐远行”
二、童年记忆:妈妈、爸爸和哥哥
三、哥俩都叫吴天明
四、回忆吴天明的从艺路
……
吴伟利访谈录
林尊鼎访谈录
编后记
节选
《天明故事:吴天明及其亲友访谈录》: 陈:回到西阳以后,开始上学了? 吴:对,先说在北边的时候,也上过学。我给你说,走这个地方,比如说一共有六个学生,六个学生四个年级。那个破窑洞,或者破草棚子,一个老师,就这种。我记得两个地方,上这种课。有一次我还记得发了新课本,这都是解放区的课本。“东方红,太阳升”,那些课本上都有。黄表纸印的课本,一打开,新鲜得很,石印。黄表纸,硬邦邦的,字清晰得很,还有画的画,工农兵,犁地。要不了几天就毛了,就成油饼了,那个书再一窝,再弄开,那个字毛毛就挡着,就模糊了。那个课本,后来一直留着,初步认识字就是那些。我妈不认识字,我爸又不在,又没有字典,不知道是什么字了。课本一直带着。走个地方,如果有这种学校,就进去报个名。我学会唱第一首歌,是我妈教给我的,“小白菜,溜溜的黄,三岁两岁没了娘。”《小白菜》。后来第二首歌学会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我爸教我的。 到西阳以后就上学,三年级。那时候上学是啥?就是给人家弄一些棉花,或者粮食,拿口袋装上,交学费。就在我镇上,西阳小学。学校有戏台子,一个大操场。我记得有一次为了拍马屁,我把我家我爷爷家破桌子中间的撑子,偷出去送给学校老师,叫老师做打手心的板子,没想到这个板子第一次打的是我。戏台子在教室外面廊檐上,一人多高,不许上。我带着一帮小孩在那玩。老师说下来!排着队,在那打。不许抽,你抽一次,老师没打着,再加一次。打得都肿了,我妈回去就骂。当时好像还是童子军,我就记得唱民国国歌,每天早上升旗。没有穿过童子军的衣服,每天上学背着书包出来进去的。大概不到一年,解放了。 在解放前,这段靠什么生活呢?我家里有20亩地,当时给我姑父种着,我们家在南边有3亩地,我记得种过西瓜,我看瓜园。晚上就住在瓜庵子,瓜庵子是大A字形,铺上床板,一个是看人,一个是獾。看瓜园,瓜从不熟就开始偷着吃。我爷爷一来,哪个地方又少了一个,就扇两个耳光。他开始以为是别人偷的,骂。后来知道是我偷的。还种甜瓜,甜瓜种得少,产量也低,不等熟都吃光了。麦子在北边,给我姑家种。记得收麦子的时候,跟我表妹捡麦穗。那个地是姑父种的,所以我捡麦穗,我表妹不让我捡,追着我撵。我捡了以后就跑。我跟我表妹的关系一直很好。当时小,她家的,不让我捡,后来我妈就骂他们。当时我妈钱是咋来?靠纺线,叫人家去织布,织成布以后(去卖)。有一次拿了三匹布还是四匹布,一匹是十丈,让我姑父捎着卖,结果我姑父说让人家偷了。我妈就知道他昧了,从此跟我姑父关系就不好,跟我姑家的关系都不好。两人到什么时候和解?两个人都老了,80年代了,我父亲不在了,我姑去,那一次,姑嫂才和解,说过去的事就算了。 我家生活当时主要靠我舅家。我舅善良,经常给一些补贴什么的,平常没啥吃的,就去拿点。我舅舅做豆腐,镇子周围还有几个小村子,每天挑着一担豆腐卖。在他家里,我就记得吃豆腐脑,吃豆渣。那个豆渣,锅里蹭一点油,搁一点葱花,搁点盐一炒,好吃得很。后来我再吃豆渣,我觉得难吃得很,那个糙,搁再多的油,搁上肉丁都不好吃。小时候觉得舅舅家的豆渣好吃。我外婆养蚕,抽那个蚕丝,每到这时候我就去给她拉风箱,吃那个蚕蛹,已经煮熟了,拿出塞在嘴里,就等着吃蚕蛹。再就是跟我小舅他家的关系比较好,小舅叫封顺友。但是我舅家穷,我不爱到我舅家去住。就是到姑家,因为姑家表姐、表弟、表妹多,一帮孩子,我们关系很好。我跟我姑关系都很好,我妈跟我姑关系不好,不管她。我们干我们的,我们觉得跟姑家更亲。姑姑对我们很好,对我兄弟几个都很好。在姑姑家,逢年过节打牌,打花花牌。跟表姐、表妹、表弟就玩那个,经常就睡在我姑家,我跟表姐、表妹,我们都在一个炕上。 陈:您母亲还在西阳镇烧过茶炉,是什么时候? 吴:1948年,就是卖茶。就在我们家门口,镇子三天一集,一到逢集的时候,我家院子门口就是街道,拿土坯盘一个茶炉子,卖茶。那个茶叶是什么?根本没有茶叶,是拿榆树叶子摘下来晾干以后,在壶里煮了,一碗一碗倒出来,带点茶叶的颜色。不知道多少钱一碗。一碗一碗晾在那,上面有时候就盖着一个板,怕灰,怕苍蝇。我就记得我在那拉风箱。当时夏天,穿开裆裤,那时候已经八九岁了。开裆裤还是啥裤?把棉裤一套,两层,夹裤。当然不好意思,人前头不能让人家看见,但是屁股露着。是烧的木炭,那种炭不太好烧,一弄多半天,水烧开了,我才能去玩,去捡瓜子。其他时间我还得看孩子,那时候小家伙还活着,还得看孩子。另外一有空,人家吃西瓜,我就捡那个西瓜子。还得淘不是?你还得捡了淘,先把地上捡光,然后要吐的时候,赶快拿手,钻在桌子底下拿手接着,吐到我手上,搁到碗里。回去拿水一清,不然有泥。淘完了以后,把它晾干,第二集卖西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