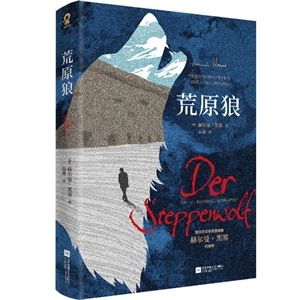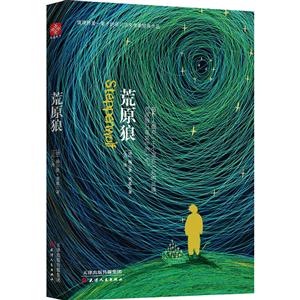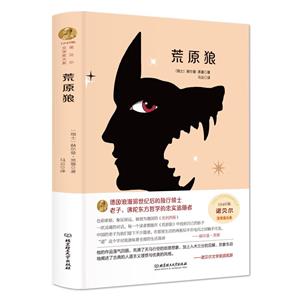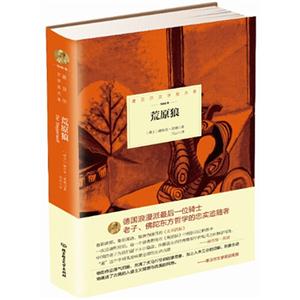作者:赫尔曼·黑塞
页数:256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
ISBN:9787533971014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荒原狼》是黑塞出版于1927年的长篇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它是赫尔曼·黑塞以对主人公哈里·哈勒的考察,力求揭示和解决其本人与大众文化、工业社会和权力阶级的冲突以及深层心理危机的文学表达。
作者简介
赫尔曼·黑塞 | Hermann Hesse
(1877—1962)
作家,诗人,画家。
1877年生于德国,1923年入籍瑞士。
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被誉为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位骑士。 主要作品
1904 《彼得·卡门青》
1906 《在轮下》
1919 《德米安》
1922 《悉达多》
1923 《辛克莱的笔记》
1925 《温泉疗养客》
1927 《荒原狼》
1930 《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
1943 《玻璃球游戏》 译者
姜乙,女,先后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和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现居北京。
本书特色
“我们所知的世界,包含其中的不公、腐朽和恶意,如何与我们信任的理想和至高愿景相协调?
一切赋予生命价值的神圣事物——美、爱、真理和善,是真实的还是空洞的幻象,给人慰藉的错觉,我们最珍视的希望和创造?
音乐仅为娱乐服务,还是一条步入内心的通道,让人类在被异化的现实中得以肢解自我并在忘我的状态下获得瞬间的幸福并回忆天堂?
我们的自我,被扼杀在社会的诫命下,又为何深感成为真正的人,成为不朽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如果生命终将结束于坟墓中,我们又为何致力于艰辛地塑造自我,探索永恒?”——姜乙
一百年前黑塞借荒原狼哈里·哈勒之笔写下的预言在往后的时间里一一应验。
在《荒原狼》中你可以看到不曾见过的、令人可畏的坦诚,它是知识分子式的,更是生而为人的坦诚。
如果二十世纪以来有过某种向内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那一定来自黑塞笔下的角色。
可以确认的是,同《悉达多》一样,《荒原狼》同样是一首长诗——
“这是一场对生而为人的最残酷的庆祝,是一部反对平庸的充满勇气的诗篇。”
节选
本书是一个人留下的笔记。这个人,我们依其多次自封的绰号称其“荒原狼”。他的笔记是否需加导论性前言姑且不论,我本人却想在荒原狼的手稿前寥记几笔,以写下我对他的回忆。我对他所知不多,特别是他的过往和来历,我一概不知。但这个人的品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无论如何我必须说,我对他心怀同情。
荒原狼是个年近五十的男人。几年前的一天,他来到我姑母家,说要找个带家具的住处。他租下了顶层阁楼和旁边的小卧室,并于几天后带着两口箱子和一只大书箱再来,在此住了十来个月。他生性喜静,孑然一身,要不是我们卧室毗邻,偶尔能在楼梯和走廊相遇,我们根本无从相识。与人交往,此人并不在行。就我的观察,他的孤僻无人能及。他的确如他时而自称的一样,是匹荒原狼:本性陌异,狂野,羞怯,甚至十分羞怯,来自一个较之普遍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至于他因资质和命运究竟生活在多深的孤寂中,他又如何自知这种孤寂乃为他的命运,我是后来读他留下的笔记才有所了解。在此之前,我跟他通过几次偶遇和攀谈相识,我发现,尽管在我们的交往中,我对他的印象难免模糊片面,却和我在他笔记中获得的认知基本吻合。
荒原狼初次踏入家门,问我姑母租房的一刻,我恰巧在场。那是个正午,桌上还摆着餐盘,离我出发去店里还剩半小时。我无法忘记他当时在我眼中的奇异与矛盾。他拉了门铃后走进玻璃门,我姑母站在昏暗的过道问明他的来意。可是他,荒原狼,却警觉地昂起留着利落短发的头,用他神经质的鼻子四下嗅着,既没回答,也没道出姓名,而是说:“哦,这里真好闻。”说着,他露出微笑。我好心的姑母也跟着笑了。而我却觉得此人的问候未免荒谬,心生反感。
“是的。”他说,“我是来看您要出租的房子。”我们三人上了楼梯,走向阁楼时,我才看清他的模样。他个头儿不高,却有着大高个儿的神态举止。他身穿一件时髦舒适的冬大衣,仪表得体却不修边幅,短发已有些花白,胡子刮得精光。起初我并不喜欢他的步态,疲惫拖沓,优柔寡断,和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以及说话时奔放的腔调极不相称。后来我才知道、注意到,他腿脚不好,这让他举步艰难。他面带固有的令人不适的微笑,打量着楼梯、墙壁、窗户以及楼梯间高大老旧的柜子。看上去,他似乎喜欢这一切,却又同时对这一切感到好笑。总之,此人给人的整体感觉是,他来自一个陌生世界,来自异地他乡,认为我们这里的一切很美,却也有些可笑。对于他,我只能说,他很客气,也算友善。他对房间、房租和早餐毫不迟疑地表示满意。但在他的周身,却洋溢着拘谨的、令人不快的、充满敌意的气息。他租下了阁楼和一间小卧室,认真而耐心地了解了关于暖气、用水、服务和房客管理条例等事宜,表示完全同意,并马上支付了定金。可同时,他又有些魂不守舍,似乎自觉行为古怪,进而玩世不恭,好似对他来说,租房子、与人用德语交谈十分稀罕,而他心里正琢磨着与此毫不相干的事。这就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并不太好,倘若不是他在各种各样的细微之处纠正和补充了我最初的印象——比如他的脸,虽说有几分奇特,却从一开始就很打动我。那是张或许有些特殊,有些忧伤,却清醒、深思熟虑、充满智慧的脸。此外,博得我好感的还有他的态度:尽管他颇费周折才表现出礼貌友善,却丝毫不傲慢。他的态度,相反,近乎恳切,近乎动人。这一点,虽然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却马上被他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