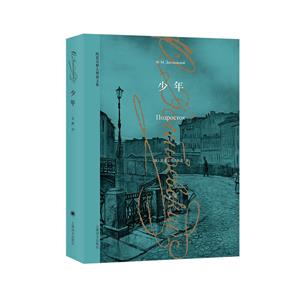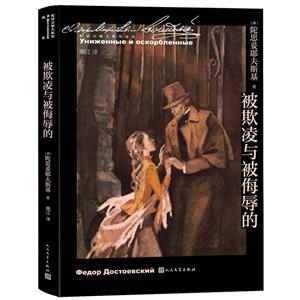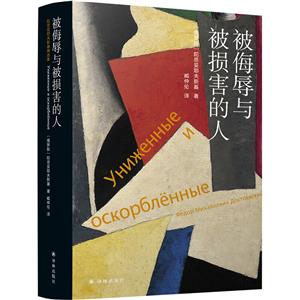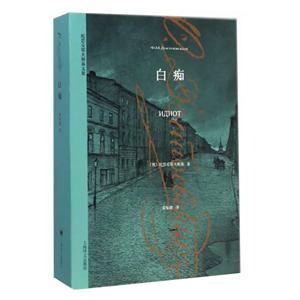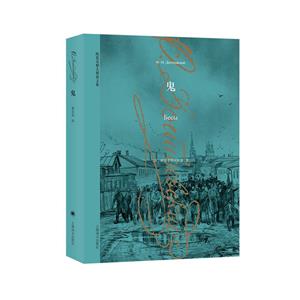作者:[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刘季星/李鸿 译
页数:320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
ISBN:9787530654316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国读者中早已以他的长篇小说享有盛誉。《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收作者的散文二十九篇,计二十万字,大多选自上述的《作家日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的海洋中,这只不过是一捧水珠、一串浪花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最后一篇散文是《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1862年初次出游欧洲五国后所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所选译的二十九篇散文,除了《农民马莱》、《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两篇之外,似乎——因为孤陋寡闻,信息不灵,不敢肯定——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
作者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著名的俄国作家。他于1844年开始文学生涯。作为小说家,以其《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鸿篇巨制早已享有世界性的盛誉。而本书汇其游记、随笔、抒情散文、评论、演说于一集,以不同时期的不同体裁、题材、风格,异彩纷呈地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散文创作上的非凡成就。 本书系第一部中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集。选译二十九篇力作,约二十万字,其中绝大部分篇章为首次译成中文。
目录
小小的图景
带着一只手的男孩
在耶稣身旁过圣诞节的小男孩
百岁老人
农民马莱
信使
被捕之夜
当代的一种伪善
再谈妇女
车厢里的俄国人
不可思议的怪事
征订1861年《当代》月刊启事
写作计划
爱伦·坡的小说
关于西欧作家
关于《巴黎圣母院》
略谈乔治·桑
旧时相识
一件私人的事
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
《安娜·卡列尼娜》。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
俄国的讽刺作品。《处女地》。《最后的歌》。旧时的回忆
涅克拉索夫逝世。关于在他墓前的演说
普希金、莱蒙托夫与涅克拉索夫
诗人与公民。对于作为凡人的涅克拉索夫的总的看法
对涅克拉索夫有利的证人
普希金——1880年6月8日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大会上的演说
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
第一章 代序
第二章 在车厢里
第三章 即完全多余的一章
第四章 对旅客并非多余的一章
第五章 太阳神
第六章 试论资产者
第七章 前一章的续篇
第八章 小鸟和“我的宝贝”
译后记
节选
不久以前我还绝对无法想象彼得堡的居民必定穿着睡袍,戴着小帽,关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以不可推卸的义务每隔两小时服一汤匙什么东西。当然,不完全是生病。义务不准许某些人生病。另外一些人则有他们魁梧的体质守护着。于是到最后,太阳出来了,这件新鲜事毫无疑问比其他任何东西更有价值。大病初愈的人正在犹豫,考虑到要整饬仪容,不大放心地脱去小帽,终于同意出去走一走。自然是要全副武装,穿上绒衣,皮大衣,套鞋。暖和的天气,街上人群中某种节日的气氛,轻便马车在袒露的路面上行驶的震耳欲聋的响声,使他感到惊异和愉快。最后,在涅瓦大街上,大病初愈的人张大嘴巴竟把新的灰尘吸了进去!他的心开始跳动,他撇了撇嘴,好像是微笑,他的嘴唇一直紧闭着,表示怀疑和不信任。清除了大量的污泥及湿气之后,彼得堡最初的灰尘是甜美的,当然,不比家乡炉灶上冒出的古老的炊烟逊色。散步的人脸上的疑虑消失了,最终决定欣赏春天的美景。一般地说,凡决定欣赏春景的彼得堡居民,他身上都有那么一种天真纯朴的东西,似乎与他的欢乐不可分割,甚至当他遇见一个朋友的时候,会把平日不离嘴边的问题“有什么新闻吗?”忘掉,而提出另外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天气怎么样?”当然,问完天气以后,特别是当天气不好的时候,彼得堡最令人难堪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新闻吗? ”我经常发现,当两个彼得堡的朋友在某地相遇,双方互致问候以后,异口同声地提出一个问题:“有什么新闻吗?”在他们的声音中有那么一种直透肺腑的苦闷,无论谈什么话都有那样一种声调。确实,彼得堡的这个问题笼罩着绝望的阴影。但是最令人感到可耻的是,经常这样提问的人却是一个完全冷漠的人,他在彼得堡土生土长,完全了解本地的习俗,事先知道人家不会回答他的问题,知道没有什么新闻,即使不多不少提出一千遍,也毫无结果,因而早就不以为怪。但他仍然要问,似乎很感兴趣,似乎是某种礼节迫使他也参加一种社会活动,具有共同的兴趣。不过,谈到共同的兴趣,……我们是有的,我们没有人表示异议。我们大家都热爱祖国,热爱我们亲爱的彼得堡,有机会也喜欢玩~玩。总而言之,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但是我们更流行的是“小团体”。甚至每个人都知道,整个彼得堡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不可胜数的小团体的大聚会,每一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礼仪,自己的法律,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神谕。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产物,这种性格对社会生活还有点不习惯,眼睛常往家里看。而且参加社会生活需要艺术,需要准备很多条件,总而言之,待在家里更舒服些。在家里比较自然,不需要艺术,更清静些。在小团体里大家会很爽快地回答你的问题:“有什么新闻吗?”问题立即有了个人的意义,你听到的答复或许是一种挑拨,或许是哈欠连连,或许是那些会使得你像白发苍苍的老朽一样也不知羞耻地打起哈欠来的东西。在小团体里,可以用最平心静气和最愉快美满的方式,在哈欠和挑拨声中延长你的有用的生命,直到流行性感冒或者腐蚀性的热病踏进你的家门,你将硬着心肠离家而去,处之坦然,而且你不知道会遇到这一切,为什么会遇到这一切,实在幸运。你将在黑夜中,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在没有一线光明的流泪的白天中死去,完全不明白这一切安排得能使你活了一辈子(似乎活过),活到了一定的岁数,因此现在就不得不抛弃这个愉快而平静的世界,移居到更好的地方去了。其实,有些小团体对事情的讨论是很激烈的;几个有文化而好心肠的人热情地聚在一起,用极端的手段取消一切无害的如同捕风捉影的议论和纸牌之类的娱乐(当然,不是在文学小组里),并且怀着难以理解的兴致谈论各种重要的话题。最后议论完了,话讲完了,几个对大家有利的问题也解决了,所有问题彼此都说通了,整个小团体就会处于某种激动状态,某种不愉快的涣散的状态。最后互相怒目而视,说出一些尖锐的实话,暴露出某些急躁和粗鲁的个性,结果闹得四分五裂。大家都心安理得,积累了大量生活经验,于是渐渐地形成了上面最初所描绘的那种性质的小团体。当然,这样生活是愉快的;但最后又会感到苦恼,苦恼得难以忍受。比方说,我对我们那个古板的小团体感到苦恼,因为这个小团体里经常会弄出一个最叫人讨厌的家伙。先生们,你们非常熟悉这些家伙。他们的人数多得不得了。这些家伙只有一副“好心肠” ;除了“好心肠”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年头有一副好心肠,好像是一件稀奇的宝贝!最后,小团体是这么需要他,仿佛他是个永远不变的“好心肠”!这个家伙既然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品质,他进入上流社会时就完全认定他的好心肠肯定会使他永远心满意足和幸福。他坚信自己会成功,因而忽视为人生道路上所准备的其他一切手段,比方说,他一点也不知道约束和克制。他坦白直率,事无不可对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