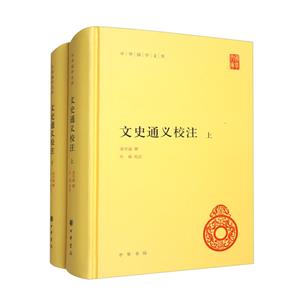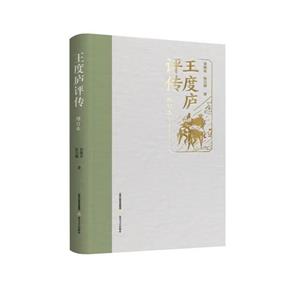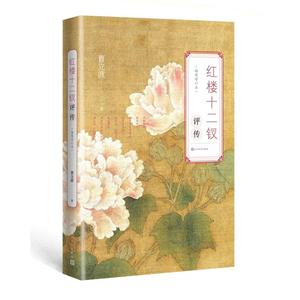作者:仓修良 叶建华
页数:346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10021413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资料翔实,论点有据,行文流畅,颇多精彩之处。章学诚是清代有名的学者、思想家。他一生坎坷,却能在学术文化方面取得杰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史学、方志学、校雠学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真正做到了集古之大成,成一家之言。他在社会政治、哲学、文学、教育学、谱牒学等方面,也都提出过许多富有时代意义的独到见解。全书共分11章,分别阐述了章学诚生活的时代背景、生平事迹和著述、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史学理论、方志学理论、校雠学理论、谱牒学理论、文学理论、教育思想以及与浙东学派的关系等等,并对章学诚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目前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作者简介
仓修良(1933-2021),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囤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浙江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宁波大学、温州大学兼职教授等。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叶建华,1987年硕士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导师仓修良教授),现为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民营经济发展中心研究员,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历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市场导报社社长等。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方志学、浙江历史文化、浙商和民营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本书特色
全面系统地论述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家,其对中国文史传统的系统阐释总结,超迈前贤,可为集大成式的史学理论高峰。本书资料翔实,论点有据,行文流畅,全面详尽地介绍了章学诚的行迹与思想,对其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目录
第一节 专制政策及其对学术文化的影响
第二节 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风
第三节 在“乾嘉盛世”的背后
第二章 穷困潦倒的坎坷一生
第一节 “意气落落,不可一世”的青年时代
第二节 “不合时好”,不敢入仕的中年时代
第三节 为人幕僚,“坎坷潦倒”的晚年
第四节 集古大成,成一家之言的史志著作
第三章 倡言改革的社会政治思想
第一节 “三王不相袭,五帝不相沿”的社会变革思想
第二节 “以吏治为急”的政治改革方案
第三节 “时会使然”的人才论
第四章 朴素唯物论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道不离器”的天道观
第二节 “效法成象”的认识论
第三节 “不负我生”的人生观
第四节 “天德天位”的伦理观
第五章 杰出的史学理论家
第一节 史学经世论
第二节 六经皆史论
第三节 史义论
第四节 史德论
第五节 史书编纂论
第六章 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
第一节 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
第二节 方志编纂理论
第三节 章学诚方志理论的三大来源
第七章 集古之大成的校雠学理论
第一节 校雠学的目的和任务
第二节 校雠学的起源和发展
第三节 校雠学的理论和方法
第八章 “史部支流”的谱牒学理论
第一节 谱牒学的性质和作用
第二节 谱牒学的起源和发展
第三节 谱牒的编纂原则和方法
第九章 别具一格的文学理论
第一节 文贵“明道”、“用世”
第二节 倡导“文德”
第三节 “文理”说
第四节 “清真”说
第十章 蕴意丰厚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学以致其道”的教育目的
第二节 “通经服古”的教学内容
第三节 “尽人达天”的教学方法
第四节 可贵的治学经验
第十一章 浙东史学的殿军
第一节 浙东史学的概况
第二节 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
结束语
后记
附记
节选
《章学诚评传(增订本)/仓修良文集》: 一、手段成为目的,博古而不通今 由于清政府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推行,造成了乾嘉时期社会学术风气大变,与清初相比显然已经大不相同。清初学者治学所关心的是当世之务,他们所提倡的考据,确是为了矫正宋明理学空言心性、束书不观的弊病,并且与反对清初民族压迫的现实斗争形势密切相关。他们提倡“实学”,要求研究历史真相,是为了博古通今,经世致用。所以,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和地理形势也就成为他们治学的重点,而各自著作,亦多言有所指,有理论,有思想,观点鲜明,决不作“无病呻吟”。可是,乾嘉考据学者虽然在治学方法上继承了清初大师们所开辟的道路,但却抛弃了大师们治学的精神实质。尽管他们把训诂、校勘等考据深入到经史子集各方面文献,可惜的是,他们把治学的手段变成了目的,为考据而考据,他们囿于古而蔽于今,博古而不通今,抛弃了“当世之务”的目标。考据学成为清廷用来粉饰所谓“乾嘉盛世”的点缀品,成为统治者歌颂“升平气象”的工具。生活在当时的章学诚对这种局面己深表不满,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和许多文章里都批评了这个怪现象,指出:“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动引刘子骏言‘与其过废,无宁过存’,即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又说:“方四库征书,遗籍秘册会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绩之勤,为功良可不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生之志焉者,则河汉矣。余尝语君,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他把这些“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的考据学者斥为“俗儒”,嘲讽他们“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遗憾的是,在当时考据学以压倒一切的优势笼罩整个学术领域的情况下,像章学诚这样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考据学风所囿而予以批评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他们依旧无法扭转整个时代的学术风气。诚如学诚死后5年出生的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1806-1873)所言:“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本来,在当时资本主义继续萌芽发展,新的市民阶层不断出现并与封建经济体系产生矛盾的社会条件下,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应该出现一种新与旧、生与死的对立冲突和尖锐斗争,产生一股生机勃勃、代表新事物新势力的力量。鞭挞旧世界,向往新的未来世界。但是,由于清政府推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垄断控制了学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从而限制和扼杀了任何进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这种局面下出现的乾嘉考据学,丝毫不代表社会的进步思潮,依然是封建专制主义幽灵的顽固体现。他们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大胆揭露和批判,更没有对未来新世界的憧憬和追求。他们甚至高呼“回到汉代去”的口号。他们从博古、求古、存古,发展到尊古,甚至是“舍古无是”,泥古不化。看看他们对于当代史迹的关心和记载情况,并与宋代稍作对比,便可一清二楚。宋代史学的最大特色,便是详于当代史迹的记述,能够及时地把现实的社会变化和政治得失编写成书。有的学者早就指出,这是宋代史学最成功的地方。当时由于统治者非常注意时事的编纂,所以激起学者们私人编修当代史的勇气,许多人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当代史著的编撰上。如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自称“网罗收拾垂四十年”,“精力几尽此书”。这与乾嘉学者的“皓首穷经”,把毕生精力埋在故纸堆中形成鲜明的对照。宋代学者私人所编当代史著之多,除李焘所著外,著名的还有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度的《国纪》、王偶的《东都事略》、熊克的《中兴小纪》和《九朝通略》、赵牲之的《中兴遗史》、李丙的《丁未录》、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江少虞的《皇朝事实类苑》、李攸的《皇朝事实》以及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等等。虽然宋统治者偶尔也曾有过几次“野史之禁”,但多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党派和权臣挑起,而且时间相对短暂,危害面也不大,绝没有像清朝一样,上自最高统治者,下至一般的权臣奸佞,一致行动,贯穿始终,波及全国。所以,乾嘉学者私人编修当代史,几付阙如。 乾嘉学者的“博古而不通今”,再次证明清统治者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残暴及其危害之极!诚如郭沫若同志早已指出的:乾嘉时代考据之学,“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于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