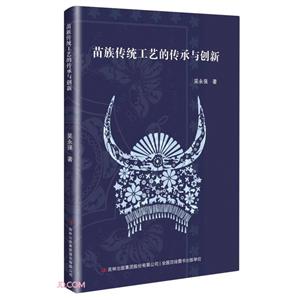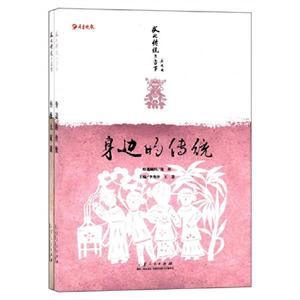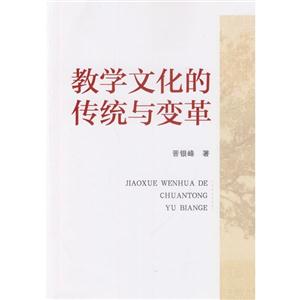作者:余冠英
页数:400
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807683438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提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余冠英,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他选注的《诗经选》《乐府诗选》等。在经典选注中,他十分重视诗人的写作个性及其诗歌的艺术特点,着力剖析诗作的语言结构,将普及文学经典与促进语文教育结合起来。在选注之外,他还写了很多说诗的论文,或考论诗歌发展源流,或鉴析具体诗歌作品。
此书为余冠英平生诗歌研究、选注讲读的精粹,共三十余篇,分考镜诗源、读诗释疑、注诗选摘三部分,系统体现了他在说诗、注诗与学术研究方面的经验、识见与贡献。
作者简介
余冠英(1906—1995),江苏扬州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教授,主编《国文月刊》。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任该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遗产》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著有《汉魏六朝诗论丛》《诗经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等。 刘跃进,1958年生,吉林白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中国文学年鉴》主编,兼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等。 蔡丹君,1981年生,湖南株洲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著有《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十六国北朝文学》《浮世本来多聚散:唐诗中的二十一种孤独》《见南山:田园诗史话》等。
本书特色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余冠英 讲给大家的诗词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蔡丹君 编选整理,万字精彩导读诠释大师卓越成就;★回归经典、细读文本,品悟古典诗词之美,了解诗的传统与兴味,在普及文学经典中接受语文教育。★装帧大气别致,内外封典雅,镂空工艺,进口轻型纸,厚却轻,书脊锁线,可完全摊开阅读。
目录
导 读…………………………………………………………..刘跃进 蔡丹君 1
考镜诗源
《诗经选》前言……………………………………………………………………………………….. 20
《汉魏六朝诗选》前言…………………………………………………………………………. 45
《三曹诗选》前言…………………………………………………………………………………… 72
《乐府诗选》前言…………………………………………………………………………………… 95
七言诗起源新论……………………………………………………………………………………. 111
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 135
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 147
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 155
《中国古代山水诗鉴赏辞典》序……………………………………………………. 177
《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序…………………………………………………………. 179
中国古代民歌的成就………………………………………………………………………….. 186
读诗释疑
关于改《诗》问题………………………………………………………………………………. 196
关于《陈风·株林》今译的几个问题………………………………………… 212
关于《诗经·伐檀》篇和乐府《孔雀东南飞》的一些问题……. 218
《诗经·郑风·将仲子》乐府新声……………………………………………….. 223
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 226
四言、五言和七言………………………………………………………………………………. 236
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 248
曹操的两首诗………………………………………………………………………………………… 254
建安诗人代表曹植………………………………………………………………………………. 259
论蔡琰《悲愤诗》…………………………………………………………………………………. 271
说“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 281
关于《孔雀东南飞》疑义………………………………………………………………… 285
说鲍诗………………………………………………………………………………………………………. 293
《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 294
谈《西洲曲》…………………………………………………………………………………………… 308
李白纪念馆成立纪念………………………………………………………………………….. 314
诗论十首………………………………………………………………………………………………….. 315
注诗选摘
《诗经》今译六篇…………………………………………………………………………………. 320
《诗经》今译六首…………………………………………………………………………………. 335
汉铙歌六曲注………………………………………………………………………………………… 351
《古诗十九首》注…………………………………………………………………………………. 357
《别诗》四首注……………………………………………………………………………………… 376
《别诗》三首注……………………………………………………………………………………… 381
鲍照诗十首注………………………………………………………………………………………… 384
节选
试读一: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
国语里有一种复合词,由并行的两词组成,在句中有时偏用其中一个的意义,可以称为偏义复词。例如:
“费了那么多精神,到后来还要落褒贬,真不值得!”
“我的丈夫受了重伤,万一有个好歹,叫我怎么过!”
这里“褒贬”偏用“贬”的意义,“好歹”偏用“歹”的意义。“褒贬”“好歹”都成为偏义复词。这种复词在古文里也
并不少见。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七,首先举出“得失,失也”“利害,害也”“缓急,急也”“成败,败也”“异同,异
也”“赢缩,缩也”“祸福,祸也”七例。俞曲园《古书疑义举例》卷二续举“因老而及幼”“因车而及马”“因父而连言
母”“因昆而连言弟”“因妹而连言姊”“因伯而连言男”“因败而连言成”七例。黎劭西先生曾著《国语中复合词的歧义和偏义》一文,载在《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添举“会同”“朝夕”“耳目”“日月”“禹稷”等八例。《燕京学报》第十二期有刘盼遂先生《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一文,又补了“爱情”“陟降”“强弱”“朅来”“安危”“虚盈”“是非”“动静”“上下”等十七例。在诗歌里,因为凑字足句的关系偏义复词也许更多些。本文单从汉魏诗歌续举十七词。这类复合词的辨别往往关系诗的了解,提出来作为讨论资料,似乎不为无益而还可能是饶有兴趣的事情。
(一)“死生”,死也。汉乐府相和歌古辞《乌生》篇:“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李因笃《汉诗音
注》说:“弹乌、射鹿、煮鹄、钓鱼,总借喻年寿之有穷,世途之难测。”这是本诗的大旨。上面所引的两句是本诗的结尾,意思是说夭寿全属天命,死亡早迟是不足计较的。这里因“死”而连言“生”,“生”字无义。这是所谓句中挟字法。
(二)“东西”,东也(或西也)。汉乐府相和歌《白头吟》本辞:“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次句费解。既是沟中的水就只能东流或西流,不能既东又西。假如“东西”不是偏义复词,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一条南流或北流的水注入和它垂直的沟,水分东西两头。但是如参看南朝《神弦歌》里的“蹀躞越桥上,河水东西流,上有神仙居,下有西流鱼”等句,就知道这样的说法不妥。《神弦歌》的河,只是一条河,因为已说明在一座桥下。从“西流鱼”三字看来,“东西流”实在就是东流,因为“河水”和“下有”两句是以古乐府《前缓声歌》“东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鱼”一句为根据的。由此推论《白头吟》篇的“东西流”,虽不能断言是东流还是西流,“东西”一词用成偏义是很可能的。
(三)“嫁娶”,嫁也。同篇:“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是说人家嫁女常常啼哭,其实嫁女是不必啼哭的,只要嫁得“一心人”,到老不分开,就是幸福了。全诗都是女子口吻,这几句也是就女子方面说。“嫁娶”也是用偏义。
(四)“松柏”,松也。汉乐府相和歌辞《艳歌行》“南山”篇:“南山石嵬嵬,松柏何离离。”这是开端的两句,下文说“洛阳发中梁,松树窃自悲”“斧锯截是松,松树东西摧”,又说“本自南山松,今为宫殿梁”,全篇只写松树的事。开端虽然松柏并提,“柏”字不过是连言而及。
(五)“木石”,木也。汉乐府杂曲歌古辞《前缓声歌》:“心非木石,荆根株数,得覆盖天。”木与荆有根株,石不能有根株。“木石”是常常连言的,所以这里因“木”而及“石”。
(六)“公姥”,姥也。汉乐府杂曲歌古辞《孔雀东南飞》篇“便可白公姥”,又“奉事循公姥”,又“勤心养公姥”。三句都是焦仲卿妻刘氏的话,但细观全诗,焦仲卿的父亲应已不在世,否则诗中有许多地方便说不通了。仲卿决心自杀时说“令母在后单”,从这句话可以见出他没有父亲。诗中叙刘氏嘱仲卿“便可白公姥”,接着便叙仲卿依嘱行事——“堂上启阿母”,从这里也可以见出仲卿没有父亲。刘氏口中屡次所说的“公姥”意思只指阿姥。这和俞曲园所举《礼记·杂记》篇因父而连言母,黎劭西所举《毛诗·将仲子》因母而连言父属于一类。
(七)“作息”,作也。《孔雀东南飞》篇又有“昼夜勤作息”一句,旧注解“作息”两字多不可通。闻一多先生《乐府诗笺》说:“息,生息也,作息谓操作生息之事。”虽属可通,还嫌生强。作息自是对待的并行词,白居易诗云“一日分五时,作息自有常”,这是“作息”通常的用法,和今语相同。这诗的“作息”用成偏义,“终日勤作息”就是终日勤于劳作,也就是上文所谓“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的意思。
(八)“父母”,母也。同篇:“我有亲父母。”和上举“公姥”例相似,这是因母而连言父。刘兰芝没有父亲也是显而易见的,她如有父亲就不当说“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了。她的婚姻也不能“处分适兄意”,应当让父亲去做主了。
(九)“父兄”,兄也。同篇:“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兰芝无父,说已见上。这里“亲父兄”意思只是“亲兄”,“父”字是因“兄”而及。有人说同父之兄叫作亲父兄,似乎缺乏根据。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将这里的“亲父兄”和《上留田行》的“亲父子”相比附。《上留田行》并非完章,那几句诗究何所云,难有定说。“亲父子”的“父”字很可能是“交”字之误,和这里的“亲父兄”不是一类。
(十)“弟兄”,兄也。同篇:“逼迫兼弟兄。”此处“弟兄”一词也是字复义奇。全诗不曾叙兰芝有弟,逼迫者只是阿兄。本句“兼”字是承上句“我有亲父母”来的,上句“父母”只指母,此句“弟兄”只指兄,“兼”是兼母与兄,不得因“兼”字认为兰芝有弟。黎劭西先生说:“今国语谓‘弟’曰‘兄弟’亦连言而成凝定的偏义,若欲称兄及弟则不得云‘兄弟’而必曰‘弟兄’,如云‘两弟兄’,谓兄弟两人也;云‘两兄弟’,则其两弟矣。”那么,这一词的用法古今又有小不同了。
(十一)“洒扫”,扫也。张衡《同声歌》:“洒扫清枕席。”这诗上文“莞蒻席”“匡床”“衾帱”等词都关涉到床榻,这句“洒扫”两字当然直连“枕席”。枕席只可扫,不可洒,“洒”字不应有义,不过借以足句而已。
(十二)“冠带”,冠也。曹操《薤露行》:“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上句用《史记·项羽本纪》“沐猴而冠”成语,加一“带”字是为了凑成五言。阮籍《咏怀诗》“被褐怀珠玉”用《老子》“被褐怀玉”,加一“珠”字,“珠玉”亦成偏义复词,引用成语,加字足句,因而构成的偏义复词是较普通的一种。
(十三)“西北”,北也。曹植《杂诗》:“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黄晦闻先生《曹子建诗注》说“织妇”喻织女星,并引《史记·天官书》说明织女星所在的方位是北方。本诗结句“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南”字与“北”字相应,“西”字无义。
(十四)“西北”,西也。阮籍《咏怀诗》第四:“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这两句诗本于汉郊祀歌“天马徕,从西极……经千里,循东道”。“北”字无义。这一类的偏义复词在诗歌里亦较常见,如古乐府“日出东南隅”之偏用“东”义,曹植“光景西南驰”之偏用“西”义等,不备举。
(十五)“存亡”,存也。阮籍《咏怀诗》第八十:“存亡有长短,慷慨将焉知。”这里“长短”指寿命(喻国祚);诗中“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是说长存不可指望,“不见季秋草,摧折在今时”是说夭折却在意中。一本“存亡”作“存日”,意义不变,但日字恐是后人不明复词偏义之例故意改的。注家也有人将“长短”解为“长短术”,似乎未得诗意。(刘盼遂先生所举也有“存亡,亡也”一条,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可参考。)(十六)“丝竹”,丝也。伪苏武诗:“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丝竹厉清响,慷慨有余哀。”《游子吟》本是琴曲,所以上句说“幸有弦歌曲”。下文“丝竹厉清响”,“竹”字自是因“丝”连言而及。
(十七)“弦望”,望也。伪李陵诗:“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此例黎劭西先生曾举过,他说:“日月,月也。日安得有弦望?”以“日月”为偏义复词固然可通,但“望”字本取日月相望之义,(《尚书》“惟二月既望”,孔安国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阮籍诗云:“日月正相望。”)假如这两句诗改作“安知非日月,相望自有时”,不也可通吗?那么问题岂不是只在“弦”字?所以也不妨说“弦望”是偏义复词。
以上十七条,是笔者平日读汉魏诗偶然注意、偶然札录的东西,相信如专意去搜寻一番,当有较多的发现。他日有暇,再来
补充。
1948 年夏
试读二:谈《西洲曲》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一作“黄”),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阑干头。阑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上面这首《西洲曲》,《乐府诗集》收在杂曲歌辞里,题为“古辞”。《玉台新咏》作江淹诗,但宋本不载。明清人的古诗选
本或题“晋辞”,或归之于梁武帝。这诗可能原是“街陌谣讴”,后经文人修饰,郭茂倩将它列于杂曲古辞,必有所据。郭书不曾注明这诗产生的时代,猜想可能和江淹、梁武帝同时。我们看《子夜》诸歌都不能这样流丽,《西洲曲》自然产生在后,说它是晋辞,似乎嫌太早些。至于产生的地域,该和清商曲的西曲歌相同,从温庭筠的《西洲曲》辞“西洲风色好,遥见武昌楼”两句可以推见。
这首诗表面看来是几首绝句连接而成,其实是两句一截。因为多用“接字”或“钩句”,产生一种特殊的节奏,因而有一种
特殊的姿致。《古诗归》说它“声情摇曳而纡回”,《古诗源》说它“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这是每个读者都能感到的。不过有些句子意义若断若连,诗中所云不能让人一目了然,读者来理解它,不免要用几分猜度,因之解释就有了纷歧。有人说这诗是若干短章的拼合,内容未必是完整统一的。这话我却不敢信,因为诗的起讫都提到“西洲”,中间也一再提到“西洲”,分明首尾可以贯串,全篇必然是一个整体,且必然道着一个与西洲有关的故事。
近来《申报》《文史副刊》有游国恩先生和叶玉华先生讨论《西洲曲》的文章,他们对这诗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
游先生说从开头到“海水摇空绿”句都是一个男子的口气,写他正在忆着梅(可能是女子的名或姓)而想到西洲(她的住处
在江南)去的时候,恰巧他的情人寄了一枝梅花到江北(他的住处)来,因而忆及她的仪容、家门、服饰、生活和心绪。末尾四句改作女子的口气,自道她的心事,希望“向南的风”将他的梦吹到西洲。
叶先生说全诗都是女子的口吻,她忆想的情郎居西洲,而西洲即在江北。她自己在江的南岸。她同她的情郎欢晤是在梅花季节,他离开她到西洲去了,不易会面;又到梅开的时候,她折梅请人寄交他。篇末是说她希望自己的梦云被南风吹向情郎的住处。
游、叶两先生所见恰恰相反,而各能自圆其说,这是很有趣的,教人想起“诗无达诂”那句老话来。
我对于这篇诗的了解和他们两位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现在也来妄谈一番。
一、说“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游、叶两先生都将第一句里的这个“下”字解作“思君不见下渝州”的“下”,因而兜了小小的圈子。叶先生把“忆”与“下”分属男女两方,游先生也把“忆”和“寄”分属男女两方,都是不得已,都是从“下”字的解释生出来的一点勉强。我以为这“下”字是“洞庭波兮木叶下”的“下”,就是落,它属梅不属人。西洲必是诗中男女共同纪念的地方,落梅时节必是他们共同纪念的时节。这两句诗是说一个女子忆起梅落西洲那一个可纪念的时节,便折一枝梅花寄给现居江北的情人,来唤起他相同的记忆。句中省略了主词,主词不是“我”而是“她”,这两句不是男子或女子自己的口气,而是作者或歌者叙述的口气。
也许有人要问这样解释时第一句岂不成了上一下四句法,会不会有害诗的音调呢?我说不会,这样的上一下四句念成上二下三还是很自然的。这种句法在乐府古诗里本属常见,例如《孔雀东南飞》篇“恐此事非奇”“还必相迎取”“因求假暂归”都是上一下四;曹操《蒿里行》“乃心在咸阳”,蔡琰《悲愤诗》“欲共讨不祥”也是上一下四,放在诗里读起来并不拗口。还有更适于拿来作比的句子,就是清商曲《那呵滩》的“闻欢下扬州”,它和“忆梅下西洲”句法完全相同,那也是南朝的民歌呀。
二、说“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曲》本是写“四季相思”,这话游先生也说了。诗中有些表明季节的句子,如“折梅寄江北”“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低头弄莲子”“仰首望飞鸿”和“卷帘天自高”都是一望而知的;另外还有几句,
表季节的意思不很显明,容易被忽略过去,像这“单衫”两句就是。
上文说这诗是两句一截,这一点和这两句诗的了解便有关系。假如把开头四句一气念下,便不知不觉地将后两句的意思过于紧密地连向上文,以为这是对寄梅人容貌服装的描写。但是着单衫的时候离寄梅的时候已经很远,梅是冬春的花,在长江附近最迟阴历二月就开完了,单衫却是春夏之交的服装。在同一句中从“杏子红”三字也见出季节,杏儿红熟的时候不正是春夏之交吗?不但这一句,下句的“鸦雏色”何尝不表明同一季节?鸦雏出世可不也正是春夏之交吗?所以这两句诗的作用不但是点明诗中的主角,而且表示自春徂夏的时节变迁。
三、说“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伯劳飞”三个字也表示时节的变迁。《礼记·月令》说“仲夏鵙始鸣”,鵙就是伯劳。
这一句表明时间进入五月了。下面写“采红莲”是六月,“南塘秋”是初秋,因为还有“莲花过人头”,“弄莲子”便到八月,“鸿飞满西洲”则是深秋景象了。全诗写时间是渐进的,假如没有“单衫”两句和“日暮伯劳飞”这一句,“折梅”和“采莲”
之间便隔开太远,和采莲以后的时序叙述就不相称了。
“日暮伯劳飞”的意义自然不仅是表时序。《古微书》说“博劳好单栖”,博劳也就是伯劳,那么岂不正可喻诗中主人的孤独?“日暮”是伯劳就栖的时间,下句说到树,树是伯劳栖息的地方,此树就在她的门前,由鸟及树,由树及门,由门及人,真是“相续相生”。这两句很容易被读者误认作闲句,事实上这首诗里并无闲句。
四、说“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上文说这诗写四季相思,其实也写日夜相思。“尽日阑干头”中“尽日”两字结束了白昼,一卷帘便又搭上了夜晚。为什么卷帘呢?自然因为“水晶帘外金波下”“开帘欲与嫦娥亲”。天高气清,乍一开帘分外觉得,也许正是“帘开最明夜”,纤云四卷,所以霜天如海。“海”,本来没有海;“水”,本不是真水,所以绿成了“空绿”。(说“空绿”是杜撰吗?民歌里就常有此类杜撰的好词。“海水摇空”可以连读却不必连读。)
但为什么会“摇”呢?谁曾见天摇过来?这就先要明白这两句是倒装,摇是帘摇,隔帘见天倒真像海水滉漾,那竹帘的绿自然也加入天海的绿,待帘一卷起,这滉漾之感也就消失了,只觉得天高了。但滉漾虽然不滉漾,像海还是像的,这海比真海还要“悠悠”,就拿它来比楼头思妇无穷无尽的相思梦罢。这时的景是“月明如练天如水”,这时的情呢,正是“碧海青天夜夜心”啊。
五、说“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先说“梦”,这个“梦”不必泥定作梦寐的梦,白日梦也是梦,上文说“忆梅”“忆郎”,“忆”就是梦。“低头弄莲子”是在梦着,“仰首望飞鸿”也是在梦着,“尽日阑干头”更是在梦着。西洲常在忆中,也就是
常在梦中。西洲的事“我”不能忘,“君”又何尝能忘?“我”为忆(梦)西洲而愁,“君”亦何尝不然?那么在忆(梦)西洲
的时候正是两情相通的时候,这忆(梦)虽苦,苦中也有甜在,整日的忆(梦),终年的忆(梦)不也很值得吗?然则南风是该
感谢的,常常吹送我的梦忆向西洲去的正是它呀。
篇末四句当然是女子的口气,这四句以上却不妨都作为第三者的叙述,(旧诗文直接、间接口气本不细分,但从“垂手明如玉”等句看来,作为第三者的叙述毕竟妥当些。)从第三者的叙述忽然变为诗中人物说话,在乐府诗中也是常见的。
最后,对于西洲在何处——江南还是江北——这一个问题试做解答:西洲固然不是诗中女子现在居住之地,也不是男子现在居住之地,它是另一个地方。西洲离江南岸并不远,既然两桨可渡,鸿飞可见,能说它远吗?“江北”可不见得近啊!要是近,就不会有这许多梦、许多愁,也就没有这首诗了。那么,西洲到底在哪儿?它不在江南是一定的了,难道也不在江北?是啊,它为什么不在江南就一定在江北呢?它何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江中的洲呢?
不过,这么说,倒好像在逃避问题,又好像有意在走游、叶两先生的“中间路线”了。
1948 年 5 月 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