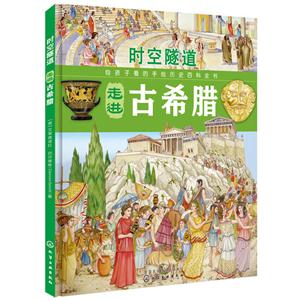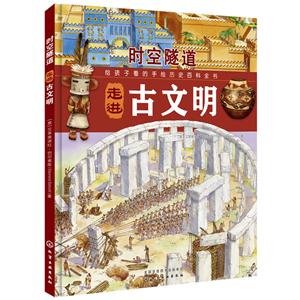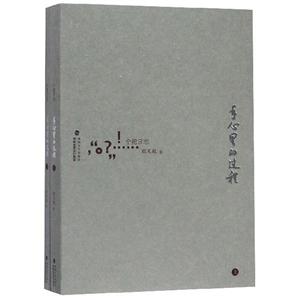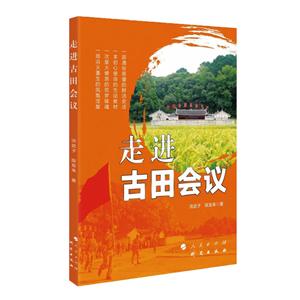作者:程章灿
页数:392
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536171404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作者强调,从事中国古典研究,是走进古典的过程。所谓 “过程”,一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的成长过程;二是指文献的生成过程;三是指文本的造作过程,即作品的题目、韵式、章句等形式结构及意义生成过程;四是指观念的锻造过程,即词汇、术语、意象等演变定型的过程。本书论文从不同角度涉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的成长过程,上篇大多聚焦各类文献的生成过程,中篇大多聚焦文本的造作过程,下篇侧重从词汇、术语、意象等角度窥探语言及观念的形成过程。
作者简介
程章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诗教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汉学、南京及江苏地方文献与文化等。出版学术著作有《魏晋南北朝赋史》《赋学论丛》《世族与六朝文学》《刘克庄年谱》《古刻新诠》《石刻刻工研究》等多种,另有国际汉学译著《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五种,学术随笔《鬼话连篇》《山围故国》《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传奇》等五种,发表论文、诗作多篇。
本书特色
本书一方面遥接文史结合与文史不分的传统治学思路,另一方面则试图结合书籍史、文化史以及文章学等研究视角。本书也有意呈现作者作为研究主体的成长过程,是对作者研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过程的阶段性回顾与总结。
目录
《诗集传》纂例举证
作为文本的汉代石刻
——读《汉代石刻集成》
宋刻《南岳稿》考论
文儒之戏与词翰之才
——《文房四友除授集》及其背后的文学政治
所谓《后村千家诗》考
一场同题竞赛的百年雅集
——读南海霍氏藏本罗聘《鬼趣图卷》题咏诗文
中篇
三十个角色与一个演员
——从《杂体诗三十首》看江淹诗歌的个性特色
题目与诗
——谢混《诫族子诗》及其诗史意义新论
读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并论南朝墓志文体格
重定时间标准与历史位置
——《新刻漏铭》新论
象阙与萧梁政权始建期的正统焦虑
——读陆倕《石阙铭》
五句体与连章诗
——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体式发微
下篇
郭象“碑论”“文论”考
文本与视野
——六朝文学研究的两点思考
树立的六朝
——柳树与一个经典文学意象的形成
从碑石、碑颂、碑传到碑文
——论汉唐之间碑文体演变之大趋势
论“碑文似赋”
后论赋绝句五十首
符祜考
——论割并年号及其相关的构词问题
尤物
——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古代石刻
程章灿主要学术著述
古典学术的现代化(代后记)
节选
万光治在其《汉赋通论》中曾专辟一章,讨论“汉代颂赞箴铭与赋同体异用”的问题,指出:“汉代是赋文学的时代,但汉代的赋又并不都是以赋名篇的。诸如颂、赞、箴、铭,因其较注重句式的整饬和用韵、换韵,不独可与赋同入韵文的范畴,而且大多数篇章文辞繁富,重在铺陈,与赋实为同体异用,这是汉文学研究中应予注意的问题。”①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虽然万光治在这里并没有提到碑文尤其是汉碑,但实际上,赋与碑文之间也存在这种“同体异用”的关系。如果从狭隘的文学观点来看,碑、赋二体似乎相去悬殊,二者没有多少联系,更没有什么共同性。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历史视野,那么,我们不难发现,碑、赋二体在体用方面其实有众多联系和类同。 首先是题材上的类同。碑文与赋,这两种文体在题材方面多有交集,尤其集中在写人、纪事、写地三大项。赋的题材,细分起来,有写人赋(如神女赋之类)、写事赋(如苑猎、征行之类)、写地赋(如京都、宫殿、堂宇赋之类)等等。而汉碑的主要题材,亦以人、事、地三者为大端。以写人而论,则或以生者为对象,赞颂其功业,如《刘熊碑》《耿勋碑》《韩仁铭》,或以死者为对象,缅怀其生前之勋德,如《曹全碑》《袁安碑》《北海相景君碑》《张平子碑》;以写事而论,则有《礼器碑》《石门颂》《李翕析里桥郙阁颂》等;以写地而论,则以山川宫庙为对象之碑文尤多,如《祀三公山碑》《华山庙碑》《封龙山颂》《仓颉庙碑》等。至于碑、赋二体不约而同地叙写相同的题材内容,更是不胜枚举。例如温泉一题,自东汉张衡开其先河,作《温泉赋》,其后西晋傅咸作《神泉赋》,北宋秦观作《汤泉赋》,元代王沂、清代彭孙通等人亦有《温泉赋》之作。①这些作品都是以赋体铺写温泉,一脉相承,勾画出赋体文学与温泉结缘的历史线索。而在碑文方面,则北周王褒、庾信并有《温汤碑》,唐太宗撰并书《温泉碑》,唐李幼卿撰《石门汤泉碑记》②,皆是以温泉为题,殊“体”而同归。从题材分类上看,温泉既可以划归写地赋之大类,亦可将其视为风物一类。从表面上看,碑体较少咏物的题材,而就赋体而言,咏物历来是其引人注目的核心题材。但实际上,像《温泉碑》这样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咏物的篇章。换句话说,碑、赋二体题材类同或重叠,并不限于写人、写事、写地三大类,在其他类别中亦时或可见。 我们也要承认,碑、赋二体题材重叠之处最多的,还是山川寺庙一类的题材。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名山大川和著名寺庙往往富有历史文化内涵,其中蕴涵的时空意义,适宜赋颂碑记之类的文体铺展发挥。例如西岳华山,汉碑有《西岳华山庙碑》,杨敬之、达奚珣皆有《华山赋》。表面上,碑以庙为题,赋以山为题,焦点不同,但实际上,华山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二者所共同叙写的侧重点之一,两篇作品内容重叠处甚多。 其次是风格上的类同。汉碑的文体风格,以颂为主。很多汉代碑文以颂为名,仅《隶释》一书所载,就有《司隶校尉杨君石门颂》《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稾长蔡湛颂》《成阳令唐扶颂》《王子香庙颂》等,这些题名表明此类碑文具有突出的颂体属性。另外一些碑文,虽然表面上不以“颂”为题,但作者在篇末铭词中,仍然明确称其所作为“颂”。如《东海庙碑》“遂作颂日……”(《隶释》卷二),《桐柏淮源庙碑》“民用作颂,其辞日……”(《隶释》卷二),《三公山碑》“乃作颂日:……”(《隶释》卷三),《无极山碑》“乃立碑铭德,颂山之神”(《隶释》卷三)。可见,这些碑文实质上也属于颂体。①众所周知,在汉代人的文体观念中,赋、颂二体本来即有一种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很多时候,赋、颂可以通称,并没有严格的分别。赋篇以颂为名,赋的主旨以“润色鸿业”的劝颂为主,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汉赋亦可以称为汉颂。②这使得汉赋与汉碑之间,在风格上有了天然的联系。在汉代各种文体中,碑、赋二体不仅以其数量与影响而占据文坛的中心位置,而且以其昭彰的文学性而格外引人注目。实际上,这两个有着类同的题材与风格的文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