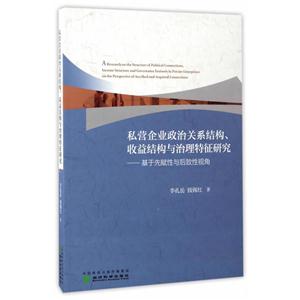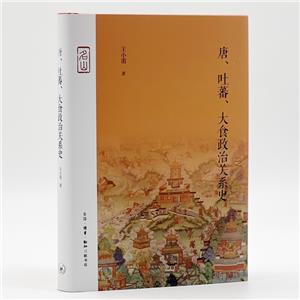
作者:王小甫
页数:368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108070890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中古史、中古民族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的代表性著作。初版于1992年,旋即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和好评。《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美国《中亚杂志》、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澳门日报》等先后发表了多篇书评。
全书主要阐述了公元七、八世纪唐、吐蕃、大食三大政治势力在中亚地区的角逐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诸如吐蕃向西域扩展势力及其与唐朝的争战、西突厥的兴衰、大食的东方扩张等。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汉、藏文书等手资料,并从阿拉伯文史籍中做了大量摘译,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推动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
作者简介
王小甫 男,四川成都人,1952年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9年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1999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导,2000年获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2012-2014年任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编委、《东方文化集成·中亚文化编》编委、《新疆通史》编委。2018年10月起被人民日报社聘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方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史、中国与周边关系史。代表专著有《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等,屡获国家教委、国家社科基金成果奖。编著教材《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国 开明开放》《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先后主持“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史研究”“3—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6—10世纪中国的族群凝聚与国家政治体制演进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
本书特色
在丝绸之路研究、中外关系研究日益隆盛的当下,如本书这种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目录
序一 季羡林
序二 张广达
引言
第一章 唐朝统治西域与吐蕃的介入
第一节 唐朝的西域统治
第二节 吐蕃的兴起
第三节 吐蕃最初进入西域之路
第四节 吐蕃在西域的早期活动
第二章 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
第一节 吐蕃与唐朝之反复争夺安西四镇
第二节 大食之介入西域
第三章 葱岭地区的政治角逐
第一节 长寿元年复四镇后的西域形势
第二节 吐蕃越葱岭进入西域之路
第三节 七、八世纪之交葱岭地区政治势力的消长
第四节 吐蕃借道小勃律攻四镇及其失败
第四章 唐、蕃西域较量的新发展
第一节 吐蕃从东道入西域
第二节 唐与大食共灭苏禄
第三节 唐朝势力在西域之臻于极盛
第五章 东争唐地、西抗大食的吐蕃帝国
第一节 安史乱后的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
第二节 “蕃军太半西御大食”说考辨
结语
附录
壹 “弓月”名义考
貳 弓月部落考
叁 崔融《拔四镇议》考实
肆 四镇都督府领州名称、地望略考
伍 古藏文Kog(Gog)yul 为俱位考
陆 金山道行军与碎叶隶北庭
柒 论古代游牧部族入侵农耕地区问题
附表
缩略语与参考文献
后记
地图
一 本书参考地区形势图
二 葱岭南部交通图
节选
总结本书研究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7世纪中叶到8世纪末叶是亚洲大陆上的强权政治时代。这一格局由于唐、吐蕃、大食三方在西域的政治扩张而呈现出阶段性(见本书《引言》);小国的向背依强权政治倾斜的方向和角度发生变化,但基本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不直接反映各强权间的关系。 2.吐蕃进入西域的道路主要有三条,它们是随着唐朝在西域经营的发展而先后被启用的。通过考证这一进程,使一些相关史实的年代得以参照确定。这一进程的发展,明显影响着西域政局的变化。然而,当吐蕃最终取代唐朝占领西域时,这里的强权政治时代也就结束了。 3.与相对稳定的强权政治不同,北部草原几易其主,操突厥语诸族基本上都是强权政治的附庸:唐朝要隔断二蕃,吐蕃力求连兵,大食则想根绝祸源,这些就构成了一种复杂的“三方四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无论和、战,突厥人均被阻隔在草原上。 通过本项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唐、吐蕃、大食关系史主要是政治史。唐朝方面,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最初只不过是保持边疆的稳定,后来又有了扩大版图的企图。”特别以掩护河西、陇右,进而保障长安之安全为然。无论是当时人的议论,还是唐朝在经营过程中巨大的人力、物力耗费,都可以用来证明这个观点。不是唐朝为攫取丝路利益而经营西域,而是丝路贸易在唐朝经营西域的活动中,由于巨额军资练的转输、使用而更加发达。 吐蕃方面也同唐朝相似,其经营西域的动机和目的已在万岁通天二年(697)论钦陵与郭元振的野狐河会谈中表露得很清楚了。白桂思说吐蕃人深入吐火罗是为了保持“商路畅通”〔1〕,这既不符合吐蕃社会农、牧兼营的情况,也不符合吐蕃向外经营活动的实际。这些,单从吐蕃入西域道路的变化情况中也可以看出来。 大食后来也许攫取到了商业利益。但在对外扩张的初期,大食人的征服活动既非为了经济利益,也不是为了“圣战”,而主要是为了在内战平息后“给各部族的好战精神找出路”。 其实,最希望控制商道贸易的是草原上游牧的突厥人〔3〕,只是他们当时还力不从心,所以这时期商业族群(如粟特人)的活动也特别活跃。国外有的学者喜欢从经济角度分析历史问题,大概与他们在殖民时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关,其实未必都中肯。 2.吐蕃向西域的积极发展表明,藏民族从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就主要是同祖国大家庭其他各族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内活动,并且通过同唐朝及西域诸族的一系列和战联系,共同创造了祖国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吐蕃在经营西域过程中,也把势力扩展到了葱岭山区和恒河岸边。通过这些活动,刚刚形成统一的藏民族为青藏高原的开发和祖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这些活动奠定了历史上藏族分布的范围,这些地域至元代大都进入了祖国统一的版图。实际上,只是到了近代,才被殖民主义者用武力与欺骗手段强行改变了中外政治边界。 3.唐朝和大食分别领有葱岭东、西,他们同突厥人的斗争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具有新旧之争的性质。然而,回鹘西迁(840)以后,连突厥人自己也逐步接受了伊斯兰教。中亚的伊斯兰化实际上是指突厥人的伊斯兰化,因此,它必须以中亚的突厥化为前提。这在突厥人不能大规模进入绿洲、进而转向农耕定居的时代是根本办不到的。尽管有的突厥人可能在草原上就接受了伊斯兰教,但那同中亚的许多伊兰人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一样,只是运动的先声。所以,只有在西域的强权政治时代结束以后,中亚才有可能变成本来意义上的“突厥斯坦”——操突厥语诸族群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