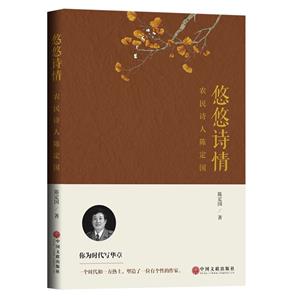
作者:陈定国
页数:272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ISBN:9787519046729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纪年体传记,从1953年7月至2018年7月,按时间顺序,以自述文逐条论述,图、文并存,以图为主,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在业余创作上走过的一路风景。
本书特色
本书作者执着于传承乡土文化,从事业余创作已60余年,并获得多个奖项和荣誉,他的作品里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及一直以奋斗者的姿态为诗乡奉献余热的孜孜不倦之精神,可提供给广大的创作爱好者鼓舞和启迪
目录
001 秀才逢生
005 我的童年
021 八形汊的故事
031 回家真好
038 四年才走上第一个台阶
044 热出一个高温天气
055 我在北京唱山歌
062 扬帆的诗船
078 婚事风波
095 她的爱在延续
104 诗乡,你长大了
113 登上文化大舞台
144 写好人生这部书的“后记”
244 代跋 陈定国:打捞洞庭民歌
250 采访手记 向坚守者致敬
251 后记
节选
秀才逢生
太阳从洞庭湖边升起,一道道红光洒在水面上、大堤上、杨柳上、芦苇上,大地显得格外燠热。
这是 1936 年 9 月 23 日,农历丙子年七月初七辰时,我出生于沅江白沙洲。
母亲临产的那一时刻,父亲在堂屋里坐立不安,有时叭几口旱烟,有时在屋里转来转去,有时心不在焉地随手翻看那本翻烂了的《三国演义》,但心里是十五只水桶提水,七上八下。 “哇”的一声,房里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
在我家接生的高大妈三脚两步跨出房门,笑嘻嘻来到我父亲面前,兴奋地说:“恭贺先生,添个男喜!”
父亲听说生个男孩,脸上流露出无限的喜悦,丢掉手里的旱烟袋,喜冲冲地跨进房门,只见我母亲躺在床上,头偏向门外,那苍白的脸上浮现了安详的笑容。父亲笑着说:“婆婆子,辛苦哒,辛苦哒啊!”
父亲走近看了看我,虎头虎脑的伢儿模样,喜得就像石磨一样地旋转起来,从里屋转到堂屋,情不自禁地哼起南宋诗人叶绍翁的诗句: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海公先生,什么事这样高兴?”
父亲抬头一看,正是方恕庵先生。
方恕庵又名方槦,清朝光绪末期拔贡,很有名望,白沙洲的第一个文人,善诗词,爱书法,有“方秀才”之称。
父亲也精通文理,喜欢舞文弄墨。两人常在一起吟诗作赋,谈今论古,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演义》《西游记》。他们还悄悄听过县里的地下党员的讲演,心情开朗起来,常和穷朋友在一起讲红色故事,传红色歌谣。穷朋友说他们是开明人士,他们说穷朋友是知心朋友。
今天,父亲洋洋得意,当着方秀才的面随口而出:
“看今日喜添贵子。”
“恭喜,恭喜。”方秀才忙忙拱手道喜,高兴地对下句:
“望未来光耀华堂。”
二人哈哈大笑。
“小少爷的大号是……”方秀才问。
“你来得正好,请取个名字。”父亲十分尊重他。
“好,我想想。”他在堂屋里坐下来,接过张大妈端上来的热茶,慢条斯理地品起来。 这时,我突然在房里几声啼哭,连小湖那边都能听见,惊飞了门外大树上的喜鹊。
“好家伙,有底气!”方秀才不觉喃喃自语,“孩儿今后必有出息,我看,就叫定国吧。” 父亲连连点头:“好,好。”
父亲摸出一壶米酒,一碟子炒豌豆,与方秀才对酒畅谈。谈着谈着,谈起了自己的即兴创作。
父亲抿口米酒,兴致勃勃地吟了起来:
洞庭月色醉蓝天,
报晓金鸡啼在先。
气概昂扬天下白,
安邦定国梦圆圆。
方秀才也抿一口米酒,应和起来:
定有蛟龙雪浪游,
国中喜气遍河洲。
苗苗迎着春风长,
喜望曙光照彩楼。
他们二人都是将我的名字“定国”嵌入诗中,只是方秀才的更加高明,吟的是藏头诗。父亲连忙打拱手,斟上满满一杯酒,敬给方秀才,说道:“方兄,佩服,佩服。”
“干!”方秀才一饮而尽。
这时,高大妈走了出来,与我父亲讲了几句耳语,父亲连忙把方秀才请到里屋。
“看看细伢子,看看。”高大妈用红格子被单紧紧包着我,抱起来,站到父亲和方秀才面前。
我父亲满脸笑容,非常得意地在我那粉嘟嘟的脸上轻轻吻一下。他那胡渣像锯齿一样,刺得我哭了。
方秀才赶忙在我身上轻轻地拍了两下,笑着说:“啊,好孩子,别哭,别哭。”
我真的不哭了。
高大妈把我抱到母亲怀里。母亲笑着向方秀才轻轻挥手:“请坐请坐,秀才进屋,全家得富。”
高大妈喜得拿一根穿了红线的缝衣针,别到方秀才的左臂衣袖上。
方秀才晓得,谁家生了小孩,第一个进门的外人就是“逢生”,男的称“逢生爹”,女的称“逢生娘”,年轻人就称“逢生哥哥”或者“逢生姐姐”。不管是谁逢生,主人必须在逢生人的衣袖上穿红线针。这是湖乡人的风俗习惯,表示对逢生人的一种喜爱与尊重,而逢生人则得到喜悦与荣耀。
接着,高大妈又给方秀才送来一碗糖水鸡蛋茶。方秀才接过碗,轻轻地抿了一口糖水。
方秀才临走时,慢慢地取下红线针,放在《三国演义》这本书上。按传统风俗,红线针应插在门前树上,暗示小孩四季常青,长命百岁。而他把红线针放在书上,自语:“腹有诗书气自华!”
父亲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那时,我家是掰着手指过日子,很穷。方秀才家里好得吹油不开,很富有,常常周济我家一些钱米。在我“三朝”那天,他以逢生爹的身份,特意送来厚礼:白米六斗、猪肉六斤、黑鸡六只、红枣六斤、黄花六斤、鸡蛋六十双,银圆六十块。还用红腊光纸写了一副对联,那就是我出生那天他和我父亲的即兴创作:
看今日喜添贵子;
望未来光耀华堂。
我的童年
难忘我的童年,第一个小镜头:躲日本
1943 年 3 月,我快七岁了。
值插秧时节,沅江来了日本鬼子,父老乡亲吓得要命,拖儿带女往外逃。我母亲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提一蓝布袋子衣服,我父亲背上挎床用绳索捆紧的白土布棉被,也外出逃难。好像日本鬼子从后面追来了,没有目的地舍命往前跑,到了桃江鸬鹚渡、安化马迹塘,寄居在山里人家。我母亲藏在衣角里的一块银圆也用完了,只得逼着往回走,走到沅江台公塘的一个亲戚家里住下来,白天躲在竹山里。
这一天,有人从南县厂窖那边来,说起了日本鬼子血洗厂窖的事。那天天气由晴转阴,非常闷热,后来慢慢地刮起了西北风,人们才喘了一口气。路上走来一位挑担秧夹子的年轻大汉子,突然望见一里路外的大堤上开来—路长长的队伍。队伍走近了,他就看见一面太阳膏药旗。他急忙甩下秧夹子,掉头回跑,双手乱舞,大声喊:“日本鬼子来了 ! 日本鬼子来了 !”
顷刻,好似洪水冲垮了大堤,人们喊的喊、哭的哭、躲的躲、跑的跑,一下子整个村子人心惶惶。那位年轻大汉拉着年迈的父亲,肩背两皮木桨,第一个跑到河边,划船逃命。不一阵子,成群集队的村民也赶到河边,上了大小不同的船只,都想躲到对岸的芦苇荡里去。哪知一艘日军汽艇迎面而来,“叭叭叭”,一阵密如雨点的子弹朝船扫射,木划子打得嘣嘣响,水上击起点点浪花。船上的村民无处藏身,只能往舱里爬,往河里跳。汽船逼近,枪声更紧,杀得血水成河,尸沉水底。那位年轻大汉的父亲中弹身亡,他含泪从船边跳到河里,顺手捞块浮在水面的船板,掩盖头部,潜水爬上岸来,伏在河滩上一个长满了野草的土凼里,才逃过一劫。大堤边那些拖儿带崽、痛哭流泪的村民在舍命奔跑,一个嫂子踉踉跄跄跪倒在地,膝盖流血,她看也不看一眼,摸也不摸一下,爬起来又跑。大家跑着跑着,遇上躲在一边的几个鬼子,一阵机枪横扫,顿时血染河堤,尸首满地。这时,“嗡嗡嗡”一阵响声,两架日本飞机飞过来,低空盘旋,扔下颗颗炸弹。村里浓烟滚滚,一间间民房大火冲天,一处处尸首堆积如柴……
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事,但日本鬼子的恶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阴影。我并没有看到过日本鬼子,但听到许多关于他们烧杀掳抢的事,还有我家在惊恐中度日的经历,深深记在我的心里。
谁不痛恨日本鬼子,只愿那班强盗早些发瘟。我父亲想了一副抗日楹联:
双拳推动海岛;
一脚踏平西山。
我不懂海岛、西山是什么意思,父亲告诉我,都是指日本鬼子。
我们全家躲兵回来不久,方秀才病故了。
听说他在临终前嘱咐家里人三件事:一是葬礼从简、薄葬;二是家里的全部资产给张家塞的穷人(他的岳父家在益阳县张家塞);三是所有田土无偿佃给白沙洲的穷人。他仅留给后人的是他生前写的四十一本日记和四大册诗词歌赋。
这天,云雾迷茫。我跟随父亲母亲到了方秀才坟地,肃立在瑟瑟的秋风里,心随着被湖风掠过的柳条而抖动。母亲望着那三尺高的细石墓碑,放了一挂千子鞭,烧了一叠钱纸。父亲站在墓碑前,深深鞠一躬,嘶哑着嗓子念着悼念方秀才的挽联:
落笔生辉传天下;为民献业贯古今。
我拱手作揖,弯腰鞠躬。心里念着:逢生爹爹,你不能再来看我了啊!
第二个小镜头:读私塾
我长到八岁,在大伯家读私塾。
大伯叫陈德福,是白沙洲有名的开明老教书先生,面相富态,一脸笑容,穿件青布长袍子,戴副老花眼镜。学堂设在大伯家里堂屋,课桌凳子都是学生从自己家里搬来的。
每天上午九点上学,下午四点放学,启蒙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每上一节课先由先生教,后是学生读,再是先生点,学生背。每次大伯点书后,满屋八九个学生,作鼓正经地坐在位子上一声一声地读,唯有我不声不响地看。
“你何解不读?”大伯走到桌边问我。
我冒冒失失地反问大伯:“你老人家何解见我没读?”
“你明明没开口读书呀。”大伯不高兴,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在心里读咧。”
“好,我来点书考考你。”
“你老人家不要点。”
“先生不点书,那是一只猪。”大伯生气了。
“大伯,你点的书我背得。”
大伯马上点书,他点上句,我背下句;他点一段,我背一段;他点一页,我背一页。每字、每句、每段、每页背得“一溜之烟”。我由此深得大伯喜爱,他说:“定国,看不出,看不出,你不要我劳神哩。”
一天中午,我大伯外出喝喜酒,就吩咐我带着同学读书,并向同学们宣布由我点书。
我有模有样地点书,大家都背得。我一看时间还早,就雷急火急地带立伢子和几个同学,翻过大堤,在堤外河滩的杨树上掰枯丫枝,只有一餐饭久,每人掰一捆,背到大伯的灶屋里,码起了一大堆。
大伯回来了,灌得脸红红的,额头上暴起一条条青筋,像蚯蚓一样。他见到灶屋里的柴禾很生气,绷着脸,瞪着眼,醉言醉语地冲着我问:“谁要你们去掰树上的枯丫枝?”
我毫不隐瞒地说:“是我要他们去的。”
“这是闯祸!”
“不是闯祸,掰掉枯丫枝,是为树整枝,让树更好地发育成长。”
“何解把树丫枝搬到我屋里来?真淘气!”
“你天天为同学们热中饭、烧茶,这不要用柴呀?我们是为自己捡柴哩。”
“讲得头头是道!这明明是为我捡柴呐。”
大伯想起昨天在课堂上的那个考题:家里养的鱼被猫吃了,这怪谁?同学们都说怪猫,我有不同看法,猫是爱吃鱼的,主人应该做好防备。
想到这里,大伯郑重宣布:“今朝我没防备你们去捡柴,教不严,师之惰,我有责任。” “我的责任。你外出了,我就是主人。”
“定国,你不要讲了,贪财是万恶之根”,大伯理直气壮地说,“先处罚我。减少每人一毛钱学费,等于向你们买了这些烧柴。”
我说:“不行,先生要罚学生才是。”
“当然要罚你们的。”大伯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接着提出,“罚你们对对子。谁要是对不上,用竹板打屁股。”
“莫打同学们,要打就打我!”
“定国,你真是好汉做事好汉当。那我先‘罚’你,你听题:
“春风。”
“细雨。”
“春天。”
“夏季。”
“正气。”
“春光。”
“万里。”
“千年。”
“日照。”
“风传。”
“书声。”
“妙语。”
“爬雪山。”
“撒火种。”
“枝枝绿竹生新笋——”
“……”我卡住了。
“你怎么对不上了?”
“大伯,我还没学七字对。”
“二字、四字、七字、十字,更多的字都是按词按字按声韵平仄相对的对法。”
“好,请大伯再念题。”
“枝枝绿竹生新笋。枝枝对什么?绿竹又对什么?”
我真是——和尚失了腊肉,开不得口。
大伯见我答不出来,就动手拿起竹板,在我眼前一闪一闪的。
“我来对。”立伢子插话,“捆捆……”
“不要你插嘴!”大伯用竹板指着他,又用竹板指着我,“你对不上呀。”大伯见我是第一次对长对子,就启发我:“你看看菜园里。”
我抬头看见菜园里那棵梅树,计上心来,我脑子灵活,来得快,想了一想答道:“朵朵红梅报早春。”
大伯的目光盯着我,点头微笑,但他故意问那几个没去捡柴的同学:“该不该打他的屁股?”
满堂同学从座位上站起来回答:“他的对子对得好,不该打他!”
我爱读书。每天从私塾回家,除了在家里劳动和帮三伯看牛外就是看书。有天下午放牛,我坐在堤边草地上,捧起一本书看起来,一下子入迷了,忘记看住牛,结果牛跑到李家妈的菜土里吃掉六蔸大白菜。我赶快把牛赶回草坪,打算回家后,再去向李家妈赔礼。哪晓得,李家妈到园里摘菜,发现了牛脚印,生气地喊:“这是哪个看牛伢子不看好牛啦。”
我闯的祸,不能瞒她,也不能推在别人身上,连忙走上去认错,把衣袋里仅有的一分钱拿出来,补偿损失。她横竖不肯要,扑哧一下笑了:“没事,没事,你是在读书呀,几蔸白菜算么子呢?”
立伢子从那边青草坪看牛赶过来了,约我明天放学后,在青草坪看牛对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