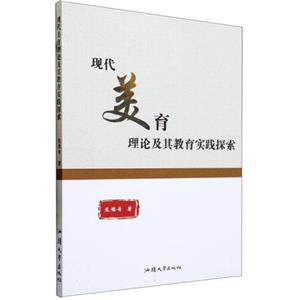作者:张永明
页数:240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ISBN:978710405109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在20世纪的美国剧坛,可以与田纳西齐名的戏剧大师,当数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他是继奥尼尔之后,美国当代著名的剧作家,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阿瑟·密勒191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在密勒中学时期,遍及全美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大萧条使得这个犹太商人家庭不幸破产。密勒的大学生活是在密歇根大学度过的,主修新闻和英文。这一时期他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一边创作剧本。密勒在美国剧坛乃至世界剧坛初露锋芒是在30岁之后,1947-1949年,他的成名作《都是我儿子》和具影响力的作品《推销员之死》在美国火热上演,并得到一致好评,最终囊括了托尼奖、普利策奖和纽约剧评界奖。除此之外,密勒的作品还有《萨勒姆的女巫》《桥头眺望》《美国时钟》《堕落之后》等,其中《堕落之后》被视为密勒的自传性剧本,涉及他与好莱坞著名演员玛丽莲·梦露失败的婚姻。密勒与中国戏剧的关系较为密切,曾于1978年和1983年两度访华,并先后写下了《访问中国》和《“推销员”在北京》两部作品,而他的剧作《萨勒姆的女巫》和《推销员之死》也都在中国成功上演。
作者简介
张永明,戏剧美学博士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编剧协会会员 河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教师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博士,师从中国戏剧美学奠基人谭霈生教授。 参与主持多个国家艺术基金、省部级重点项目等。主要从事影视剧创作,还有戏剧美学、中国戏曲、中外音乐剧、中外戏剧经典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中国戏剧》《戏剧文学》《中国文艺评论》《艺术学研究》《艺术评论》《中国艺术时空》《传记文学》《当代戏剧》《北京文史》《曲艺》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并在《人民日报》《中国艺术报》《北京青年报》、新华网等媒体上发表文章十余篇。 影视剧(编剧):《茧镇奇缘》《爱情万万岁》等导演舞台剧:《长椅》《兄弟》《恋爱的犀牛》等
目录
第一节 国内外对于密勒的研究概况及评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三、一个简单的评述
第二节 一个新的切入点:阿瑟·密勒与中国戏剧的关系
上篇
第一章 关于中国的“问题剧”
第一节 中国戏剧倡导“问题剧”的原初动机
第二节 为”问题剧“正本清源”
第三节 新时期中国戏剧创作的趋势
一从问题剧向社会剧的转变
第二章 阿瑟·密勒关于社会剧的主张
第一节 密勒心目中的“易卜生”
第二节 倡导严肃戏剧
第三节 悲剧的主人公是普通人
第四节 戏剧要有“社会性”
第五节 倡导新型社会剧
中篇
第一章 《都是我儿子》(以下简称“《都》”)
第一节 家庭和社会——《都》剧中的父子关系
第二节 引入讨论,使得情节戏剧化
第三节 从第三幕看《都》剧创作的得与失
第二章 《推销员之死》
第一节 《推销员之死》:阿瑟·密勒的改变及其评价
第二节 戏剧情境的构成
一、环境
二、事件
三、关系
第三章 《萨勒姆的女巫》《桥头眺望》和《回忆两个星期一》
第一节 关于几部剧中的“社会问题”的探讨
一、《萨勒姆女巫》和“麦肯锡主义”
二、《桥头眺望》和“美籍意大利移民”问题
三、《回忆两个星期一》:赤裸裸的现实和心中压抑不住的欲望
……
下篇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节选
《阿瑟·密勒关于社会剧的理论及其多方位的探索》: 《萨勒姆的女巫》(以下简称“《萨》”)是密勒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的戏剧作品中上演次数最多的剧目之一。让很多观众和评论家不解的是,密勒完全可以按照《推销员之死》(以下简称“《推》”)成功的路子,继续创作和《推》同类型的剧本。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另辟蹊径,决心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创作。他“希望找到写出一部尖锐剧本的方式,这样的剧本要从主观主义的陷阱中把那令人辗转不安的、单一的、规定好的过程拉出来,以显现它造成公众恐怖的罪行,是它在剥夺人的良心,剥夺人的自主权。这个主题与前几部剧本的主旨不无关联”①。 《萨》这个剧本以独特的视角、特殊的事件以及和当时政治的特殊关系,常常被认为是密勒借以对抗当局对其采取不公正“待遇”的一部作品。故事的背景是美国马萨诸塞州萨拉姆镇1692年发生的一场惨案,剧本根据真实历史改编,剧中主要人物的原型,也都是在当时的文件中有记载的。故事围绕主人公普洛克托展开,这个35岁上下的庄稼人给人的感觉是“沉稳而富有信心”,当他从喧闹的人群中走来的时候,身上“隐藏着一股尚未发挥出来的力量”仿佛是这个布满“女巫”疑云的小镇的一股坚定的力量。 因为几个女孩子深夜在树林中围绕着一口大锅跳舞,之后其中的一个小孩子——当地牧师巴里斯的女儿贝蒂昏迷不醒。这原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却被别有用心的地主普特南夫妇搞得沸沸扬扬,造成了“小镇上隐藏着歹毒的‘女巫’”这一风言风语盛传的混乱局面。普洛克托作为全剧中心人物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他的现任女仆玛丽·沃伦是那晚在树林里面跳舞念咒的当事人之一,这无疑给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麻烦,使得他无法置身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剧作家给他安排了一段不能回避的“旧事”——整个“女巫”事件中最主要的煽动者阿碧格,曾经是他的女佣人,且与他有过奸情,这也直接导致了普洛克托的妻子辞退了阿碧格,并且减少了去教堂的次数,理由是“不想和那个脏东西坐在一起祷告”。这也为后面妻子伊丽莎白被指控埋下了伏笔,成为普洛克托无法面对的旧疾。 不同于《推》剧中老年的威利·洛曼因为疲于应对高强度的工作以及面对两个不成器的儿子的内疚所形成的经常喃喃自语的状态,普洛克托所面对的是更为复杂和严峻的现实。在塑造普洛克托这个人物的时候,一方面,作者要将其放置在错综复杂的事件纠葛中去;另一方面,还不能不兼顾他的个性化的塑造。然而纵观整个剧本,在《萨》剧中,阿瑟·密勒似乎并没有做得很好,正如他自己谈的“在《萨勒姆的女巫》中还试图超越那发现并揭露主人公的内疚的境界,这种内疚扼杀了个性。在我过去的作品里,我对这个主题的感受日益深切,并且也意识到像过去那样把剧本的基础仅仅建立在揭示内疚上以及使剧本完全依仗在一种向应受惩罚的人索取代价的命运上是不够的”①。通过上述的话我们也可以感知到,阿瑟·密勒并不满足于依靠这种“内疚”来揭示应该受惩罚的人物的命运,而是将全部的笔力集中在主人公的心灵最深处的隐痛的展示上。 剧本一开始,小镇的人们都深信牧师巴里斯的女儿贝蒂的昏迷不醒与“女巫”的迫害有关时,这位一向以正直和坚定而著称的硬汉并没有将这些看得很重要,而是认为这仅仅是几个小孩子的“小把戏”而已,所以他面对整个事件,表现很“轻松”的态度,这从他第一次和阿碧格在巴里斯主教的家里见面时候的状态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他面对含情脉脉的阿碧格,尽管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是还是似乎带有一种成年男性对心爱女孩的一种特有的“默契”在里面。这种大意的态度一直延续到第二幕的开始才发生了改变,只是当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为时已晚。 第二幕是以一种类似于契诃夫式的日常的、琐碎的笔触来开始的。幕启的时候,普洛克托外出干农活刚刚回到家。尽管夫妻两个都是带着一种表面平静的语气在对话,但是细心的观众不难看出,两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终于,在谈到萨勒姆镇的这场灾难时,普洛克托漫不经心的态度引起了妻子的爆发,她终于将矛头对准了普洛克托最隐蔽的伤口,直接指出,为了事态不至于进一步发展成无法回避的悲剧,他应去法庭“揭露那个婊子”的真面目。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普洛克托猝不及防,他陷入了犹豫之中,而正是这种犹豫进一步激怒了妻子,让她将整个事实揭露出来。但是现在这个时刻似乎有点晚了,警长带着人已经到了他家,要带走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理由是妻子遭到了阿碧格的指控,说她使用巫术来陷害她。尽管怀着很大的愤怒,但是普洛克托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带走,同时带走的还有在村里一向有着良好声誉的善良的老奶奶吕蓓卡,以及詹理斯的妻子。眼看着眼前这场闹剧一步步演变成更大的悲剧,普洛克托的内心五味杂陈,他终于决定要站出来,用自己的正义来制止这场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