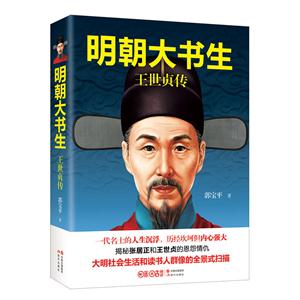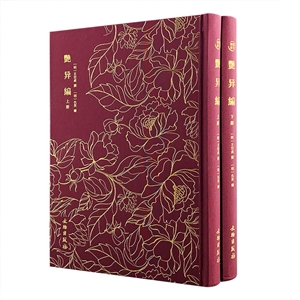作者:孙卫国
页数:428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ISBN:9787220121548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中国历目前多元学术佼佼者王世贞,在私人修史之风大盛的明代,他的史学思想为何独树一帜?他的史学实践为何宏愿难成?他的史学影响为何影响至今?本书以王世贞的仕途生涯与治史历程为考察线索,系统介绍了王世贞的史学理论、史学实践和史学成就,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爬梳王世贞所有著述的相关材料,客观公允地评价了王世贞的史学地位和史学影响,进而揭示出传统史学在传统社会末期的发展轨迹与困境。《王世贞史学研究》(修订版)研究了王世贞史学的诸方面:论述了王世贞的时代背景和他的仕途生涯,王世贞与当时诸首辅的关系是否影响他的史学著述历来有不同看法,作者正是通过探讨王世贞的仕途生涯,在有关章节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系统介绍了王世贞的史学理论,包括他的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理论和史学批评思想;探讨了王世贞的史学实践,包括他的明代史学批评与考证、明史著述与研究;论述了王世贞史学的影响,包括对明清史家以及对朝鲜的影响。
作者简介
孙卫国,湖南衡东人。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所和历史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并获得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8)、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朝鲜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自1994年以来,多次赴韩、日进修语言和访问研究。2001年7月到2002年元月,为韩国高丽大学客座研究员。2005年9月至2006年7月,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明清史,明清中朝关系史与海外中国学,在海内外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明代史学研究者和文史研究者和跨学科研究者和当代史名著的读者中国历史上多元学术佼佼者王世贞
在私人修史之风大盛的明代
他的史学思想为何独树一帜?
他的史学实践为何宏愿难成?
他的史学影响为何影响至今? 本书以王世贞的仕途生涯与治史历程为考察线索
系统介绍了王世贞的史学理论、史学实践和史学成就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爬梳王世贞最有著述的相关材料
客观公允地评价了王世贞的史学地位和史学影响
进而最示出传统史学在传统社会末期的发展轨迹与困境
目录
一、王世贞年谱
二、研究王世贞史学的论著
三、研究王世贞的博士与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王世贞生活的时代与生平
第一节 王世贞生活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王世贞的生平与仕途生涯
一、王世贞与严嵩
二、王世贞与张居正
第二章 王世贞的史学理论
第一节 王世贞的史学思想
一、经史关系的探讨
二、历史是连续发展的
三、迥异于时的正统观
四、审时度势的人物评价标准
第二节 王世贞之历史编撰学理论与史学批评思想
一、史书重因循模拟
二、对史书体裁与范畴的意见
三、史书三分法与官私修撰
四、王世贞对中国历代史书的批评
第三章 王世贞之明代史学批评与考证
第一节 王世贞从事史学批评与考证的原因
一、学风之转变与时代的影响
二、王世贞朋友之间的影响
三、明代史书之状况与王世贞的心志
第二节 王世贞对明代诸史之批评与辨正
一、对明代“国史”之批评与辨正
二、对明代“野史”之批评与辨正
三、对“家乘”之批评与考订
第三节 王世贞史学考证的原则与方法
一、国史、野史、家乘参互比证
二、重视撰者心术与作史动机
三、比附前史者皆证其误
四、疑以存疑
第四节 《史乘考误》以外之考证
一、《弇山堂别集》中之诸《考》
二、《四部稿》及他书之考证
第五节 王世贞考证史学之评价
第四章 王世贞的明史著述与明史研究
第一节 王世贞的明史著述
一、王世贞明史著述的四大类别
二、《弁山堂别集》及其对《史记》的模拟
三、《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之内容与体例特点
四、王世贞计划中的明史与《弇州史料》
第二节 王世贞的明史研究
一、对明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二、对宦官专权与宗藩膨胀问题的探讨
三、对明代政治与党争的研究
四、边疆问题的探讨
五、新掌故史料
第三节 王世贞明史研究的特点
第五章 王世贞明史学的影响
第一节 王世贞明史学对明清史家的影响
一、张萱与王世贞
二、沈德符与王世贞
三、谈迁与王世贞
四、钱谦益与王世贞
第二节 王世贞明史学对清官修《明史》与朝鲜的影响
一、清官修《明史》与王世贞
二、王世贞对朝鲜王朝的影响
附录一 王世贞著作目录表
附录二 征引与参考文献目录
一、中文目录
二、外文目录
后记
修订版后记
节选
一、王世贞与严嵩
王世贞与严嵩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围绕他们二人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对王忬之死严嵩应负何种责任;二是严嵩被列入《明史·奸臣传》与王世贞是否有关。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略论之如次。
王世贞举进士后,却不谒馆试,因为“耻从柄臣道地”。当时其父王忬告诫他:“士重始进,即名位当自致,毋濡迹权路。”王世贞牢记父亲教诲,入仕以后,对权贵始终敬而远之,对文人社团却极为热心。王世贞重视作为文人的身份,而作为文人重视自我的追求与个人价值身份的肯定,这种肯定不是官场的职位,而是在文人社团中的地位。而这种社团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初入仕途的王世贞不是谋求高官厚职,而是充分展示文人的本色,广交天下文士。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王世贞以进士入大理院,次年为刑部郎,即参加京师王宗沐等人组织的诗社。不久,授刑部主事。嘉靖二十八年(1549),与李攀龙交往,从此诗文唱和无虚日。王世贞诗文皆好,在文人社团中声名鹊起。王世贞自言:
余为郎燕京时,颇得游诸名隽间,而诸名隽独盛于庚戌(1550,时王世贞二十五岁,中进士三年)之对公车者。若吴兴徐子与(中行)、武昌吴明卿(国伦)、广陵宗子相(臣)、南海梁公实(有誉),以气谊相激昂还往,至穷昕夕亡间。未几而豫章余德甫(曰德)、铜梁张肖甫(佳胤)、郢上高伯宗(岱)、吾郡徐子言(诗)亦阑入焉,相与修觞酒觚翰之政。
王世贞与这些新科进士,吟诗作文,间亦臧否时政,但实质上只是文人之间的活动。陈继儒称之“以刑曹郎与李于麟诸子日相唱和,名夺公卿间”。《明史》称:“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唱和,绍述何、李,名益日盛。”在文人社团中,诸新科进士意气风发,毫不掩饰,“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年轻气盛,既觉得当时无人,亦不以权贵为意,自然也就容易得罪他们。而王世贞相当自负,随着文坛上声名日盛,士人间互相激宕,有议论之曰:“都人士聚而叹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公益自负,强项如故,而又性不能曲事权贵人,往往肮脏守法。”可见,一开始,王世贞就热心文人社团活动,对于权贵不肯曲意奉承,在政治与文化双重专制的明代,注定王世贞仕途的坎坷与不平。王世贞对自己仕途的坎坷有深切的体会,道:
然余往者则已有一时名,既名日以削,而宦日以薄,守尚书郎满九岁仅得迁为按察,治青齐兵,此其意将困余以所不习故。於乎!即令余未见嫉,司命削其官,与田父、猎徒角寸阴于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御魑魅、咏山鬼,亦有以自乐也,乌在其为困哉!
自古文人的秉性即有不事权贵的风范,王世贞以文人而自负, 因而引起权贵嫉恨,使得他仕途上陷于困境,无法施展才干,王世贞也就只得自我解嘲了。王世贞首先是一个文人,而他在随后的岁月里,又多年担当文人领袖,文人的身份注定了他仕途的坎坷。对权贵不依附、不逢迎,反而处处唱反调,而对文人则大加笼络。王世贞平生看重的是作为文人与史家的身份,无论是吟诗作文,还是修史以传之后世、藏之名山,都是文人的志向,所以王世贞志向更多的是希望成为一流的文人与一流的史家。正如前面提到,王世贞入仕后,就热心于文人的社团活动,后来与李攀龙同为天下文坛宗主。李攀龙去世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明史》称: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天下文人皆奔走于王世贞门下,王世贞对此非常看重,尤重视提携后进,奖掖不遗余力。陈继儒称之:“公之奖护后进,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出。”王锡爵亦赞之:“尤好以文字奖掖人,后生初学每得公一言品题,一面倾吐,则或希声射影,传相引重……以故人皆归心。”王世贞作为文坛领袖,对后学有循循长者之风,故在文坛有极高的威望。在“反智”高涨而极端专制的明代,文坛领袖注定是被摧残的对象。
王世贞为刑部主事时,有一阎姓犯人藏在当时权贵锦衣卫陆炳家,王世贞竟从陆炳家把他抓走,陆炳求首辅严嵩说情,王世贞竟不予理睬。最初严嵩鉴于王世贞的才气,有意笼络他,王世贞不仅不领情,反而故意讥讽。王锡爵言:“时分宜相当国,雅重公才名,数令具酒食征逐,微论相指,欲阴收公门下,公意不善也。”而文人间的唱和,颇令严嵩顾忌,王世贞自言道:“吟咏时流布人间,或称七子,或八子。吾曹实未尝相标榜也,而分宜氏当国,自谓得旁采风雅权,谗者间之,眈眈虎视,俱不免矣。”严嵩是权臣首辅,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谓“旁采风雅权”,严嵩想控制他们,这正是“反智”的一种重要表现,因为他是掌权者,所谓“有位者必有德”,但王世贞等人并不服从,故严嵩就要借机打击他们。更何况王世贞故意不买严嵩的账,令严嵩相当不满。多年后王世贞回忆这段时期的事情时,写道:
嘉靖中,余守尚书郎,九岁不迁,当自劾罢。客有过者, 谓贵人申申而詈:子非吴中小儿耶?奈何阔武膺视,不置长安睫间也?而又多使酒骂坐,抵掌谈说世事。一二少年嬲之不休,夫夫安能自罢!客谓:“吾子敖士也。”余愧谢无有。因忆曩者不自怿,间从历下小妇索苦满引,实不敢作步兵眼孔向人。性畏热,伏时从曹中还,以急谢谒剌,不善捉发,晨恒令家人捉之,以故蓬解不受栉,腰腹小肥,磬折差碍耳。即使酒骂坐,与世龌龊争长,岂真能为敖者。
由此可见,王世贞生性有一种傲气,所谓“使酒骂坐”“谈说世事”,正是士人历来的特性,而他这种性格正是当政者所难容的,是“反智”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最遭当权者忌恨的,故而他一直备受压制。但王世贞并没有从这种事情中吸取教训,他始终与严嵩对着干。沈德符从另一角度谈及这个时期王世贞与严嵩父子的关系,“王弇州为曹郎,故与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质(忬) 方总督蓟辽,姑示密以防其忮,而心甚薄之。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会王弟敬美继登第,分宜呼诸孙切责,以不克负荷,诃诮之。世蕃益恨望,日谮于父前,分宜遂欲以长史处之,赖徐华亭(阶)力救得免”。后来同榜进士杨继盛弹劾严嵩十大罪,严嵩不仅未动毫发,反而将杨继盛处以斩刑。杨继盛夫人上疏求救,王世贞亲为润色疏文。临刑前,杨继盛托孤于王世贞。杨继盛问斩以后,王世贞祭奠并亲为其收丧,“严氏微闻之,意不乐”。严嵩几度“意欲引置公为重,数近而公数远之,终不能笼公”。几度接触,王世贞皆不为所动。正因如此,严嵩在等待机会,以惩处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才子”。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犯大同,并围困北京达八日之久,而严嵩指令党羽丁汝夔、仇鸾坚壁清野,勿与俺答战,这就是“庚戌之变”。次年正月,锦衣卫经历沈炼即上《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策》疏,直接指陈“今虏寇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弹劾严嵩父子“十大罪状”。严嵩不仅未受丝毫损害,大学士李本在严世蕃的授意下,票拟圣旨,将沈炼杖责并流放塞外保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其党羽以“捕诸白莲教通叛者,窜炼名籍中,以叛闻,下兵部议尚书许论不为申理,嵩竟杀之,籍其家”。王世贞父亲王忬获知严嵩曲杀沈炼经历,非常气愤,“复对众指斥其奸,嵩闻知愈加切齿”。于是严嵩就寻找机会,报复王世贞父子。
嘉靖三十八年(1559),王忬以滦河战事失利,诏逮下狱。王世贞当即辞官,与弟王世懋日在京师,托门说客,求乞于严嵩及诸权贵,但最终没有结果。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其父被杀。王世贞扶柩归乡,从此归隐不出。王世贞认为其父被杀乃严嵩落井下石的结果。隆庆元年(1567),王世贞向同榜进士、内阁大学士李春芳上书,谈及其父被杀原因时说: 至于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冬,仲芳兄(杨继盛)且论报,世贞不自揣,托所知为严氏解救,不遂。已见其嫂代死疏辞戆,少为笔削。就义之后,躬视含殓, 经纪其丧。为奸人某某文饰以媚严氏。先人闻报,弹指唾骂, 亦为所诇。其二,杨某(指宣大总督杨顺)为严氏报仇,曲杀沈炼,奸罪万状,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间有指斥。渠误谓青琐之抨,先人预力,必欲报之而后已。其三,严氏与今元老相公(徐阶)方水火,时先人偶辱见收葭莩之末。渠复大疑有所弃就,奸人从中搆,牢不可解。以故练兵一事,于拟票内,一则曰大不如前,一则曰一卒不练,所以阴夺先帝之心而中伤先人者深矣。预报贼耗,则曰王某恐吓朝廷,多费军饷。虏贼既退,则曰将士欲战,王其不肯。兹谤既腾,虽使曾参为子,慈母有不投杼者哉! 这是王世贞向李春芳进言严嵩之所以迫害其父之原因,所以王世贞认为其父被杀,严嵩是应负责任的,这一点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但王忬被杀,严嵩是否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呢?王世贞是否亦认为严嵩对其父之死应负全部责任呢?对此学术界则有不同的看法,试细论之。
王世贞自始至终认为其父被杀是严嵩“阴夺先帝之心而中伤” 的结果,是故对严氏父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而最初王、严两家并无深仇大恨,只因一件件小事积忤成仇,以致最后有杀父之恨。即便如此,王世贞觉得最后决断还是出于世宗之手,以他作为史学家的眼光,他自然知道世宗的处事风格,王世贞论及世宗及严嵩与世宗的关系,道:
当是时,上深坐宫中,欲以威服远摄连率大臣,时时有所逮讯,若阮鹗、吴嘉会、章焕等多从重典。虽甚亲礼嵩而不尽信之,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而嵩与世蕃能得其窽,欲有所解救,则必顺上意极詈之,而婉曲解释,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称其微露若与彼亲者,而以冷语中之,或触上所耻与讳,上更为之怒。以是,卒不能脱其笼络而威福益广。
王世贞认为严嵩深得帝意的根源乃是他摸透了世宗的脾性, 故能巧借世宗皇帝之手而达到其打击政敌的目的。但有关大事的决断皆出自“圣裁”,是由世宗本人决定的,王世贞对这一点也是深信不疑的。范守己也称:世宗“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哉”。可见,世宗大权独揽,当时的人是坚信这一点的。因此王忬被杀,王世贞亦知是世宗最后决断的。所以事实上,王世贞并不认为严嵩对其父之被杀应负全部之责,而是指出他确实有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的责任,所以他说严嵩“阴夺先帝之心而中伤先人者深矣”,这是王世贞怪罪严嵩的原因。
王世贞与严嵩既有此仇恨,而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等史书中,又掩饰不住对严嵩的贬斥与厌恶,又有言在明末清初广为人知的、丑化严嵩的戏剧《鸣凤记》是王世贞所作,清官修《明史》则将严嵩定位奸臣,入《奸臣传》,于是,学术界咸认为严嵩被定为奸臣,与王世贞有直接的关系。即便当代学者,如美国学者苏均炜、新加坡学者李焯然和江西学者曹国庆等皆有此论。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也举出了各种史料予以支持,例如李焯然就说严嵩对嘉靖一朝亦有许多功绩,而他所重用之臣并非全是无能无德之辈,不能一概抹杀。且言:“严嵩对世宗皇帝,他可以说是一个忠臣。而在外廷,面对政府的官员,他是一个权臣。严嵩的忠, 是鞠躬尽瘁、俯首听命的忠,这也是在世宗这种皇帝底下唯一可以存在和得到信任的‘为臣之道’。”又说:“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我们认为严嵩对世宗的举动是过于奉承和谄媚,那么,严嵩的忠也可以说是庸。如因为这样便说严嵩是奸臣,是过分苛刻的。”所论甚是。不过,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从另一角度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意思,王世贞也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严嵩就是奸臣,评断人物也较为客观。
而清修《明史》,即便是秉承了王世贞《首辅传》的评断,而将严嵩列入《奸臣传》,也不能将责任推到王世贞身上。究其原因: 一方面,清修《明史》有其取舍标准,前人的资料只是参考,故不可太夸张前人的影响。《明史·奸臣传》所谓奸臣之标准是:“必其窃弄威柄、搆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胡惟庸、陈瑛、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莫不如此。二则,最重要的是看看严嵩本人的作为,严嵩与《明史·奸臣传》所收录的其他几位相比,所干坏事并不逊色。《明史》称:“嵩无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遣。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严嵩有这么多的“冤魂债主”,再加上他儿子严世蕃的助纣为虐,故而列入《奸臣传》是罪有应得。三则,明末清初,有关贬斥严嵩的戏剧、小说广为人知,严嵩在民众心目中早已是臭名昭著,或许王世贞在其中起过一些作用,但民众的心态非他一人所能左右,而是自沈炼、杨继盛等诸臣弹劾严嵩以来,民众同情他们的命运,接受并认同他们的观点,逐渐发展的结果。
总之,由于王世贞的不亲附,入仕一开始就把自己处于权臣首辅严嵩的对立面,又因他才高气傲,屡次冒犯严嵩,终成了被打击的对象,成了严嵩“反智”的牺牲品。杨继盛事件、沈炼事件,王世贞父子都表现出与严嵩完全不同的态度,从而更引起了严嵩的不满,严嵩遂从各方面对王世贞加以压制,不迁王世贞官职。他又借王忬领兵失事,将王忬推向刑场,同时也是对王世贞致命的一击。尽管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对严嵩有所讥刺,但因此而将清修《明史》将严嵩列入《奸臣传》的责任推到王世贞头上是不当的,也过分夸大了王世贞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