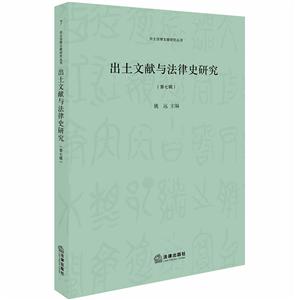作者:马凤春著
页数:226页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ISBN:9787562094197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简要介绍研究缘起、学界研究现状、研究对象等内容 ; 第二章对“例”字进行考证 ; 第三章介绍历代以“例”为名的法律形式 ; 第四章论述“例”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影响。
作者简介
马凤春,男,1977年生于山东济南,法学博士,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西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坚持“有教无类”的育人思想,秉承“述而不著”的治学观念,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和中国刑法史,已在《南京社会科学》《政法论丛》和《法治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目录
序
摘要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现状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
第三节 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 “例”的考证与“例”的前身
第一节 “例”的考证
第二节 比附、比与决事比
第三节 廷行事
第四节 故事
第三章 历代“例”的考证
第一节 历代“例”的具体表现
第二节 历代“例”的产生原因
第三节 “例”的生命力与“省例”的出现
第四章 “例”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影响
第一节 传统中国法的两个问题
第二节 缜密的法律立法技术——以刑法领域为例
第三节 “例”在当代的影响
第四节 应对当代法律文件数量膨胀的措施——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备案与审查
参考文献
致谢
节选
《“例”的法律史研究》: 第一,当各个部门法对特定社会关系还能调整的时候,刑法不宜出面,即当其他法律对某些行为尚未进行民事、行政调整之时,不能由刑法将尚未“违法”的行为直接“人罪”。 第二,当刑法对某类行为已有相关条文进行调整时,应当通过构成要件的解释,将目标行为解释纳入相关构成要件。即面对新出现的社会行为,应当考虑用尽既有刑法资源,而不是一味增加刑法罪刑条款。 就前述“虐待动物罪”的提议而言,我国目前尚缺乏《动物保护法》。虐待动物虽然遭到人们的指责,其肇事者的行为也属残忍之举,但这并不违法。在不违法的情况下,直接将这种行为人罪,是难以令人接受的。我国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目前受到保护的也只是野生动物。对于普通动物的保护,尚需人们道德素养的进一步提高,而且,随着社会精神文明的普遍提升,《动物保护法》的出台也许并不是奢望,进而由刑法考虑是否增设“虐待动物罪”也就水到渠成。不过,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虐待动物事件并非一律无法予以刑法规制,例如,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或破坏生产经营罪时,完全可以以此类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就前述“不孝罪”“袭警罪”的建议而言,相关当事人并未考虑到目前的刑法资源足以应对此两种情形。一方面,“不孝罪”的本质就是遗弃,刑法已有遗弃罪的设置。一方面,无论行为人“袭警”是否在人民警察履行公务之际,妨害公务罪与故意伤害罪足以解决。 其实,民众屡屡呼吁立法者增设新罪,是出于形象化思维。立法者不断增设某些罪名,是欠缺对于诸多犯罪问题的“类型化”思考。 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动辄呼吁刑法介入并增加新罪名的原因有二。第一,我国历史悠久的刑法文化。人们往往以为,自古至今刑法是最为主要的法律,运用刑法这个武器对丑恶社会现象进行打击是理所应当的。人们阅读的文学作品以及充斥荧屏的影视作品,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于法律的直接观感。甚至刑法学的一些研究者,也有一种思想误区,即认为中国古代法律一直“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第二,普通民众对于增设的新罪,往往根据行为的外在表象进行概括,而非把握其行为本质。即使对法律有所关注的人,也不一定能去除现象表面发现事件本质。因此,人们遇到某些丑恶社会现象作出以上两种反应很正常。而且中国人善于运用形象化的思维方式。明清时期,刑事条例不断增多,往往“因律生例”“因例生例”或者“因案生例”。除考虑封建服制等因素外,形象化思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存在比附这种技术,刑事条例数量的膨胀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作为制定法律的立法者过于惯用形象化思维,动辄新增所谓“新型犯罪”,则是不可取的。德国法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曾经指出对事物的本质思考属类型思考,类型介于普遍与特殊中间,其以可比较可区别之事物为前提,有别于个别现象或者个别事物,而犯罪类型介于刑法理念与生活事实之中间点,立法活动的任务就是要描述各种犯罪类型,因此,《刑法》分则罪状并非对具体犯罪定义的界定,而是对犯罪类型的描述。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其本质就是将具体案件中的相关因素进行类型化界定。而进行类型化界定之前,立法者应当对现实社会发生的形形色色案件,就侵害的法益(犯罪客体)、危害行为的特点、犯罪主体的身份、主观罪过的区别以及有无目的动机.进行抽象、提炼、概括,将值得科处刑罚的因素纳入刑法视野,进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犯罪。 《刑法》修订之际立法者对刑法与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的整合,以及修订施行的《刑法》本身存在的诸多缺陷,一方面令刑法学者思考今后刑法的修改模式,一方面让法史同仁给予从历史上律例关系角度的关注。 本书认为,刑法应当“凹凸有致”“厚此薄彼”,对社会危害较大而为立法者所重点关注的犯罪给予重点考量,对社会危害较小而立法者没有特别关注的犯罪给予一般对待。有此思路,在犯罪的设置问题上,才会有刑法体系轻重缓急。我国当前需要建立的是“严而不厉”的刑法体系,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仍然处于“厉而不严”的阶段和状态。早在1980年代,储槐植先生就曾指出刑法的主要倾向在于“厉而不严”。亦即,对于刑事犯罪的打击不能一味靠重刑靠“严打”,反之,对于应当由刑法予以规制的问题,刑法需要做到未曾有所遗漏。同时需要注意,刑法具有谦抑性,对于某些不值得动用刑法资源进行调整的问题,应抑制刑法的过多干涉。 对于犯罪的类型化设置问题,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可资借鉴。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对于故意杀人的犯罪,分别设有普通故意杀人罪、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义愤杀人罪、生母杀婴罪、教唆或者帮助自杀罪、受嘱托或者得承诺的杀人罪等多种具体犯罪。故意杀人罪是古今中外统治者普遍重视的犯罪。将故意杀人区分为不同的犯罪的做法,有利于实现罪刑相应。又如,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法普遍设有“强迫罪”(或称“强制罪”“强要罪”),对于那些行为人强迫被害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危害行为予以刑事制裁,而未对林林总总强迫型的犯罪,各立专条,不厌其烦地重复“施工”。 这启示我们,对于侵害重要法益的多发犯罪,宜分别立法,创制不同的罪刑条款;对于侵害次要法益的少发犯罪,宜统一立法规制,使之无所遗漏。 我国刑法在此方面尚有很大欠缺。1997年《刑法》修订之际,立法机关大量增设罪名,即是没有注意犯罪类型化问题的表现。例如,《刑法》未规定强迫罪,却规定大量具体的强迫型犯罪:强迫交易罪(第二百二十六条)、强迫职工劳动罪(第二百四十四条)、强迫卖血罪(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款)、强迫他人吸毒罪(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强迫卖淫罪(第三百五十八条)等。立法者始终未考虑增设或改设具有普遍涵摄功能的“强迫罪”以涵摄刑法未单独规定但社会生活可能发生的其他强迫行为或取代上述数种强迫型犯罪。实际上,刑法设置“强迫罪”这类概括性较强的犯罪,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稳定性,有利于实现刑法的正义性。2011年春,《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交易罪与强迫劳动罪进行修改,但是仍然没有进行类型化思考,未增设“强迫罪”以统一各类强迫型犯罪,而仅仅是具体列举或扩张该两罪的强迫内容。同样,2015年秋,《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对强迫卖淫罪有所改动,但远未触及犯罪类型化问题,其更是在虐待罪之外增设不免叠床架屋之嫌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第二百六十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