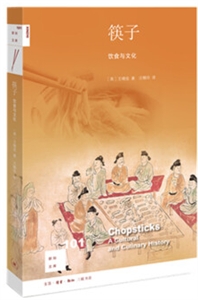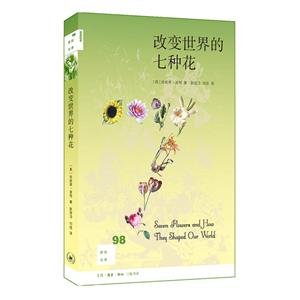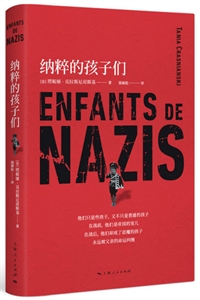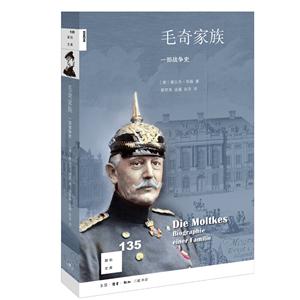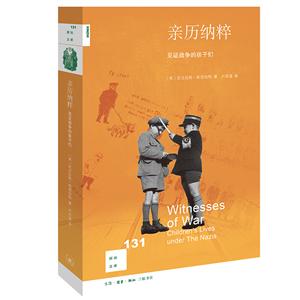
作者:[英]尼古拉斯·斯塔加特
页数:504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108069665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是部系统披露纳粹统治下孩子们艰辛生活的著作,也是一项对第三帝国政权下所有国籍和宗教的儿童遭遇的突破性研究。作者参考了档案、病例、日记、信笺、绘画和照片等大量资料,并对梦境、记忆碎片以及相关的图像或实物进行解析。通过对典型人物的长时段追踪,他把那些经历过第三帝国统治的人们的对立观点,以及形成强烈反差的经历逐一展现出来,所得发人深思,而他对战争后果的历史性描述更是意义深远,令人震撼。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在机械化战斗、饥饿政策、大逃亡、大屠杀、大轰炸中,孩子们往往是优选的牺牲品。而德意志儿童、犹太儿童、波兰儿童、捷克儿童、吉卜赛儿童以及缺陷儿童,都必须依据不同种族、国籍、身份而被隔离筛选,被培养成统治者或者奴隶,乃至被判定生死。作者同时打破了“受害者”和“心理创伤”的刻板印象,给我们讲述了战争中成长的那代人扣人心弦的故事。孩子们是活跃的积极分子,小小年纪就出来走私食品,倒卖物资,照顾病怏怏的父母和弱小的弟弟妹妹。而面对残酷现实,孩子们的适应能力则异乎寻常地强大。波兰男孩假扮盖世太保的审判官,犹太儿童则扮犹太人区的纳粹党卫军,在德军投降前夕,德国孩子甚至开始玩假扮苏军的游戏。通过角色扮演,孩子们得以发泄屈辱、嫉妒和恐惧,也得以寄托他们微薄的希望。
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父亲是德国犹太人,母亲是澳大利亚人,本人出生于墨尔本,在澳大利亚、日本和英国长大。他是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现代欧洲史教授,也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
目录
本书主要人物
导言
第一部分 大后方
第一章 战争中的德国人
第二章 受管制的年轻人
第三章 医学谋杀
第二部分 种族战争
第四章 生存空间
第五章 伟大的东征
第六章 驱逐犹太人
第七章 家庭集中营
第三部分 战争打到了德国境内
第八章 大轰炸
第九章 被赶回老家
第十章 最后的牺牲
第四部分 尾声
第十一章 战败的德国
第十二章 解放的人们
注释
地名对照表
致谢
译者的话
节选
第十一章 战败的德国(节选)
在奥地利上施蒂里亚(Upper Styria)的偏远地区,9岁的埃德加·普洛奇外出拾柴,正往婴儿车里塞柴火时,他看见一队携带武器的俄国人走下公路,往他们村走来。这个年纪轻轻的奥地利男孩沿着偏僻的小径一路奔回家里,给家人报了信。对战争的结束,埃德加永世难忘的记忆并非俄国人到来本身,而是俄国人到来前发生的极度恐慌。他第一次体验到,全家人坐在屋里一起等候俄国人到来,有种难逃一死的恐惧,这与1943年11月空袭柏林时莉泽洛
特·京策尔的体验,以及1939年9月米丽娅姆·瓦滕伯格的体验如出一辙。上施蒂里亚是受第三帝国保护的地区,这类地区的孩子们对战争最初的以及最后的体验往往像左脚倒右脚一样迅捷。在一个梅克伦堡(Mecklenburg)女孩眼里,俄国人占领数天前,看起来“大人们好像都想玩藏猫猫一样”。手表呀,剩余的珠宝呀,全都失踪了,都塞进玻璃储藏罐,埋到了地下。她玩的那些娃娃也藏进了柴堆里,为的是防止在农场干活的波兰小女孩们找到它们:她甚至不知道那些女孩多大年纪,不过她确实记得,她们“对所有玩具都抱有童心”。
恐惧会把成年人的权威和信心撕得粉碎,让他们像孩子一样觉得身心无助。在艰难跋涉途中,一个来自东普鲁士的女孩被苏联红军撵上,20世纪50年代中叶,已届豆蔻年华的她回忆道:“哪怕疑神疑鬼幻听出针尖掉到地上的声音,我们都会从睡梦中跳起来拼命尖叫,就像野兽害怕丢命一样尖叫。”不过,她接着记述道,那些当兵的一进门:“……我们的哭声立刻停了,我们双手拼命抓住妈妈,越抓越紧,大气不敢出,我们死盯着眼前的机关枪,从内心最深处不敢出气。其中一些当兵的被我们的行李绊倒,没有一个成年人敢喊停他们。一看见俄国人,所有胆量、所有力量、所有意志都被恐惧僵住了。”
自1945年2月伊始,一阵自杀狂潮席卷德国。4月和5月,仅柏林一地,就有5000人自杀。有时候,母亲和父亲自杀前,还会把孩子们杀掉。警方事后发现,从自杀留言看,多数人是被俄国人吓到了,或者仅仅是因为,德国战败后,他们怎么都想象不出还有未来。
对其他许多人来说,俄国人真的来了,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解脱感。士兵们向人们撒糖果和巧克力,还伸手抚摸新生儿,俄国人喜欢孩子,这说法很快成了传奇。在维也纳,俄国骑兵抱起6岁的卡尔·普凡德勒(Karl Pfandl),让他轮番坐到一匹匹战马背上。在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孩子们将骑兵连围了个水泄不通。卡尔·卡尔斯(Karl Kahrs)的小妹妹尖叫着跑回家,尾随她的是个想给她一根香肠的俄国士兵。
俄国人占领弗里德里希斯哈根第一夜,莉泽洛特·京策尔的母亲被强奸了。红军士兵到达威尔默斯多夫区第一夜,强奸的事也开始发生。每次俄国人走进赫塔·冯·格布哈特所在的地下室,她总会想方设法将女儿莱娜特藏到身后,希望来人会把别的女人带走。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士兵进来后,威胁将他们一个个全都枪毙,要么就用手榴弹把他们全都炸死,赫塔和另几个女人撺掇从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来的说捷克话的女人跟那人谈谈,后来那人停止威胁,将说捷克话的女人带走了。在附近的策伦多夫区(Zehlendorf),乌尔苏拉·冯·卡多夫有个朋友,俄国人到来时,她本来已经躲到一堆煤后边,结果被一个试图保护自己女儿的女人出卖。四个月后,第一次来看乌尔苏拉时,那个活泼漂亮的青年女子告诉乌尔苏拉,她如何被23个当兵的一个接一个轮奸,事后,人们只好把她送进医院,给她缝了好几针。“我再也不想,”那女人最后说,“跟男人做那种事了。”她也不想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了。许多母亲将处于青春期的女儿的头发剪短,把她们打扮成男孩。为了给年轻女性提供避难所,一位女医生在门上钉了个牌子,用德文和俄文注明:内有伤寒。用街上的水泵打水的女人喜欢扎堆,这些消息像野火一样在她们嘴里传开了。
女性被强奸的场合包括地下室、楼梯间、公寓内、大街上,甚至在强制劳动过程中——例如清理废墟,拆除生产性工厂,为俄国人削土豆皮,其中还夹杂着俄语喊声“手表,手表”——俄国人的喊声无处不在,尤其在天黑以后,喊声会变成“太太,来呀”。性暴力浪潮始于柏林城市保卫战,强奸女性常常当着邻居、丈夫、孩子、甚至陌生者的面。5月3日,德国军方停止抵抗后,性暴力才渐渐平息。在大型首都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多达一两成的女性成了强奸的牺牲品。红军士兵庆贺自己仍然活着取得了胜利,原本有严格的命令,举止要像“解放者”,而不是“复仇者”。苏联人跨过奥得河不久,他们的一些军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1942年以来,红军内部的宣传基调一直是复仇,如今新军令取而代之,变
成必须区别对待“纳粹”和普通德国人。斯大林心里清楚,英美同盟肯定不会阻止苏联占领东德,他要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的新领地,首当其冲的是,确保柏林不发生东普鲁士和西里西安那样的屠杀。要在身经百战的、必定要承担巨大伤亡的军队里实施如此天翻地覆的改变,已经为时过晚。当涉及到强奸的时候,苏联军官发现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采用即决处决的方式来让他们的人听话。最初几夜,为了给平民提供保护,一些苏联军官甚至睡在柏林的地窖里;还有一些军官则嘲笑德国妇女来告诉他们的故事。
孩子们如何看待那场性暴力爆发?1946年1月,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47所中学的学生受邀就那场战争写作文。许多孩子聚焦于柏林城保卫战。莲娜·H(Liane H)是个笃信共产主义的女孩,她曾经感谢“最高统帅斯大林将他们从纳粹帝国解放出来”,还诅咒过“该死的纳粹蠢猪”,她也曾经胆小地为第三帝国“摇旗呐喊”,就连她这样的人都承认:“那些俄国人曾经强暴过我们的女人,将许多人从人群里拉走。”一个男孩在日记里这样记述道,俄国人占领第一夜,他所在的位于希韦百纳大街的地下室有五个女人被拉走,在大楼第一层公寓里被强奸。不过,他的描述属于孤例。大多数提到强奸的男孩和女孩像莲娜·H一样坚称,这种事没有伤及他们自身和他们的母亲,或他们所在楼宇的女性。与莲娜不同的是,他们没表现出特殊的亲苏同情心。20世纪90年代,这些女孩里的两位接受了采访——时间是事情过去将近五十年后,东德政府已经消失后——她们仍然坚持当初的说法。两个人中的一位是克丽丝塔·J(Christa J),对当初的沉默,她给了个说法。她承认,当年他们班里的人,年龄都在十四五岁,“我的许多同学被强奸了,但我不记得是谁说过这种事”。即便如此,她依然坚称:“我被藏在地下室的某个地方……”
大规模强奸同时出现,却坚称躲过了强奸,这成了孩子们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阴影,20世纪50年代中叶,也就是事情过去十年后,那个将娃娃藏进柴堆的梅克伦堡女孩回忆说,妈妈如何“立刻给她穿上一件破衣服,裹上一条头巾,事先还往她头发上撒了些白粉,以便头发显得花白”。关于她对俄国人的看法,她是这么说的:“这些让我从心里对俄国人特别仇恨,与他们的关系变得较为正常后,一个俄国人想把我抱到膝头,我拼命尖叫,两脚乱踢。”20世纪90年代,“二战”中的孩子开始撰写回忆录,他们记述的内容与史实大同小异,只是细节方面更加精雕细琢。赫米内·狄里格尔(Hermine Dirrigl)当年14岁,一个非常年轻的俄国人闯入他们在维也纳的公寓时,很快看见了她和一个女孩朋友瑟缩地躲在窗帘背后。那个朋友跑了,赫米内没跑成,相反,妈妈把当时还是婴儿的弟弟塞进她怀里。“那当兵的用手势明确表示,我应当把婴儿交给别人,”五十多年后,赫米内回忆说,“我叔叔试图把那俄国人拉到屋外,他用枪威胁叔叔,最终他走了。”与各种成人的记述相较,赫米内的讲述似乎有缺失,那个俄国人竟然那么轻易便走了。难道存在当时她无法理解的某种成人的干预,一种压制的记忆,抑或是她刻意避免将某些事纳入个人回忆录,以免孩子和晚辈们读到,我们几乎没有可能说清这些。他们全家得到一位俄国军官无时无刻的保护,他成了他们的保护神,接下来继续讲述这件事时,关于妈妈是否与军官有性交往,她甚至也一带而过。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女孩们装聋作哑,像赫尔曼·格赖纳(Hermann Greiner)那样的男孩则引以为傲地宣称,自己如何堵在父母位于维也纳的公寓楼门口,阻止一个俄国士兵找一个女人,那俄国士兵已经看见那女人站在其中一扇窗子后边。以下内容摘自他的记述:“如果我个子再高点,我肯定会揍他,当时我就是用那种眼神看他的。我们之间虽然没说话,那俄国人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狠狠地一摔门,离开了公寓楼。”
在保护母亲和邻居方面,赫尔曼·格赖纳自认为是以爸爸为榜样,爸爸肯定会这么做。的确如此,在接下来的记述中,他很快谈到父亲如何上街斥责——用俄语——一个士兵,那当兵的正在追赶住在对面的一个女子。后边的内容摘自他的记述:“在我看来,其他所有男性移民和邻居都是鼠辈,就知道躲。”当年赫尔曼只有8岁。
孩子的沉默与当时身在柏林的成年女性之间露骨的笑谈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城市保卫战期间,那些举止文雅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的女性也得排队打水,领取配给,她们甚至也开始像大兵一样讲粗话。德国刚战败那几个月,女人们的话题开始转向对比德国士兵和俄国士兵的内衣裤、战争期间各交战方在欧洲大陆传播性病的方式,以及俄国人和美国人不同的性取向等。她们创造了新俚语,用以舒缓寻找军官们保护所带来的耻辱,如“为肚子陪睡”“少校的心肝”“越轨的鞋子”等。让人深为怀疑的是,她们曾否对自己的孩子,甚或青春期的女儿说过此等低俗的话。那个年代,14岁的女孩们都没有接受过性教育,更别说性经历了,她们没办法形容发生了什么;当时所有学校和家庭好像都无法帮助女孩和男孩们说出自己的性经历。
随着“社会常态”得以恢复,强奸渐渐成了禁忌话题。在苏联占领区,一些共产党员向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请愿,要求党内公开讨论苏联人强奸的问题,他告诉那些人,这个问题必须留待以后讨论。到了冷战兴起,乌布利希领导的东德政权就此问题设立了一个审查机构,这个机构一直存在到1989年该政权垮台。在西德,冷战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在1949年第一次联邦选举期间,蒙古眼型的苏联强奸犯形象出现在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巴伐利亚地区选举海报上,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全国各地采用,并成为鲁尔地区部分地区的常见话题。鲁尔地区大大小小的城镇已经被英美同盟夷为平地,而苏联士兵从未涉足那一地区。随着“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犹太意象,在西德完全失宠,戈培尔的“欧洲文化”的最终形象,与“亚洲的”俄罗斯“野蛮主义”对抗,获得了新的生机。
以上这些对强奸受害者毫无助益。20世纪50年代初,就女性受到的各种伤害,政府往往拒绝给予补偿,女性谈论其经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打压。这一不断强化的社会禁忌使得用恰当方式表白受伤害的痛苦和耻辱变得愈加困难,20世纪90年代,口述史学家开始就这一主题不断提问,这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明显。那些战争期间还是孩子的女性不愿意谈论自己当年究竟经历了什么,她们的讲述全都以第三人称开篇,她们说的那些事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非自己或自己母亲身上。一部分困难源自家庭内部,那些已经建立婚姻关系的夫妻,整个
战争期间一直保持着频繁密切的通信往来,尽管如此,女方往往认为,无法将自己遭受的强奸披露给男方,是为了不让对方感到无地自容,从而避免家庭风暴。不仅从战俘营返回的德国士兵对自己和妻子的性行为有双重道德标准,德国男人还在男性荣誉观的培养下成长,秉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捍卫家庭是他们的责任,而强奸是对家庭的破坏。强奸既是背叛,也是男性无能的标志。
青春前期男孩赫尔曼·格赖纳的座右铭是“生当作人杰”,如果说,男性“懦夫”在维也纳的失败让他深感失望,对其他年龄更小的少年来说,父辈权威的垮塌实在出人意料。汉堡遭燃烧弹轰炸后,乌韦·蒂姆和妈妈住到了科堡市(Coburg)一个小区的纳粹党领袖遗孀隔壁,许多纳粹官员经常登门拜访这位遗孀。对5岁的乌韦来说,“二战”结束时,“时隔一天,所有大人物、成年人,一下子都变小了”。第三帝国的声音消失了。过去他经常在街上和他家房子的楼梯间里听到男人们说话声若洪钟,如今人们的说话方式似乎都变成了小人物道歉的方式。犹如德国士兵脚踏钉了铁掌的长靴,落地有声,如今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大兵”的胶底鞋,近乎落地无声。连美国人使用的汽油气味都有些不一样,更甜一些,有点儿类似他们扔给像他一样的孩子们的口香糖和巧克力。正如波兰孩子和犹太孩子往往不自觉地嫉妒德国士兵,德国孩子们亦如此,征服者所拥有的一切难以避免地吸引着他们。
成人仍然畏惧与俄国人交往之际,常常指使孩子们与征服者打交道。为了给父亲要到卷“大炮”用的烟丝,维也纳的黑尔佳·格罗兹(Helga Grotzsch)前去与俄国人打交道。还有一次,母亲带着孩子们前往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求情,母亲让孩子们大哭,以便对
方不把他们赶出现有住宅。黑尔佳·格罗兹挖苦地回忆道:“显然,我们大哭大闹得恰到好处。他们同意我们继续住下去。”更为常见的是,孩子被当作中间人。黑尔佳·费勒(Helga Feyler)仍然记得奶奶派她前往村子旁边的苏联营地要食物的场景,奶奶已经想到,派成年人过去实在危险,不过她非常肯定,俄国人不会伤害孩子。俄国人的营地周围有一圈围栏,10岁的黑尔佳带着还是婴儿的弟弟刚刚靠近,第一个看见他们的士兵就发出嘘声,驱赶他们离开。后来他们遇到了第二个士兵,对方示意要用白面包交换她弟弟。她摇头拒绝,为赢得信任,对方掏出一张与自己儿子合影的照片,同时指着自己,用磕磕巴巴的德语说:“我,父亲……想儿子。”黑尔佳把包包递给对方,然后将婴儿弟弟举过围栏。当时她觉得,那当兵的满脸都是思念家人的样子,他把孩子高高举起,转了几圈,然后紧紧地搂进怀里,抚摸着孩子的头发。小男孩开始哭闹,他把孩子从围栏上递了出来,还在包包上放了两块面包。后来黑尔佳发现,面包下边还压着食用糖和一块肉。那一时期,太多成年人在孩子们眼里失去了地位,诸如此类的事让孩子对自身的重要性有了新发现。对这类与占领有关的事情,孩子不仅是旁观者,他们很快成了积极的参与者。
成人烧掉了旧制服、纳粹党徽以及许多藏书,烧掉的还包括孩子的东西,实际上,大人是在抛弃孩子成长过程中珍视的许多东西。英国军队列队进入奥斯纳布吕克时,迪克·西韦特的家人甚至将他倾注全副身心收集的、粘贴在《英格兰强盗国》(Raubstaat England)里的香烟卡全都清理掉了。各家各户将希特勒青年团的穗带和服装、德国国防军的海报、党卫军的制服等全都丢弃了,还把青年运动纪念短剑和其他武器一同扔进各村的池塘。那一时期,出门到野地里和林子里玩耍的孩子偷偷捡回一些他人丢弃的武器,拿在手里把玩,时常会引发致命的后果。维也纳是4月13日陷落的,5月1日那天,当地人缝制了一些新旗帜外出悬挂,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急中生智,用红布盖住旧旗帜白色的圆心,将其缝死。好像是为了嘲弄与“解放者”团结一心的种种努力,当时红布掩盖的纳粹“卐”字符在阳光映照下暴露无遗。对孩子和青少年而言,在必须撕掉希特勒青年团的徽章和丢弃短剑那一刻,往往特别痛苦,也颠覆了一直以来灌输给他们的所有关于责任、服从、荣誉的说教。一些男孩偷偷标记了丢弃武器的地点,以便将来把它们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