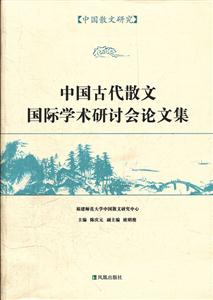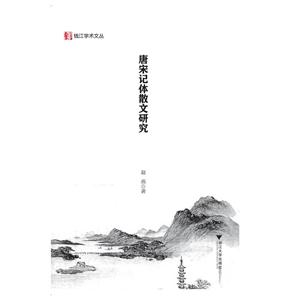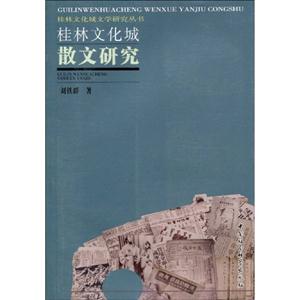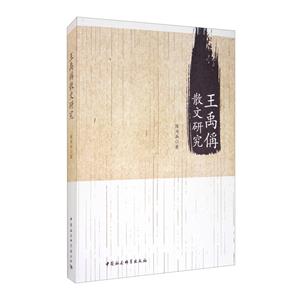
作者:沈石溪
页数:301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2036714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王禹偁散文研究》主要对王禹偁散文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除绪论、结语外,主要内容包括:王禹偁生平及作品概述、王禹偁的碑体文、王禹俑的序体文、王禹偁的表体文和王禹偁散文的其他几种文体。该书的特点是对王禹偁散文按立体进行分类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为该书主体部分。除第五章介绍多种文体、形式不固定外,其余三章均是介绍单一文体并按照“文体概论-作品分析-文体小结”的行文模式展开讨论。另外该书附录部分还汇集了大量的王禹偁研究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可供后来的研究者参考。
作者简介
陈为兵,山东五莲人,华中科技大学文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已发表文章近二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
本书特色
关于文章的体式,金代王若虚有文章“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之说,可见界定一种文体并非易事,因此在讨论王禹偁散文之前有必要对“散文”这一概念作个说明。
“散文”一词□早出现于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其丙编卷二称黄庭坚“山谷诗骚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甲编卷二则引周必大语,评论黄庭坚“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虽然没明确指明什么是散文,但也明显将其与诗对立了。而且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就是罗大经提到了黄庭坚的“四六”即骈体文虽讲究骈偶对仗但意蕴与“散文”同,很明显“散文”与骈体文在形式上也是相对的。
秦汉之前骈散是不分的,而且汉赋产生之后骈体文一直在中国文坛上占有绝对统治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唐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所尊崇的正是先秦时期的诸子散文,诸子散文是不讲韵律和骈偶的。因此宋明两代文人更愿意将长短错落、无韵律骈俪之拘束,不讲求辞藻与用典的文章称为“古文”,其实就是散文,朱自清在《什么是散文》一文中予以了确认了这一点:“散文的意思不止一个。对骈文来说,是不用对偶的单笔,即所谓的散行的文字,唐以来的’古文’便是这东西”。
其他很多现代文学家也对此进行了解释,譬如葛琴在《略谈散文》中认为:“’散文’一词( Prose),在西洋里是相对于韵文(Po-etry)而言,凡不是用韵脚的文体,都总称散文。”梁实秋在《论散文》中则指出散文和韵文的区别“便是形式上的不同:散文没有准定的节奏,而韵文有规则的音律;散文没有一定格式,是□自由的,而韵文格式是一定的,韵法也是有准则的”,近代文学家陈衍更是在《散体文正名》中直接指出“不骈俪即为散文”。
由此可见,“散文”是个很宽泛的概念,除了诗歌、辞赋和骈体文等讲究音韵、格式的文体之外所有文章都可以被称为“散文”。“但中国的散文不能这样包罗万有,不惟不能把小说拉进来做它的部下,就是介乎诗文之间的赋、骈文及戏剧,也不能包括在内。’散文云者,乃对四六对偶之文而言’,这真是中国散文□好的定义”(罗泽根《罗泽根古典论文集》)。由此我们可以基本断定,古代作家作品中排除诗歌、骈文、赋、戏剧及小说之外的文体就是“散文”了。
就本书讨论的宋代作家王禹偁而言,其所留存的文集中并无小说和戏剧,排除其中的诗歌和赋,剩余皆可视之为散文,具体情况阐述如下:
《小畜集》三十卷卷一为古赋,卷二为律赋,卷三、卷四和卷五为古调诗,卷六为古诗,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和卷十一为律诗,卷十二和卷十三为歌行,以上皆不在本书讨论之列。其余十七卷均为散文,分别为:卷十四杂文,卷十五论,卷十六、十七碑记,卷十八书,卷十九、卷二十序,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表,卷二十五笺启,卷二十六、卷二十七拟试内制五题,卷二十八、卷二十九碑志,卷三十志碣。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王禹偁生平及作品概述
第一节 王禹偁生平简介
第二节 王禹偁作品概述
第二章 王禹偁的碑体文
第一节 碑体文的形态演变和特征
第二节 王禹偁的碑体文
第三节 王禹偁碑体文小结
第三章 王禹偁的序体文
第一节 序体文的发展及特征
第二节 王禹偁的作品集序
第三节 王禹偁的赠序文
第四节 王禹偁序体文小结
第四章 王禹偁的表体文
第一节 表体文的发展与文体特征
第二节 王禹偁的表体文
第三节 王禹偁的笺、启文
第四节 王禹偁表体文小结
第五章 王禹偁散文的其他几种文体
第一节 杂体文
第二节 书体文
第三节 记体文
第四节 论体文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一 王禹偁作品书目提要
附录二 王禹偁《滁州全椒县宝林寺重修大殿碑》考证一则
附录三 王禹偁年谱简编(黄启方)
附录四 王禹偁史料汇编
附录五 王禹偁政论文研究
后记
节选
《王禹偁散文研究》: 二 个体作品集序:叙事详尽、色彩浓厚王禹偁专门为个人的作品集撰写的序包括《东观集序》《冯氏家集前序》《孟水部诗集序》《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桂阳罗君游太湖洞庭诗序》和《神童刘少逸与时贤联句诗序》等6篇,从文章结构来看,这几篇序和我们今天的书序是大致一样的。 这些序文有着很明显的共同体例,每篇一开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先对作品集作者做一个定位性评价,然后叙述著作者的个人履历,接着对作品集及其著作者进行评价,说明作品集的编写体例和内容,最后交代作序的目的、时间和撰序者的身份,当然也不忘顺便表达一下自谦之意,这种体例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 《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以“释子谓佛书为内典,谓儒书为外学,工诗则众,工文则鲜,并是四者,其惟大师”将通惠大师定义为精通儒佛两家之学、工于诗文的大家,接着全文用大篇幅叙述大师的平生履历,重点突出其文名备受时人推崇,最后以“猥蒙见托,不克固辞。总其篇题,具如别录,凡内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学集四十九卷。览其文,知其道矣。因征其世家行事,备而书之,使后之传高僧铭塔庙者,于兹取信云”收尾,将作序者自谦、大师文集的编写体例和作序的目的一一解释清楚。 总体说来,王禹偁这类序文有两大特点。一是叙事极为详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叙事本来也是序的特征,只不过因为所序之事的特殊性,王禹偁在这些序里叙事可谓是不惜笔墨。譬如《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就将通惠大师从出生到终老的过程完整而详尽地一一交代,《孟水部诗集序》尤其如此,其他序亦然。之所以如此,是跟王禹偁作此类序的目的和原则有关,如《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云“因征其世家行事,备而书之,使后之传高僧铭塔庙者,于兹取信云”,《东观集序》亦云“故并序其官氏,拜章进御,乞付三馆,亦所以备史笔之阙文也”,正是出于“备”的目的,所以在王禹偁的这类序里所序之人的生平资料尤为详尽,这就使这些序文具备了史料价值。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是《孟水部诗集序》,由于孟水部诗集在元代之后佚失,现存于各种史料著作中有关作者孟宾于的资料都是以王禹偁这篇序为依据的,后人也只能从这篇序里了解孟宾于的生平履历和著作情况,其史学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这类序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主观色彩浓厚。通过序文内容来看,这应该跟王禹偁与所序之人之间的关系有关。在《东观集序》《冯氏家集前序》《孟水部诗集序》《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桂阳罗君游太湖洞庭诗序》和《神童刘少逸与时贤联句诗序》等6篇序文里所叙之人不是王禹偁的同年挚友就是其钦佩之人,在叙事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个人情感是无法避免的,唯其如此,王禹偁此类序文往往充溢着动人的感情色彩,这种感情或是由衷的仰慕,或者是痛彻心扉的悲伤,抑或是情不自胜的欢欣。 王禹傅是很反对佛教的,认为“像教弥兴,兰若过多,缁徒孔炽,蠹人害政,莫甚于斯”,其对佛教强烈的排斥态度招致众僧尼的怨恨,直接导致被贬商州,王禹偁的一生从此大起大落、反反复复直至死于职守。从这一点来说,王禹偁能够为通惠大师的文集作序实属难当,如果不是出于对通惠大师学贯儒释两家的超人文学才华的敬佩,单凭他对佛教的态度是绝对不可能为一个僧人作序的,文章不但开始就发出了“其惟大师”的赞叹,而且最后还用“岂所谓必得其寿,必得其位乎”来表达对大师的仰羡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