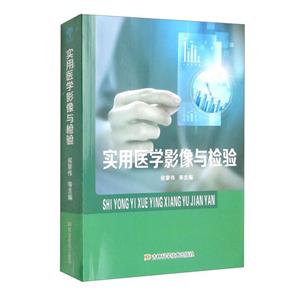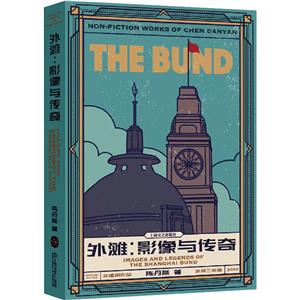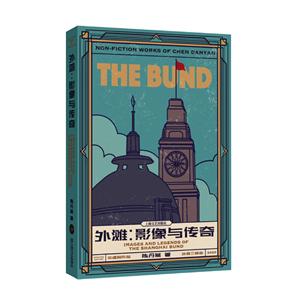
作者:陈丹燕著
页数:409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32154067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作者以“非虚构”、“影像”这种特殊的视角,以海派式绵密、细腻的文字讲述了外滩的前世今生,揭开了外滩这艘内蕴丰富的历史巨轮光影斑驳的面纱。
在作者笔下,为逃避中靠前战从外滩乘船离开的外国侨民,出生于上海、拍摄了1949年外滩的外国摄影师山姆?塔塔,携女儿到上海总会遗址追寻自己童年记忆的母亲,号称要重新点亮外滩的“外滩三号联合会”主席李景汉,以及租界时期连接外滩商业繁荣的洋泾浜英语,1950年代外滩长夜一般的寂静,1966年出现在友谊商店外墙上“全世界劳动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巨型宣传画, 1970、1980年代的外滩恋人墙,1990年代的外滩改造工程……绵密的细节铺陈着那些与外滩有过特殊经验的人与事,使得历史具有了呼吸和温度。
全书配图170多幅。影像式表达与非虚构讲述联袂,生动再现了外滩前世今生的传奇。
作者简介
陈丹燕,1980年代以儿童文学创作步入文坛, 1990年代转入成人文学创作,以非虚构纪实类作品和其漫游世界的旅行文学广受关注。主要作品有外滩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另有《永不拓宽的街道》《慢船去中国》《一个女孩》《我的妈妈是精灵》,以及12本陈丹燕旅行文学丛书和新长篇小说《白雪公主的简历》。 作品在国内外广受赞誉。曾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上海图书奖一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金奖,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银奖,及中国台湾《联合报》等媒体颁发的年度优秀图书奖。其旅行文学作品获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特殊贡献奖,及中国百家书店评选的“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之“旅行文学奖”。作品已被译为英、德、日等多国文字。
本书特色
陈丹燕的外滩故事使我们得以了解城市的记忆和建筑的灵魂,得以触摸城市的文脉,让生活在此处的人们知道自己的来历,也因此看见自己的未来。
——同济大学教授 阮仪三
陈丹燕凭着幼年记忆、前辈口述和从欧洲查阅到的各种档案,以“再全球化”视角,回看上海文化中一直保存着的“大都会精神”。外滩是他,是你,也是我,陈丹燕这本“大好的小书”诠释了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外滩。
——复旦大学教授、史诗纪录片《外滩》学术总顾问 李天纲
读陈丹燕的外滩,你能体会到作者敏锐的感受、细密的观察、真实而诚实的态度以及开阔的世界观。她笔下上海人的视角、中国人的视角、亚州人的视角以及西方人的视角,都有所不同。
——德国汉学家、本书德文版译者 郝慕天
目录
第二章·宿命
第三章·不可能的世界
第四章·纪念碑
第五章·梦想的烟尘岁月
第六章: 怀乡痛
跋: 外滩写作记
节选
第一章 黑白马赛克 黑衣人走向灯光璀璨的门厅,拖着他们长长的影子,那是维多利亚时代飘洋过海而来的自重,趣味,势利,还有工业革命时代的人们对光鲜事物无限热衷的遗风。 他们的背影看上去真是时髦与复杂,就像混合亚欧口味的食物那样,带有一种开放和投机的灵巧。东方人细长单薄的身体,宛如一只单反相机里极其敏感的测光仪,时刻根据不同的光线做出调整。即使是后背,也长着眼睛,时刻观察自己在外人眼中的反应,以及四周的动静。男人们穿着黑色的夏季西装,意大利鞋,里面的衬衣也是黑色的,并敞着领口,这样既冲淡了拘谨,又保持了进出外滩大楼应有的隆重。现在,出没夜店的男人们已再次讲究起来。他们谨慎地选择黑色,在面料和牌子上下工夫,掩盖自己在颜色和款式上的贫乏想象,他们投入浮华生活的时间毕竟太短,趣味与自信都还没有成熟,还不能炫技,只可求不错。 十九世纪末的晚上,外滩的生意人只有上海总会一个去处。去上海总会,他们要穿好黑色燕尾服和白色衬衣,打黑色呔。有一夜,遇到租界火警,正靠在吧台边喝酒的救火会志愿者们来不及换衣服,就冲出去救火。镶了一层黑缎子边的黑色衣尾在火光熊熊的夜色里随风飘起,沾满了焦炭的气味。过后,工部局通知他们,可以将那晚洗烫修补礼服的洗衣店发票拿去报销。这是另一个关于黄浦滩上的黑色礼服的故事。 黑衣人三五成群地消失在旧渣打银行门庭的灯光里,像解一道合并同类项的数学题那样,归成一个符号。 她们是一对长得很相像的母女,长脸。在自天花板而下的灯光里显得更长。 玛丽莲吊灯洒下明亮而匀称的光芒。这些大小不一,出现在大楼各个角落的、红色里夹了金箔的玻璃吊灯,是第二次从意大利舶来的镇楼之宝。第一次从意大利来的镇楼之宝,是1920年代从意大利教堂里买来的大理石圆柱,据说它们还是米开朗基罗时代开采的。精确地说,这次不再是舶来,而是空运。“舶来品”这个词也已经过气了。 玛丽莲吊灯让人想起威尼斯那些昂贵而易碎的古老玻璃,和弥漫着旧缎子和耗子味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往事。但是,如果经历过上海1970年代和1980年代由于电力不足而全城灯光黯淡发红的岁月,才能体会到它们给予的明亮与柔和所意味着的渴望。这是完全不同于威尼斯的渴望。 地上细小,而且排列并不规则的白黑两色的马赛克铺满了她的眼睛,犹如《太阳帝国》里描绘过的,在黄浦江里漂浮的一口小孩的棺材那样,在她回忆里晃动。“是它吗?是原来的那些吗?”她猜测着。 大楼修复时,专门介绍了修复时对马赛克地坪的保护。当时她读到报道,眼前浮现出的门厅,是幽暗而高大的。马赛克地面好像蠕动的蟒蛇一样冰凉,并有一种威慑力强大的鳞状图案,马赛克在水泥上微轻的不规则排列,就像蟒蛇隆起时,撑开了鳞状物之间的皱褶。 这是八十年前的旧物。保留着1920年代亲切的手工痕迹的马赛克,看上去像雨后的泥地一样柔软,容易留下痕迹。完全没有如今的马赛克那样冰冷和规整。那些手工的痕迹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黑衣人沐浴在灯光下,洗得干干净净并散发名牌香水气味的身体,保养良好的头发,在黑色的衬托下格外白皙的手背和下巴,如同沐浴在阳光里的植物一样自在而感恩。冷气很快就使皮肤变得凉爽干燥,他们脸上因争斗而隆起的肌肉放松下来,变得彬彬有礼。 出示请柬。 与迎候的英国领事馆雇员寒暄,握手,探出上身去行贴面礼,嘬起嘴唇,轻轻向对方的耳朵发出亲吻的声音,“啧”,客气的,只贴一次。 留下名片。 “请好好享受我们的晚会。”领事馆的年轻本地雇员说了一口伦敦音,是上海的知识阶层一贯崇尚的口音,象征着教养与见识。说伦敦音的年轻女子将人群引向装饰着红色琉璃的电梯。曾有人形容它像一只圣罗兰的皮箱。这是外滩大楼渐渐成为展示西方世界奢侈品世界的前沿后,最为时兴和卖弄的联想。媒体对外滩的变化总是如此惊喜,并试图确切地形容。 “不,不不,我们更喜欢走楼梯。”她说。 于是她们拾阶而上。 她的女儿探头看了看楼梯井。 楼梯井很宽大,带有1920年代的欧洲线条,轻微的装饰艺术风格,扶手蜿蜒盘旋,很有线条感。下面,是满满一地细小的马赛克,彬彬有礼地闪亮在灯光里。 少女伸出手,用日本产的照相机拍下一张照片。她是属于针孔时代的孩子,到哪都带着照相机,当她想要了解什么的时候,就去拍一堆照片过来,然后去研究照片,得出自己的结论。她保留着大量自己的作品,从幼儿园时代的老师硕大的鼻孔,菜场附近地上被人丢弃的橘子皮,到今年春天深夜,自己被突然涌出的鼻血惊醒后惊恐的脸。 她有些怀疑女儿此刻这样做,更多是为了安慰她。于是,她感激而委屈地瞥了她一眼。 她也探头看了看楼梯井。金色的灯光从每一层楼的扶手处倾泻出来,楼梯间里寂静无声,她再次见到各个楼层转角处露出的黑白镶嵌的马赛克地面。 在外滩,当你走进一栋建筑,堤岸上的嘈杂之声被门切断,门厅里的光线照耀你,大楼里的空气包裹你,你顿时落入另一个时空,落入丧失自己方位的恍惚中。也许这是一种令人感到舒服的恍惚,假扮成另外一个人的可能,像迅速上涨的水一般令身体浮起,划动四肢是这时的本能,它令你开始漂浮。从各种外滩在经历沧海桑田时的各种遗留物中浮起,它们宛如在被多年污染的海里掠过的鱼虾和海藻,以及轮船留下的油污和可疑的拖鞋,还有长满绿苔的碎木板。你心中悠悠地交织着惊喜与厌恶。 “我们先去看看外公从前的办公室吧。”她说,“就在电梯出来左拐,第一间,有一扇窗,我在那扇窗前第一次看到外滩。” “唔。”她的孩子应道。 天花板是乳白色的,很高,与墙壁连接处饰有宽大的顶角线。房间也很大,这是一间气派讲究的办公室。 里面的家具虽然是木头的,可所有桌椅,沙发,茶几和书橱的腿,都刻意雕刻出竹子的样子,突出它的中国风格。宽大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景德镇出产的瓷杯,杯子上画了满满的中国山水,明媚的青山绿水,蚱蜢舟,一行白鹭,山中草亭里凭栏而立的书生。 墙上挂着一只双鱼铜盘,一条鱼象征中国,另一条象征波兰,它们交颈缠绕,好像很亲密,但它们脸上身上的什么地方,却有种阴沉不快的神情。C-P的缩写被刻在一面狭长而僵硬的旗帜上,在鱼头上方。 办公室的窗子正对外滩堤岸,很有处在世界中心的荣耀感。当年在窗前,一眼望出去,先看到的,是英国领事巴夏礼的铜像。铜像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本海军捣毁,到1960年代中期,渣打银行遗下的家具也已不知去向。 沙发椅前的茶几上有一大本轮船的照片集。甲板,大海,高大的桅杆,从蒸汽轮脱胎而来的粗大烟囱上印着C-P,那是中波海运公司的标志,1950年成立于美国对中国海岸线的全面封锁中。它是1949年后中国政府建立的第一家合营航运公司。整个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一时间只得依靠几条挂波兰国旗的轮船。它也是外滩各家洋行迁出以后,唯一一家在外滩有外国雇员的航运公司。这间办公室,大概也是外滩大楼里唯一不合适挂毛泽东像的党委书记办公室。所以,办公室里有由活生生的咖啡,香水和纸烟混合在一起的非中国气味,和刻意为之的中国风格。但这却并不是要强调东方情调,而是婉转表达的民族自尊。 颗粒粗大的黑白照片散发着海洋的气息,它勾起人去揣测和幻想漂洋过海的自由。某一张照片中的甲板上,凭栏站着一个年轻的波兰水手。他的影子长长地与桅杆和缆绳的影子交错在一起。他脸上,肩膀上,从白色制服裤子里隆起的窄小而结实的胯骨上,迎风露出的额头上,处处洋溢着令人羡慕的自由。一个迎风而立的水手对被迫封闭的通商口岸城市,充满了诱惑。 这间办公室里套着一个小衣帽间。里面有一排柚木做的衣架,靠墙还有一排鞋架。衣架上挂着一套卡叽布衣服。每个星期四,西装革履去上班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穿这套带着汗味的布衣回家,好像换了一个人。因为每星期四下午,是当时全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日子。每个星期四,他都去码头和装卸工一起劳动。他一直都喜欢与码头工人在一起,也喜欢出汗。他非常警惕自己生活中出现的修正主义元素。 更衣间靠墙角的阴影里竖着一只圣罗兰旅行箱。那个半人高的硬壳箱子里能挂好几套烫好的西装和衬衣,还有几个用缎子包着的小抽屉,可以分别放袖卡,领带夹,和皮鞋。箱子把手上,用白色的细棉线吊着东欧各国航空公司的标签。可以看出,箱子的主人对航空公司的热衷,那是1960年代男人对新科技的欣赏和沾沾自喜。那是一只属于他的旅行箱,出差去东欧各个港口时用的。 宽大的办公桌斜斜横在窗边,那张桌子大得就像一张床。坐在大桌子上,正好能看到窗外长长一条外滩。 满满一窗,都是1960年代的外滩。 她坐在窗前的写字桌上望着窗外的外滩。 那时,她还不足六岁,为了跟父亲到办公室来加班,母亲为她换上了最好的连衣裙,还梳了头。裙子是用红白两色的朝阳格做的,领口镶了一圈白色的的确良,上面分别绣着小房子,花,热带鱼,和戴草帽的小姑娘。 父亲要去会议室开一个小会。离开前,他给了她几块糖,和一大玻璃杯水。告诉她,要等嘴里一点甜味也没有了,才能吃第二块糖。等糖全吃光了,水也喝干净了,他就应该开完会回来了。 穿着一身淡蓝色薄呢连衣裙的波兰秘书抱着一本大笔记本,在门口看他安顿自己的小女儿,微笑在她脸上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她走进来,到小女孩面前,摊开手掌。 粉红色的手掌里躺着一粒苏联产的太妃糖,比中国糖果要大一倍,像一条大肚子金鱼。 她将太妃糖放进小女孩的糖果堆里:“波兰糖,我妈妈寄来的。”她有很重的波兰口音。 “谢谢拉拉小姐。”小女孩看父亲脸上没有反对的暗示,便收下这件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