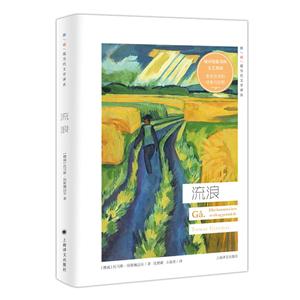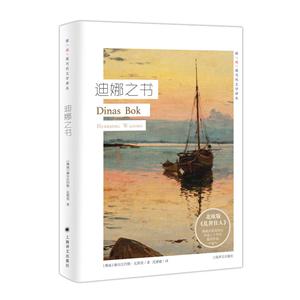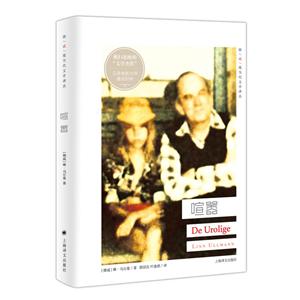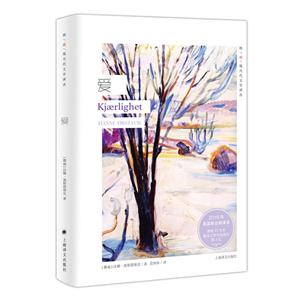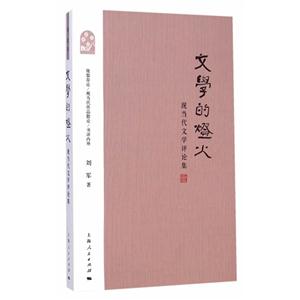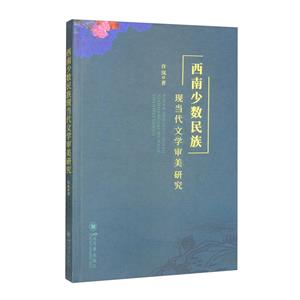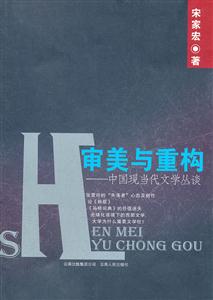作者:王存良
页数:242页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45148114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学革命的发动、激进与保守的争论、中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白话新诗的创立与发展、现代小说的新探索、现代散文的新貌、现代话剧的萌芽、文学思潮等。
目录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第二节 文学革命的发动
第三节 激进与保守的争论
第二章 运动中的新文学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
第二节 白话新诗的创立与发展
第三节 现代小说的新探索
第四节 现代散文的新貌
第五节 现代话剧的萌芽
第三章 革命文学
第一节 文学思潮
第二节 革命文学时期的小说
第三节 文学运动时期的诗歌
第四节 文学运动时期的散文
第五节 革命文学时代的戏剧
第四章 战争中的文学
第一节 战争时代的小说
第二节 战争时期的诗歌
第三节 战争时代的散文
第四节 战争时期的话剧
第五章 十七年文学
第一节 十七年文学创作概述
第二节 十七年文学的审美特征
第三节 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势态
第六章 当代文学的启蒙
第一节 新启蒙时代的小说创作
第二节 新启蒙时代的诗歌创作
第三节 新启蒙时代的散文创作
第四节 新启蒙时代的话剧创作
第七章 互联网时期的文学发展
第一节 网络文学概述
……
第八章 现当代散文审美
第九章 现当代诗歌审美
第十章 现当代戏剧审美
第十一章 现当代小说赏析
参考文献
节选
《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审美》: (一)前期杂文 鲁迅的前期杂文包括从1918年到1927年的作品,大都收入《坟》《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还有一部分收入《而已集》《集外集》中。鲁迅本期的杂文始终贯穿着清醒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直面现实,用敏锐的洞察力,透彻地剖析了病态的社会现象和心理,无情地鞭挞了吃人的旧礼教、旧思想和一切反动的社会势力。 妇女和下一代,是儒家三纲中压迫的两大对象,因而在反对封建礼教,张扬民主的斗争中,鲁迅首先说到了妇女和儿童的问题。发表于1918年8月《新青年》上的论文《我之节烈观》,1919年11月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后来发表的《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等都深入批判了吃人的礼教,腐朽的文明,主张妇女解放、社会解放。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猛烈地批判了封建礼教最腐朽的节烈观念,指出封建道德家所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了节烈,国便得救”的说教,不过是为了把女人当成私有物品或牺牲品,使自己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是为了维护他们僵尸似的统治,号召人们“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对被压迫妇女表示深切同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以进化论观点,批判了封建父权观念,为了让孩子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做父亲的应该“自己背着困袭的重担,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一种大仁大勇的精神。并且鲁迅还进一步指出,要确立新的父子关系,“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可见鲁迅不是就事论事探讨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把社会局部问题与整个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务求彻底解放。 在“五四”运动期间,鲁迅就批判了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妥协性、反动性。1925年五卅惨案前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相勾结,一方面阴谋复古;一方面用血腥屠杀来反对镇压人民的正义斗争。鲁迅以杂文为主要武器与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灯下漫笔》对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文明进行了极其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指出正是封建文明造就了人吃人的历史;《春末闲谈》则以细腰蜂的毒针做比喻,揭露历代统治者企图把人民群众治成“不死不活”,永远供其奴役的工具的毒辣用心;在《十四年的读经》和《青年必读书》等文里,再次暴露了孔孟之徒的丑恶面目,并且提出,倘有阻碍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充分表现了鲁迅反击复古逆流的坚决性和彻底性。 总观鲁迅这时期的杂文,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而且勇猛顽强,毫不妥协,其斗争目标、战略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呼应并非常一致的。虽然进化论的思想的确给他带来过消极的影响,但他从来停止他的探索追求。 (二)后期杂文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因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失败了。但中国革命并没有止步,鲁迅也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开始了他后期的光辉战斗生活。这时期的杂文,大多收入《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还有一部分收入《而已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1935年底,鲁迅为《且介亭杂文二集》所写的后记中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历时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事实上,不仅数量,内容上后期杂文也比前期杂文丰富深刻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