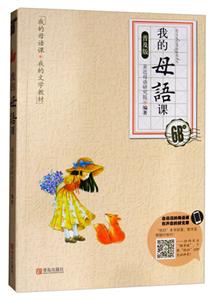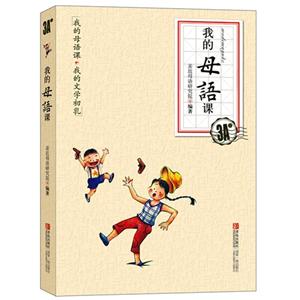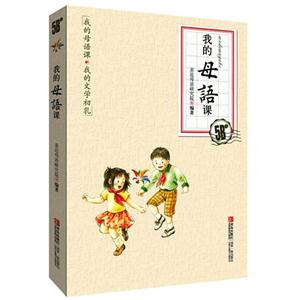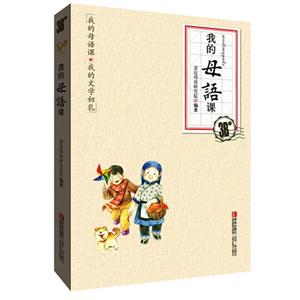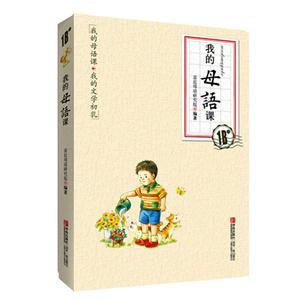作者:袁智中
页数:296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ISBN:978722218199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我的母语部落》一书是沧源佤族自治县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佤族本土作家、教授、滇西科技师范学院靠前佤文化研究院专职研究员为深入研究佤族文化历史变革的专著,该书获得“201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规划项目”立项,2017年获得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云南“民族直过区”佤族村落社会变迁研究》,该作品由此前两项研究成果整理而成,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准的关于佤族的历史散文作品。作者讲述的佤族村落故事,全部是发生在作者的故乡--沧源,时间自2004年10月至2017年2月。其中,大部分故事发生在2010年。这一年,是作者以学者研究佤族村落而进驻到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乡芒公村委会。在这年的10月,芒公村委会所辖的6个佤族村落、360余户沿坡而建的干栏式民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全部拆除,全面迈开了佤山幸福新村的建设步伐。在之后的5年里,作者不断重返芒公村,与族人共同亲历、见证着母语部落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和跨越,以及这种变迁交集中的震荡、惶恐、喜悦、梦想与挣扎。作者通过一个个带着生命体温的文字、一个个鲜活的场景、一群群鲜活的小人物的故事,向读者呈现其亲历见证的村落变革,以及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交集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改变。作者试图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佤族村落的变化应该是优选化和城乡一体化语境中,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村落深刻变迁的样本,是作者为自己的母语部落和族人们书写的一部村落志,是人类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心灵史。书中所描绘的应该是作者的母语部落和族人们,当下的生存现实、文化生态、独特审美的真实画卷,著作的讲述应该是从容的、客观的、理性的,同时又充满着生命的质感、情感的温度和人性的温暖,而不应该承载过多个人主义的情绪和民族主义的偏见。作者试图通过云淡风轻的文字,带有母语韵律的叙事,真实客观立体的记录,并希望通过这样的探索,拓宽自己文学叙事的边界,为传统村落志的书写提供更多的可能。全书稿共计25万字(含图片),由6章23篇作品构成。该书稿具有较高的文学和文化水准,出版价值高。尤其是对于一般读者了解和认识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变化,具有较高的提升和作用。
作者简介
袁智中,佤族,1967年生,沧源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临沧市作协副主席,云南省“四个一批”人才,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委联系专家。 文学作品获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新人新作奖、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边疆文学奖”“滇西文学奖”;教育成果获云南省高等教育成果二等奖。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主持完成云南省社科普及规划项目一项。 出版短篇小说集《最后的魔巴》,佤族文化散文集《远古部落的访问》,口述史《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口述实录》(合著),参编《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佤族卷》《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集·佤族卷》等。
本书特色
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以“在场者”和以母语部落“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记述了自己的母语部落和族人们在城乡一体化语境中经历的深刻变革、文化冲击、心理震荡、生存现实、文化生态和独特审美,是当代中国佤族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鲜活样本,是作者为自己的母语部落和族人们留下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
目录
重返芒公
村落的预言
贺帕猎王
贵喜的婚事
依惹家的摩托魂
寨主的家事
新米的节日
永莱动迁记
第二章 拱弄村落纪事
支书的家事
延迟的婚礼
村落的葬礼
沉重的祭祀
第三章 远古部落的访问
戛多村落记忆
最后的魔巴
小城的魅惑
第四章 芒公村落日记
芒公村落日记(一)
芒公村落日记(二)
芒公村落日记(三)
第五章 拱弄村落日记
拱弄村落日记(一)
拱弄村落日记(二)
拱弄村落日记(三)
附录
一种文化的梦想
以写作的方式爱着自己的民族
后记
节选
《我的母语部落》: 重返芒公 一 再回芒公,是说了三年的事。我知道,三年的时间里,芒公村正经历着她生命中最为深刻的变革。但无论世事怎样改变,无论我的心翻越了怎样的万水千山,都抹不去初到芒公村时那些总被金色阳光洒满的早晨和黄昏。 自从决定回芒公村过年,白天、晚上,吃饭、睡觉,脑子里满满的都是芒公村。三年前离别时的情景还在眼前,村民送的细如葵花籽般的蒜粒被仔细地一粒一粒剥着吃了,送的扫帚早已经用烂,手工编织的麻线床单还每日垫在床上,藤蔑圆桌还放在书房里,藤蔑圆凳则高高地堆在阳台上。拿出藤蔑圆凳坐一次,就要跟人讲一次芒公,每讲一次,芒公村的人和事就翻江倒海在心底汹涌一次。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深切地爱着芒公,爱着这些连汉话都讲不通顺的族人?于是,回芒公过年这样平凡的事,被我的思念无限地放大着。 二 佤历除夕的前一天,我和丈夫在沧源县城殷勤地买了烟和酒,驾着自家的福特轿车向着芒公开去。 穿过县城已经开始繁荣的街景,穿过勐角乡政府唯一的水泥路面街道,天便开始黑暗下来,路边的森林也变得浓密厚实起来。我知道,在这弹石公路的尽头就是我的芒公,我血脉偾张的源头。 车不断向着黑夜进发,昔日和大学生村官骑着摩托奔驰在星空下的景象不断在脑海中重现,对芒公村急切的思念在内心涌动升腾。我知道,穿过翁丁村成排的牛头桩,穿过独木成林的榕树和茂密的竹林,再一直向前,就是我亲亲的芒公了。曾经的沙石路面已经全部铺成了水泥路,但山还是三年前那座连绵的大山,坡还是三年前那个连绵的大坡。车在黑暗的山谷穿行着,我则在车的千转百回中,在黑夜中不断捕捉着芒公的气息。 灯光中终于映现出那片再熟悉不过的竹林,竹梢在黑夜中垂成优美的弧线。一个熟悉的90度大弯后,几栋红瓦白墙建筑开始在树林和竹林间闪过。这是芒公村的边缘地带,也是芒公村中离寨桩最远的位置。在这里,我曾经用相机记录过一对刚分家的年轻夫妇的生活。霞光中,他们五岁的儿子站在自家低矮的鸡罩笼草房前,用一双清澈无畏的眼睛望着我。即将呈现的村落变迁让我心底滑过一丝莫名的胆怯和不安。再连接转过两个大弯,那个被我日思夜想的芒公村就会在黑夜中呈现。 车灯有些刺眼,灯下的水泥路面显得越发地白,夜也显得越发地黑。几天来模糊零乱的记忆突然间变得清晰生动起来:路上边是芒公村二组,所有的房子都环绕着寨桩沿坡而建,这里不仅是太阳出来最早照亮的地方,也是芒公村最早的建筑群。三年前,我以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的身份入驻该村的时候,这里仍旧恪守着佤族村落最古老的格局:寨主和最古老的家族仍住在距离寨桩最近的地方,管理神林的副寨主家仍住在离神林最近的地方,所有分家而立的新家族成员,则沿坡而下分布在低于父辈的位置。村落看似错落无序,却暗藏着传统礼俗必须遵从的村落法则。 路下边是芒公村一组,下行的山坡较为平缓,干栏式草房和木楼一直从寨子中间的主干道延伸至村口的路边。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距离公路最近的位置,但从传统村落布局来看,这里仅仅是村落的拓展和延伸。或许正因为如此,与二组相连的是长满百年老树的神林,里面供奉着山神、寨魂和木依吉神;与一组相连的则是长满灌木的坟场,里面住着先辈的阴魂和被驱逐的恶鬼。 记忆的影像在脑子里重重叠叠,心却在包裹着芒公的黑夜中安稳下来。狗零乱的叫声在黑夜中响起,路旁村委会的灯正明晃晃地亮着。双层平顶钢混结构楼的墙壁看上去是那样的白,水泥院场也是那样的宽敞明亮,太阳能电热板在房顶若隐若现。 驻村那年,村委会没有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等身上的灰尘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脏得像爬满蚂蚁一样难受,就是最想回家的时候。当时的苦,回想时却成了别具趣味的浪漫回想。想起和村组干部一起,在还没铺上水泥浆的院场心,用石头垒成三角灶台烧起大火,支上洗澡盆一样的大锅,抬着两尺多长的锅铲炒菜做饭的情景。最喜欢吃的是村支书王林用腌得酸酸的竹笋和红红的小米辣煮的猪内脏和鱼。村里一有人家杀猪,或是有人进村,这样的美味就会重现一次。 我站在陌生的水泥路面举目四望,努力在黑夜中捕捉一些三年前的生活场景。三年时间,似乎自己没有多少改变,但芒公的房子、芒公的路、村委会的设施,都已经全部改变了模样。村寨是如此寂静,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副组长王贵喜家的小卖部亮着灯。 几辆摩托从黑夜中飞驰而来,一阵急刹车后,停在了小卖部前光亮的边沿地带,与我隔着一条灯光的河。在河的逆流中,几张男人的脸依次浮现:憨厚热烈的桑木茸、永远带着羞涩甜蜜笑容的陈岩门、新当选的副支书陈岩不勒,还有几个常扛着犁架、赶着牛从村委会大路旁经过的阿佤小伙。他们成排站着,手搭在摩托车扶手上,用一张张笑脸对着我。我的身体开始有暖流在涌动。是啊,无论村落经历着怎样的世纪变迁,但人还是这样一些人,脸还是这样一些脸。或许,自己怀念的并非是那个已经消失的村落,而是这一张张真诚坦荡的面容。 灯光深处突然响起了“袁姐”的惊叫声。副组长王贵喜顶着湿漉漉的头发,从小卖部的亮光中冲了出来,笑纹从嘴角一直向上蔓延,直到布满整张脸。凝固的“雕像”们从这声惊叫中惊醒过来,一同越过时间的河,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我的双手被紧紧握在了他们粗大厚实的手掌里,久违的山野气息开始在周身弥漫。我和芒公就这样轻易地穿越了时间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