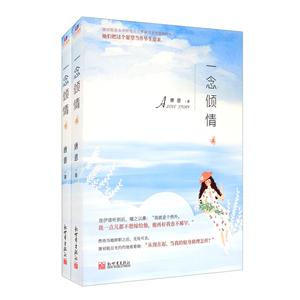作者:陶尔夫刘敬圻
页数:648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ISBN:978753173908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套丛书贯通陶尔夫和刘敬圻的学术精髓。词的抒情功能在他们笔下有了表达和多样的呈现,既从历时性方向揭示出了宋词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也从共时性角度展示出了每一阶段词坛丰富多元的审美形态,从深度上推进了宋词史的研究层次,也从广度上拓展了宋词史的研究领域。 《南宋词史(套装上下册)》以天然的多元互补和繁复开放的优势,令读者感受到宋词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对研究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及爱好者来说,是一部值得珍藏的文化积淀著作。
作者简介
陶尔夫(1928.9-1997.5),四川盐亭人。1948年参加东北地区林业系统工作。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毕业后赴黑龙江大学任教。教授,黑龙江省文史馆馆员。主要著作有《北宋词坛》《南宋词史》《晏欧词传》《姜张词传》《增订注释全宋词·吴文英词》《梦幻的窗口梦窗词选》《宋词今译》《说诗说稗·说诗篇》等。 刘敬圻(1936年生人),山东邹平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赴黑龙江大学任教,至今。教授,博士生导9币。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小说,词史。首届国家教学名师。
本书特色
《南宋词史》丛书贯通陶尔夫、刘敬圻的大家精髓,整套词史清晰地展现了南宋词史的生命构架,将宋词的产生、发展、艺术特色、各个流派、代表人物和代表作等进行了多样赏析评说,呈现了当时相关的文化背景、思想观念、文学风格等社会意识形态。既从历时性方向揭示出了宋词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也从共时性角度展示出了每一阶段词坛丰富多元的审美形态;深度上推进了宋词史的研究层次,广度上拓展了宋词史的研究领域。全书以天然的多元互补和繁复开放的创作意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令读者感受到宋词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词坛的转型期
第一节 亡国的哀吟与救国的呼号
第二节 高手云集的南渡词人之林
第三节 杰出的南渡女词人李清照
第二章 词史的高峰期
第一节 张孝祥及其他豪放词人
第二节 辛弃疾与词史的高峰
第三节 后南渡词人群
第三章 词艺的深化期
第一节 婉约词的进展与深化
第二节 “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姜夔
第三节 史达祖与高观国
第四节 “缒幽抉潜,开径自行”的吴文英
第四章 宋词的结获期
第一节 南宋灭亡前夕的激愤
第二节 灭亡前后的伤痛与悲惋
第三节 绝灭中的抗争与怒号
结语
后记
重印后记
再版后记
节选
《南宋词史(套装上下册)》: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参与过变法革新。父陆宰曾任淮南计度转运副使。陆游在其父溯淮进京时,生于舟中。出生第二年,金兵大举攻宋,他随家南渡。北宋覆灭后,陆宰因不满秦桧等人的卖国投降政策而退隐家居。陆游受家庭影响,自幼便立志抗金。因他坚决主战,29岁参加礼部考试时,被秦桧除名。从此陆游归乡返里,通过诗歌创作表达爱国激情,同时钻研兵书,学习剑法,随时准备报国杀敌。秦桧死后,陆游以父荫得官。在他任镇江通判时,正值隆兴抗战,他积极参与。抗战失利,投降派上台。“隆兴和议”达成后,他被诬陷免官。45岁时,因生计困难而乞任夔州通判,后任四川制置司及成都府安抚署参议官等职,居蜀中九年,到过南郑前线。晚年被迫闲居山阴20年之久,中间曾一度兼修国史。最后,他怀着“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憾恨,结束了作为诗人的一生。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大诗人,存诗9300余首。他的诗题材宽阔,内容丰富。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时代的剧变、百姓的苦难、个人的不幸以及细微的感情活动,无不被他写入诗中。抗金复国、爱国统一是他诗中的主旋律,是他诗中的最强音。 陆游也是南宋的重要词人。但是,他对词远不及对诗那么重视。对他来说,填词只不过是“余事”和“副业”而已。他的词同他的诗一样,始终饱含着昂扬激愤的政治热情。恢复失地的壮志与忧国忧民的怀抱,洋溢在他词篇的字里行间,具有一种俊爽流利、沉郁雄放的风格。著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有《放翁词》,存词145首。 在词史上,词人之成就高低、贡献大小,是跟他的创作实践、跟他作品的价值成正比的。而一个词人作品价值的高下,除其他条件(如天赋、生活阅历、创作激情、艺术修养等)外,最重要的还跟他对词这一诗体形式的认知密切相关。陆游的词远不如诗的声名煊赫。陆游之所以以诗名世,而不以词彪炳千古,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词的认知上有偏差,因而不可能在词的创作方面全面发挥他的天资与优势。 在词学观念方面,他恰恰和李清照的《词论》相左,甚至对词的性质产生隔膜与迷惘。词之初起,乃在民间,其所配音乐,为花前月下、舞席酒边之“燕乐”小调,故文人始作,便有“花间”“尊前”之称。之后北宋词人也多有用歌妓低俗口吻直写艳情者,与正统诗文之高雅尊严判然有别。因之,作者自谦、自惭、自悔之情时常有之,自毁之作者也不乏其人。陆游在《长短句序》(《渭南文集》卷十四)中说:“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①轻视词体,菲薄旧作,甚至悔之不及,凡此,都足以影响《放翁词》创作激情与才力的正常发挥。在另文《跋花间集》中,陆游对此说得更为清楚:“《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渭南文集》卷三十)①这两篇文字大约写于作者65岁。后来他的观点略有变化。如《跋后山居士长短句》说:“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渭南文集》卷二十八)②“汉魏”在文学史上是被称之为最具“风骨”的历史时期,思想艺术成绩显著,影响深远。以将汉魏乐府比之唐五代词,显然是对其予以高度肯定。他在《跋东坡七夕词后》中说:“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唯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渭南文集》卷二十八)所谓“东坡此篇”,当指《鹊桥仙·七夕》。其下片云:“客槎曾犯,银河微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陆游认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显然是说这样的词,应是诗人从中悟取为诗之道了。他的第二篇《跋花间集》对词的态度比之从前有明显改变:“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 ……